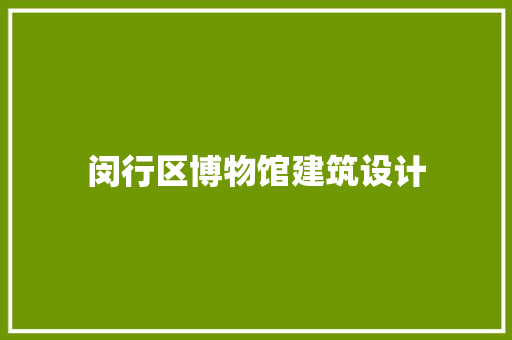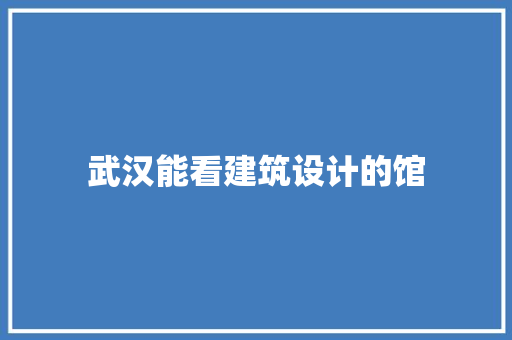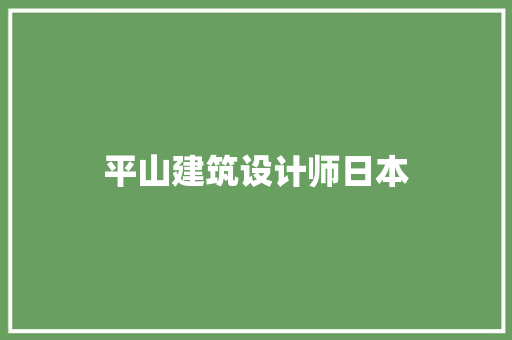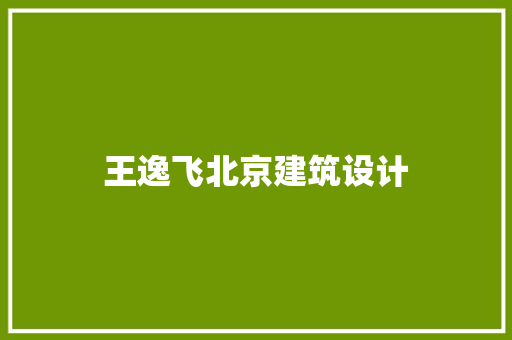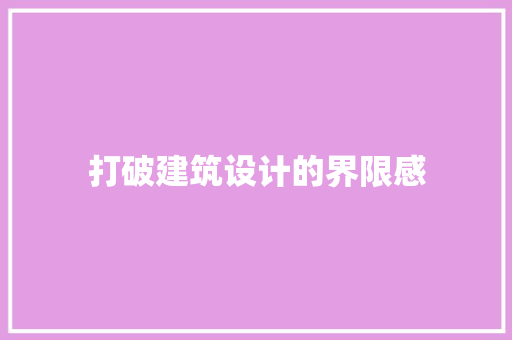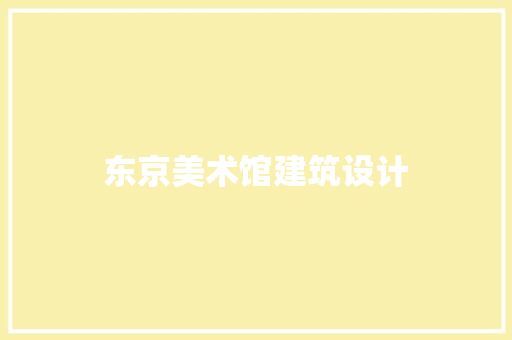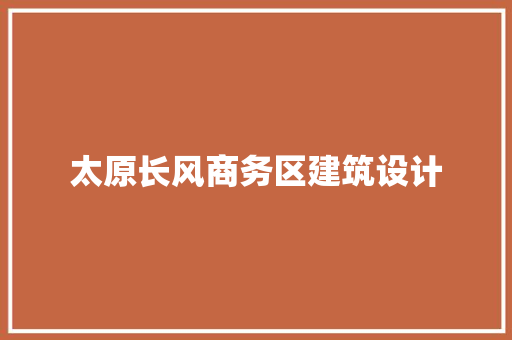近日,武汉琴台美术馆完成工程质量竣工验收,整体面貌得以呈现。长江日报独家连线专访琴台美术馆设计者、著名建筑师柳亦春,听他讲述琴台美术馆建筑设计背后的故事、他与武汉的分外情缘,以及他对建筑与城市、建筑与文化的所思所想。
柳亦春,53岁,大舍建筑设计事务所创始合资人、主持建筑师。

“‘琴台美术馆的薄暮’或许会变成一种风景的代名词。”和翘首以盼的武汉市民一样,建筑师本人同样流露出他对这座美术馆的期待与遐想。
选址在月湖畔形成文化场馆集聚效应
最近几年,因琴台美术馆项目,柳亦春频繁来回于沪汉之间。他多了个习气,每回来武汉,都会吃一碗热干面。“我一样平常是早7点多乘高铁,到汉口站是中午,去工地食堂午餐,下午开会和看工地,然后傍晚去机场,吃一碗热干面,上飞机回上海。”在这次专访中,我们首次得知柳亦春的籍贯是武汉新洲。柳亦春说,只管他没有在武汉长期生活过,但祖辈、父辈都曾在这座城市生活多年,父亲年近八旬乡音仍能脱口而出,虽身在山东,故土终难忘,这都让他对武汉这座城市多了别样的亲切之感。长江日报:从上海龙美术馆西岸馆到雅昌(上海)艺术中央、艺仓美术馆,近年来,你设计了不少美术馆等公共建筑,你特殊钟爱艺术吗?你是如何与武汉琴台美术馆结缘的?柳亦春:建筑本身便是一个跟艺术特殊干系的学科。2008年起,我在上海设计一些艺术家的事情室,开始故意识地对当代艺术做了一个别系性的理解。随后,在龙美术馆的设计中,我把自己对当代艺术的理解融入建筑设计,同时,将龙美术馆所处的黄浦江边的工业遗迹、城市历史影象浓缩其间。美术馆的建成引起了比较大的关注,也是由于这个缘故原由,我收到约请,为武汉设计一座新的美术馆。长江日报:第一次为琴台美术馆项目来到武汉,这片月湖之畔的地皮给了你若何的印象?柳亦春:2016年5月,我第一次专程为琴台美术馆项目来武汉做调研。看了好几个地方,包括琴台大剧院、琴台音乐厅、龟山、“汉阳造”艺术区等等。来之前,还做了很多作业,查阅了很多资料,尤其是身处月湖之畔的古琴台,这是一个有着深厚历史文化秘闻的地方。最开始,美术馆选址有三个选项,一处位于汉口的长江边上,另两处罚别位于汉阳的月湖边和龟山上。终极选址于月湖之畔,由于这里与琴台大剧院、琴台音乐厅为邻,更随意马虎形成文化场馆的集聚效应。美术馆建筑的参与重新定义了月湖南岸的城市空间。建筑西侧还预留城市广场,以及未来与方案中的图书馆和戏剧中央等公共空间,这样,叠加上古琴台文化名胜,全体月湖地区就可以形成一个聚拢性的文化旅游目的地。我以为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这是一座外柔内刚的美术馆
在柳亦春眼里,琴台美术馆是“外柔内刚”的。不少人认为,这是看起来最不像柳亦春作品的一个作品。但当人们进入室内,就会创造,净水混凝土等设计措辞的利用依旧为这座建筑打下深深的“柳氏烙印”。长江日报:为什么选择为琴台美术馆授予这样一种自然的建筑形态?柳亦春:琴台美术馆地块南邻月湖,湖对面是看上去树木茂密的梅子山,山不是很高,北侧隔知音大道是宽阔的汉江。正是由于美术馆所处的地理位置有着强烈的自然属性,以是采取自然形态的建筑策略成为一个险些不假思虑的选择。同时,考虑到湖边现有的琴台大剧院体量大,线条刚硬,以是想用一个相对柔和的形态参与,采取起伏的自然地形的造型减轻建筑对湖面的压迫,而且地下空间也可以和地面层更有机地连为整体。做一个自然地景造型的湖边美术馆——这一思考以及大略的成形险些是在一周内完成的。
长江日报:有人以为琴台美术馆的形状很像一片梯田,充满了古朴自然的气息;也有人以为被银白色、曲线包裹的美术馆像是来自未来的建筑,你怎么看?柳亦春:我以为大家的觉得都没有错。越是未来的,可能越是远古的,未来跟远古实在是相通的,就像我们看那些关于人类未来的科幻片,它们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同等,都是阔别现在的韶光。琴台美术馆里既用到了特殊当代的阳极氧化铝等材料,又有自然的植物、天然的石子,它们共同构成一个既当代又带有古意的建筑。起伏的屋面以略显抽象的等高线阶梯状造型完成,阶梯的侧面是银色的金属表面,顶面则为白色的石子和低矮的绿植。我没有让植物把它全部覆盖掉,由于这依旧是一个人工的产物,一部分是植物,一部分便是那种白色的石子,以此创造一种幽古的觉得,一种有一点间隔的韶光感。用当代的建筑手腕去呼应古琴台这样一个文化遗存,也是今与古的对话,人工与自然的对话。长江日报:琴台美术馆内部设计有何特点?柳亦春:美术馆大厅的空间和起伏的屋顶造型结合,塑造了独一无二的展览空间。当代艺术展厅采取漫游式的展墙布局,展墙既是展览的墙面也是起伏屋顶的支撑构造。首层和二层能共享一个大厅,在二层不雅观展的不雅观众看向首层,还能回顾起某幅画的位置。当代艺术展厅采取了相对传统的盒式展厅,位于当代展厅的东侧,有通透的玻璃面向月湖的景致。古代艺术展厅以及特展展厅位于地下一层,古代展厅相对封闭,是固定玻璃展柜的展览模式,特展展厅则比较开放和灵巧,具备多功能利用的可能。美术馆内的当代艺术展厅、当代艺术展厅、古代艺术展厅以及特展展厅在不雅观展流线上均可各自独立,亦可连续串联,具有非常好的功能灵巧性。希望琴台美术馆通过高水平的运营、内部丰富的展览以及各种公共活动的开展,能够成为武汉这座城市文化生活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它表达了我对当代建筑的东方思考
柳亦春出生于山东,幼年在江苏南京终年夜,10岁到17岁在青岛生活。父亲是一名作家,家中藏书甚多,他自幼喜好文学、历史。在一篇回顾青岛的文章中,柳亦春曾自述,高中阶段在杂志上看到了悉尼歌剧院和贝聿铭设计的喷鼻香山饭店的宣布,以为这个职业可以兼取文理之长,从此与建筑结缘。长江日报:人类是站在巨人肩膀长进步的。你最欣赏的建筑师是哪一位?柳亦春:我最欣赏的建筑师是当代主义建筑大师路易斯·康。他设计的著名建筑包括索尔克生物研究所、金贝尔美术馆,孟加拉国达卡国民议会厅、耶鲁大学艺术画廊等等。他是一个大器晚成的建筑师,他的建筑能够把历史和当代,把不同国家的文化搜集在一起。他是一位天下主义的建筑师。路易斯·康有一个著名的建筑之问——“砖是什么?”他用这样一种大略的措辞来表达他对建筑的态度。他是一位建筑哲人。如今,这句话常常会成为建筑系老师给学生们上第一堂课时提的第一个问题。“砖是什么”提醒着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做任何设计的时候,都要去追问问题的实质,从哪里开始,将走向哪里。长江日报:当代建筑开启于西方,我把稳到你曾多次提涌当代建筑的“东方思考”。在你的设计实践中蕴藏着若何的“东方思考”?柳亦春:我是一个身处东方的建筑师,我们在东方这样的环境里面做建筑,自然会有我们自己的文化思考。我们的文化思考可以来自文化传统、生活办法,还跟景象、习俗密切干系,这种思考可以来自唐诗宋词的意境,这种意境是我们独占的,可以通过建筑的措辞去表达它。比如同样是砖,路易斯·康用砖做出可能是一种觉得,我用这个砖做出的会是另一个觉得,以是只要我们找到了问题的实质,我们就可以从这样一个出发点去塑造属于我们自己的建筑。中国人对付风景的理解也是独特的。中国古代有非常多笔墨描述这样的思考,像唐代柳宗元的文章中,就提到了“旷如”“奥如”(注:柳宗元《永州龙兴寺东丘记》中,“游之适,大率有二:旷如也,奥如也,如此而已。”),便是说你看一个风景的时候,先有一个开阔的视野,然后溘然转到一个狭窄幽深的空间里面,然后再打开,就会特殊有传染力。“旷、奥”这种比拟,也便是欲扬先抑,中国园林也是这样的,这是中国的风景文化。琴台美术馆建筑的内部幽暗如“奥”,一旦从某一个洞口出去,则“旷如也”。我以为要在建筑中表达“东方思考”,不在乎说你用的秦砖汉瓦才是东方建筑,用当代的材料、用新的建筑形式将“旷如”“奥如”那种觉得表达出来,甚或达到诗意的境界,就会是属于东方的建筑,而且是一个更加符合时期特色、能够面向未来的东方建筑。不但是塑造建筑也是在塑造风景
柳亦春毕业于同济大学建筑系。今年3月,他曾撰文深情思念自己的恩师蔡德道师长西席。文中提到:“蔡师长西席在送别我回上海时的一封信中,描述建筑形式的最高境界,惶恐于师长西席的期待,迄今难以忘怀。”长江日报:我们常常会听到“网红”“打卡”这样的词,你怎么看待建筑领域的“网红”?柳亦春:我以为“网红”这个观点,里面可能存在着两种征象,一种便是为了网红而网红,为了博取眼球故意去做一些谄媚大众或者是夸年夜的、吸睛的东西,缺少一些深度的思考。还有一种便是为了去做一个贰心目中的好的东西,由于受到了大众的喜好,它变成了一个“网红”,我以为这两者是不一样的。真恰好的东西该当是能够为大多数人所理解、所喜好的。“网红”受到年轻人的欢迎,它里面也有大众审美的一种趋向,我以为肯定存在一定的合理性,或者说有他们捕捉新的要素的能力在里面。一旦有个东西好多人都喜好,证明它实在是有代价的,但是这个代价究竟是什么?实在须要去梳理、去判断或者是去提取,而不是说彷佛不经由思考,就只是点个赞。喜好是它背后的某一些东西,这个时候反而须要一些更专业性的勾引和沉淀。我也听说琴台美术馆还没有完备竣工就有很多人去拍照,然后在社交媒体上展示他们的照片,这彷佛已成为一种当代征象。一个建筑实在是一个时期的影象。它浓缩的是这个时期中,人们对付空间的理解、对付生活办法的记录以及对付美的印记。对付我来说,设计琴台美术馆,便是用建筑的措辞去表达我对这个时期的意见,对未来的一种期待,对人和自然之间关系的一种理解。
长江日报:设计琴台美术馆与你之前设计其他建筑有何不同?我们想象一下,在琴台美术馆正式开启的那一刻,公众年夜众溜达其间,你希望这座建筑留给人们若何的印象?柳亦春:做琴台美术馆跟我做其他的建筑最大的不同在于,在这里,我不仅仅只是在塑造一座建筑,同时也是在塑造一种风景。任何一个地方的风景名胜,实在都会跟某个特定的自然征象,某个特定的时令、环境干系。比如说在泰山顶上看云海日出。它一旦跟一个大的自然背景关联在一起的时候,就会超越功能性的体验,变成能够穿越时空的风景。琴台美术馆屋顶有蜿蜒弯曲的栈道穿行,这也是对自然山路的仿照或隐喻。它联系了月湖公园,也串联起美术馆的展厅出口、公共教诲空间、艺术品商店和图书馆、讲堂、咖啡厅平分歧的公共空间。人们的活动于是也成了建筑表面的一部分。设想一下,每当薄暮和夜色降临,小径上的灯光亮起,人们从四面八方溜达而上,就像是一种韶光的庆典,逐步地,“琴台美术馆的薄暮”或许也会变成一种风景的代名词、一个当代艺术的地标。长江日报:你怎么理解老师心目中的建筑形式的最高境界?柳亦春:“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是一种艺术表达的至高境界。便是说要超越一个详细的表面的形式,而去追求事物的实质。当建筑融入环境、融入不雅观者内心,成为一种印象,而不是这个建筑本身,我以为那会是一个更高的境界,也是一个美好的体验。就像我所期待的“琴台美术馆的薄暮”,末了带给我们的是一个印象,而不但是一个建筑的样子,那会是一个更高的境界。希望来到这里的每位不雅观众都能感想熏染到独属于自己内心的风景。
长江日报出品 采写:夏琼拍照:任勇 通讯员谢杰夫老白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