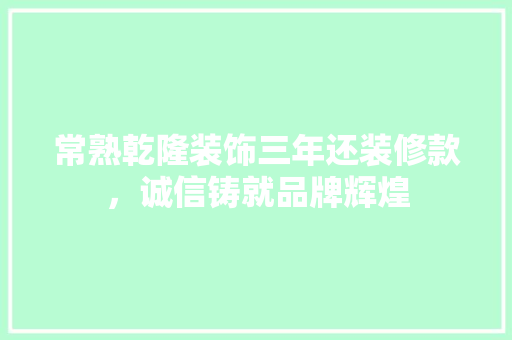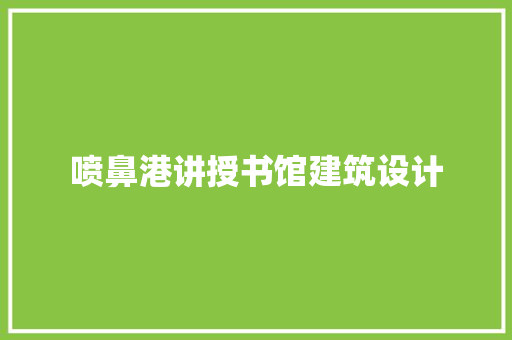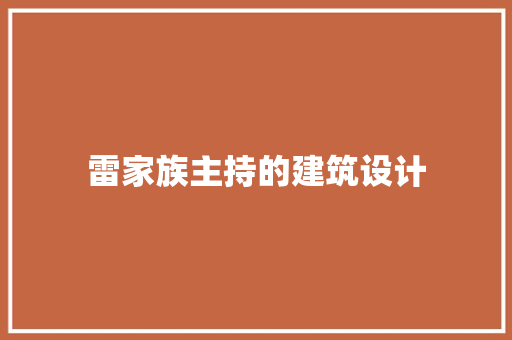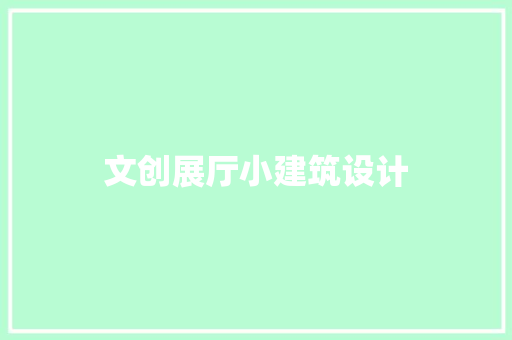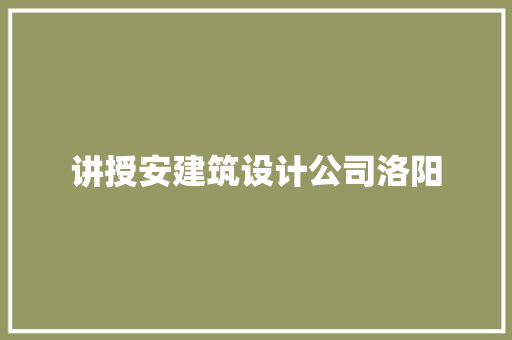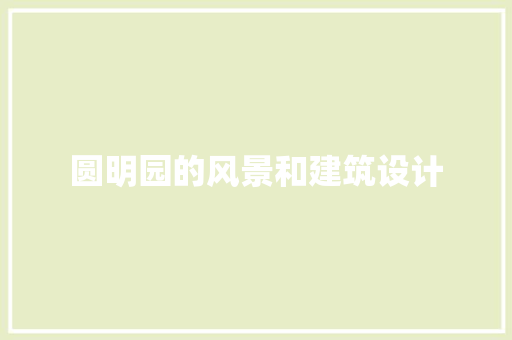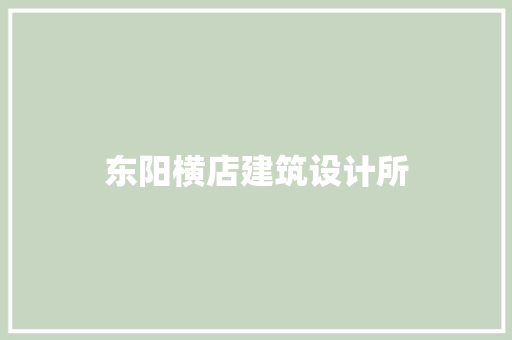△清代皇家园林代表——“三山五园”
满族统治者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长期以佃猎为生,与大自然结下了不解之缘。入关往后,不习气北京夏天的酷热和湿润,准备择地筑城避暑。顺治七年(1650年)七月,摄政王多尔衮谕令户部加派直隶、山西、浙江、山东、江南、河南、湖广、江西、陕西、九省地丁银二百四十九万余两,“输京师备工用。”同年十仲春,多尔衮病去世,筑城避暑的操持被搁置起来。由于频年战役,库款支绌,“终世祖之世,岁支常浮于入”,无力兴建皇家园林,仅将明代的南苑稍加修葺,“用备蒐狩。”

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二十二年(1683年),台湾归顺,清王朝的统治得到巩固,经济也有所规复。一次,康熙来到北京西郊的丹棱沜,“饮泉水而甘”,于是,在海淀明代皇亲武清侯李伟清华园的旧址上兴建了清代第一座占地约800亩的皇家园林畅春园,用以“避喧听政。”
△畅春园复原鸟瞰图
由于这个缘故,一些王公大臣和康熙的已成年的儿子们纷纭在畅春园的附近兴建自己的住所。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康熙将畅春园北一里许,地名华家屯的一块地皮赏给他的第四个儿子胤禛,胤禛用了几个月的韶光,建成一座小园。四十八年(1708年),康熙为之题额曰:圆明。这时的圆明园,占地面积约600余亩。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胤禛登基,这便是雍正。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在圆明园原有“亭台邱壑”的根本上进行扩建。“培植轩墀,分列朝署,俾侍值诸臣有视事之所。构殿于园之南,御以听政。”全园面积增至3000余亩,有风景建筑组群28处。从此,圆明园成为清朝五代天子(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常常居住和向全国发号施令的政治中央。
△圆明园复原图
乾隆登基的时候,清王朝已经建立了将近100年。国家的统一,政权的巩固,特殊是经济的规复和发展,为乾隆的大兴土木奠定雄厚的物质根本。乾隆认为,“泉货本流利之物,财散民聚,圣训甚明。与其聚之于上,毋宁散之于下。”他以“物给价,工给值”的办法,将国库的存银散到民间。从乾隆三年(1738年)开始,他就大规模地建筑圆明园。九年(1744年),建成圆明园四十景。命宫廷画家唐岱、沈源绘制成图,乾隆逐一题咏,命工部尚书汪由敦书写,按照左图右书的传统,装裱成高下两册,题名《圆明园四十景图咏》。
△圆明园四十景图咏——光亮磊落
乾隆在《圆明园后记》中犹豫满志地写道:“圆明园规模之宏敞,邱壑之幽深,风土草木之清佳,高楼邃室之具备,亦可称不雅观止。实天宝地灵之区,帝王豫游之地,无以逾此。”
△圆明园春景 费仓/摄
△圆明园后湖 胡光荣/摄
△圆明园福海 程师长西席/摄
接着,又在圆明园的东邻建筑长春园,并沿着长春园的北墙建筑一组欧式建筑泰西楼。后来,又将圆明圆东南邻的两座赐园并入,称为绮春园,从而形成了圆明三园的格局,占地面积5200余亩。
△圆明三园布局
与此同时,又先后改建和扩建了玉泉山的静明园、喷鼻香山的静宜园,并借疏通西湖的机会兴建了万寿山的清漪园。这便是人们常说的“三山五园”。
△三山五园
“三山五园”虽然相去不远,但是各有分工。乾隆在《清漪园记》中说:“畅春以奉东朝,圆明以恒莅政,清漪、静明,一水可通,以为敕几清暇散志澄怀之所。”这便是说,畅春园,是用来侍奉生母孝圣皇太后的;圆明园,是用来处理国家大事的;清漪园和静明园,是用作公余之暇放松身心的。这里,没有讲到静宜园,但是,它的功能,和清漪园、静明园是一样的。以是,畅春园、圆明园(包括长春园、绮春园)都各有一位内务府大臣管理,而清漪、静明、静宜三园则由同一位内务府大臣管理。
长城以北,还有一座规模宏伟的皇家园林承德避暑山庄。
△承德避暑山庄
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之后,康熙把事情重点转向北方。为了巩固边陲和提高八旗官兵的战斗力,建立了以“习武绥远”为目的的“木兰秋狝”制度。从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开始,在北京和木兰围场之间,先后建立了许多行宫,个中的一座,便是热河上营的热河行宫。由于这里环境柔美,既有西北山川的雄奇,又有东南山川的幽曲,与北京和蒙古都相距不远,得到康熙的讴歌。于是,这座行宫就在浩瀚行宫中脱颖而出,规模不断扩大。康熙五十年(1711年),康熙在澹泊敬诚殿前内午朝门上题写了“避暑山庄”四字,从此,这座行宫正式命名“避暑山庄”。
乾隆登基往后,连续经营避暑山庄。从乾隆六年(1741年)到五十七年(1792年)又建成以三字题名的三十六景。乾隆一朝,是康乾盛世的顶峰,这一期间避暑山庄的工程,也达到了皇家园林培植的最高水平。
宗教建筑,是清代皇家园林的主要组成部分。被称为“万园之园”和“统统造园艺术的典范”的圆明园中,不仅有佛教建筑,也有玄门建筑。在佛教建筑中,不仅有汉传佛教的建筑,而且有藏传佛教、乃至古代印度的佛教建筑。乾隆在《月地云居词》中说:“何分东土西天,倩他装点名园。”这就解释了皇家园林中宗教建筑的浸染。
△圆明园四十景图——月地云居
避暑山庄内虽然也有宗教建筑,但是,大量的宗教建筑,特殊是黄教的建筑却建在避暑山庄之外。康熙年间,建有汉式寺庙溥仁寺和溥善寺。乾隆二十年(1755年)至四十五年(1780年)的二十五年中,又建筑了十二座规模宏伟的宗教建筑。
△外八庙
这里,有仿西藏三摩耶寺(桑鸢寺)的普宁寺,有仿新疆伊犁固尔札庙的安远庙,有仿西藏布达拉宫的普陀宗乘之庙,有仿西藏日喀则札什伦布寺的须弥福寿之庙。此外,还有汉式的殊像寺、罗汉堂和前面是汉式、后面是藏式的普乐寺。这些宏伟壮丽的寺庙,都面向朴素淡雅的避暑山庄,排列在避暑山庄的东面和北面,有如众星捧月,象征着各民族对付中心政府的向力心,也象征着清代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巩固。它已不再是皇家园林的点缀,而是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了。避暑山庄和周围寺庙,是康熙、乾隆处理边陲民族问题的主要场所。
清代皇家园林的兴建,紧张是在乾隆期间。乾隆对皇家园林的兴建,为什么如此热衷?人们每每用乾隆自己的话“山水之乐不能忘于怀”来阐明。实在乾隆这样做,还有更高的追求。
△颐和园(前身为清漪园)
清漪园,是“三山五园”中末了建成的一座皇家园林,按照乾隆的习气,每一座皇家园林建成后,他都要写一篇记。清漪园是在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建成的,建成之后,却迟迟没有作记。一个主要的缘故原由是乾隆九年(1744年)圆明园建成后,他在《圆明园后记》中曾经说过:“后世子孙,必不舍此而重费民力以创建苑围。”清漪园的兴建,便是自食其言,于心有愧。但是,当他想到一个人有了缺点,自己不讲,别人也会讲的时候,终于写了一篇《清漪园记》。记中提到一个故事:西汉高帝七年(公元前200年),萧何在长安建筑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颇为壮丽。刘邦见后,非常生气,批评萧何说:“天下匈匈,劳苦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
”萧何回答说:“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宫室。且天子到处为家,非令壮丽,亡以重威,且亡以今后世有以加也。”刘邦听后,转怒为喜,将都城由栎阳迁到长安。乾隆对萧何的议论非常讴歌。他在《清漪园记》中写道:“萧何所谓必令后世无以加者,意在斯乎!
意在斯乎!
”往后人无法超越的宏伟壮丽的园林表现至高无上的皇家派头,这便是乾隆刻意追求的目标。乾隆的追求,客不雅观上推动了中国建筑艺术和园林艺术的发展,使清代皇家园林成为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和园林艺术发展的高峰。
有人认为,清统治者大规模地兴建皇家园林,导致清王朝国库空虚,国势衰落。这个意见,未必符合实际。清统治者建筑北京的“三山五园”和承德避暑山庄究竟用了多少白银?由于史料缺少,很难得出一个准确的数字。但是,清漪园的建筑经费,却是有案可查的。
“总管内务府谨奏:为遵旨查明具奏事。据内务府大臣三和等奏称:万寿山自乾隆十五年兴修起,至二十九年工竣,通共领收过银五百六十九万五千六百三十九两六钱八分五厘。万寿山建筑工程,用过银四百八十九万七千三百七十二两三钱四分六厘。内除各项木植旧料抵银四十九万四千五百二十两三钱九分三厘,实净销银四百四十八万二千八百五十一两九钱五分三厘。”
△颐和园(前身为清漪园)
清漪园,是乾隆为庆祝生母孝圣皇太后六十岁生日而兴建的一座皇家园林,占地3500余亩,是畅春园的三倍多,仅次于圆明三园。精心设计,精心施工,一气呵成,充分表示了乾隆的造园思想。乾隆对清漪园的景致也十分欣常。他在《昆明湖泛舟》一诗中说:“何处燕山最畅情?无双风月属昆明。”从清漪园的建筑经费,可以推定“三山五园”的建筑经费,不会超过一千五百万两,避暑山庄和周围寺庙的建筑经费,也不可能超过这个数字。两者相加,约即是乾隆朝一年的财政收入,而这笔建筑经费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天子在近100年中陆续支出的。
尤其主要的是,康乾盛世的土木工程,并不但是皇家园林。乾隆在《日下旧闻考》的《题词》中说:“余临御四十余年,凡京师坛庙、宫殿、城郭、河渠、苑囿、衙罢,莫不修整。”这一期间,北京涌现了一个城市培植的高潮,承德更是一个新兴的城市,全国各地,都不同程度地进行培植。只管如此,国库的存银,却由乾隆登基时的不过三千万两增加到四十六年(1781年)的七千多万两,增加了一倍多,这一数字相称于全国两年多的财政收入。这时,皇家园林的培植已靠近尾声了。说清统治者大修皇家园林,导致国库空虚、国势衰落是缺少根据的。
△雨果雕像和圆明园泰西楼遗址 王琇/摄
法国伟大作家雨果认为,天下上的艺术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东方艺术,一类是西方艺术。东方艺术是梦幻艺术,西方艺术是理念艺术。东方艺术的代表是圆明园,西方艺术的代表是雅典的巴黛农神庙。他盛赞圆明园“不但是一个绝无仅有、全球无双的精品。而且堪称梦幻艺术的崇高典范。”实在,梦幻艺术,是中国古典园林共有的特色。雨果说的梦幻艺术,便是我们说的诗情画意。清代皇家园林是中国古典园林的精彩代表,是中国公民为人类文明做出的主要贡献,也是我国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作为中国人,我们该当为此感到自满。
[文章来源]
《清代皇家园林与康乾盛世》
[作者]
王 道 成
[编辑]
赵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