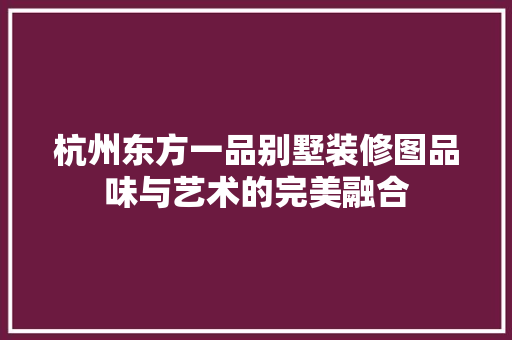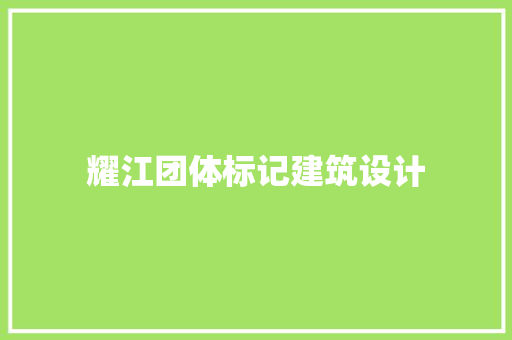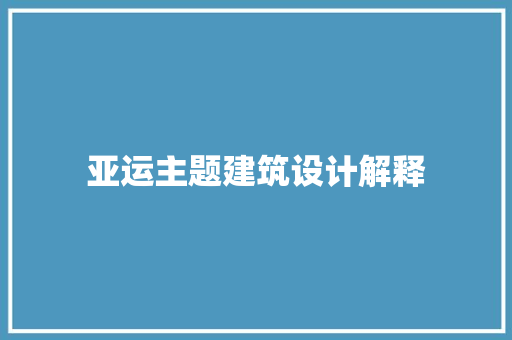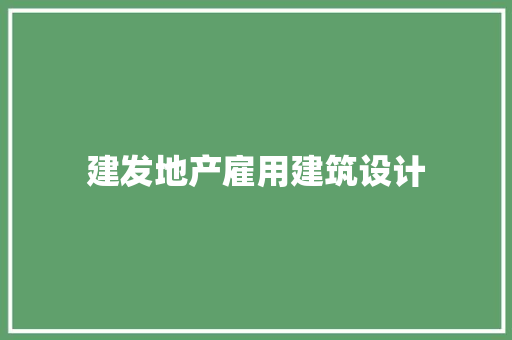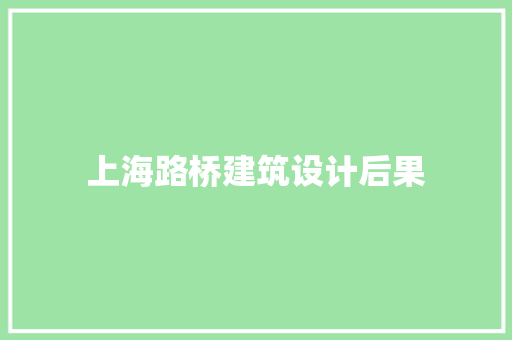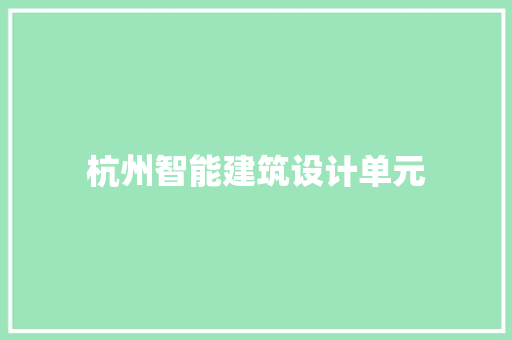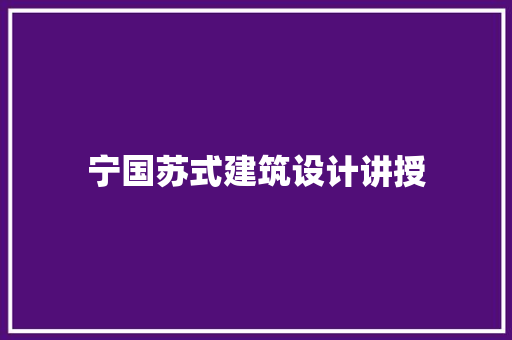唐末的墨客韦庄在《菩萨蛮》里写有一句家喻户晓的名句,“大家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论及江南美景,众人每每会遐想到元人奥敦周卿在《蟾宫曲·咏西湖》里所写的“上有天国,下有苏杭”这八个字。可以说,这句广泛流传的针言至今令杭州散发着持久的魅力。
但杭州这座城市并非一开始就具备“地上天国”的美姿。秦始皇统一六国,天下设为郡县。本日的长江三角洲一带属于会稽郡,而会稽郡治在苏州。到了东汉,会稽南部仍名会稽郡,治所在绍兴;而北部则分立为吴郡,治所仍在苏州。吴郡所辖的钱唐县便是今日杭州的前身,在吴、会以钱塘江为界分治之后,钱唐县紧靠两郡分界,不过是个处于边缘地带的蕞尔小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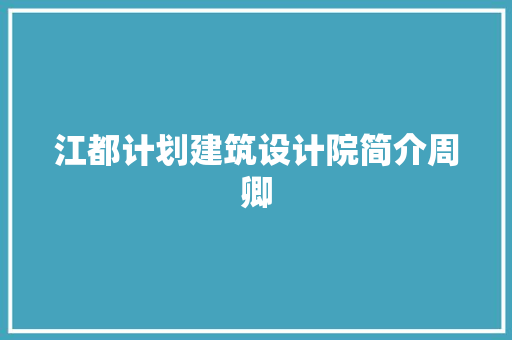
夏圭《钱塘秋潮图》
究其缘故原由是,由于直至南北朝期间,囿于生产力的局限,钱塘江下贱南北两岸的开拓还集中在中山丘陵与平原相接地带,以及海拔相对较高的平原地带。至于杭嘉湖平原则处于杭州湾与太湖之间,阵势四周高而中间低,呈浅碟状地形,外有海水入侵,内有湖水弥漫,注入“碟”中之水不易排出而形成沼泽区,开拓难度大,大面积的地皮因此长期处于未开拓状态。
改变这一情形的大约有两点,一方面,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们逐渐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水利培植,通过在杭州湾北岸修建海塘抵御海潮的侵袭、在平原内部太湖沿岸修建湖堤以阻挡湖水的上岸弥漫,在平原区内部兴修塘浦以利排水,促进了杭嘉湖平原低洼区的开拓;另一方面,公元589年,隋灭陈之后置余杭郡(唐代改为“杭州”),随后以钱塘县为郡治所在;比政治地位提升更主要的是,大业六年(610)十仲春,隋炀帝敕令“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广十余丈”,而江南(运)河的终点,恰在钱唐县。
自从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开通往后,如唐代的杜佑所说,“自是天下利于转输”。杭州这块曾经处于吴郡和会稽郡“边地”的地皮也因此一跃而“咽喉吴越,势雄江海”,确立起了它在钱塘江下贱地区“水牵卉服,陆控山夷”的交通枢纽地位,在全体钱塘江下贱地区取得了核心的地位。杭州的人口也因此迅速增加。公元609年,余杭郡的户口不过1.5万,到了不久之后的唐贞不雅观年间(627-650),已经猛增一倍,达到3万户,再过一个世纪,到天宝年间(742-756),又翻了一倍还多,达到8.6万户。到了唐代后期,杭州已是“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的茂盛景象。元和八年(813)中心政府任命卢元辅为杭州刺史的制文中也涌现了“江南列郡,余杭为大”的赞誉。
进入宋代往后,杭州开始得到“东南第一州”的美誉。嘉裕四年(1059)欧阳修作《有美堂记》时,杭州城已是“四方之聚,百货之所交,物盛人众为一都会”,到了南宋期间,朝廷建都杭州(称为“行在”),中原人口大量南迁。宋高宗赵构做了太上皇往后,有一次游西湖时碰到一个卖鱼羹的宋五嫂,原是东京(河南开封)人,太上皇见她年迈,特地宣她上船,赏给金、银钱和绢,命她常常送羹进宫。赵构有一次还见告宰相史浩,在行在做小买卖的“皆京师旧人”。也正是由于开封旧人大批移居杭州,杭州的措辞也起了变革,至今的杭州话还带有“方言岛”的味道。
到南宋孝宗时,杭州有26万户、55万余口。南宋末年时,杭州连同临安府属县共39万户,124万余口,这在古代,是个非同小可的数字。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著名游记里说杭州是当时“天下上最俏丽华贵的天城”;并夸奖“行在(即杭州)之大,全球无匹。一个人可以在那里寻到这么多的乐子,切实其实恍若步入天国”。这也是杭州城在古代历史上的顶峰。
14世纪杭州西湖
苏扬兴衰
经由元朝相对短暂的统治后,明代的杭州在江南失落去了独领风骚的地位。朱元璋定鼎金陵,南京在历史上首次成为大一统王朝的都城并因此臻于极致。可惜随着明成祖迁都北京,大批官员、军人和工匠随之北迁。降为留都的南京政治地位降格,人口也急剧减少,一时就衰落下去了。
反而苏州连续着发展的势头。苏州城居大运河之上,向来是南北水运商道的枢纽,比位于大运河尾闾的杭州交通更便捷,其余苏州还可以通过运河,以及浏河、福山塘等通道,成为长江这条东西向水运商路的主要转口集散之地。因此明代中叶,苏州城已经涌现了超越前代的繁盛景象。生活在苏州的王锜就说,“吴中素号繁华”,“以至于今,愈益繁盛”。晚明苏州出产的器物、衣饰等日用品以及字画技法更是受到了众人的追捧。浙江人王士性就感叹,“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
到了清代前期,苏州已成为全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城市。康熙时人沈寓就说:“东南财赋,苏州最重;东南水利,苏州最要;东南人士,苏州最盛。”苏州一府,区区9万余顷地皮,仅占全国土地的1%强。而每年交纳的税粮却多达250万石,占全国税粮将近10%。当时天下有“四聚”(京师、佛山、汉口、苏州)之说,而“四聚”之中,清人又同等认为市廛繁华以苏州为最。人称“吴闾至枫桥,列市二十里”。经济繁荣促进了人口的增长与集聚,康熙年间,已经涌现了“除是京师吴下有”的说法。时人盛称“吴城烟火,奚啻百万”。只管“百万”之说仍是个笼统之数,但既然有人敢于把苏州与人口达百万的京城相提并论,解释苏州人口纵然不及北京,相去也不会太远,应是当时的全国数一数二的大城市。这方面的另一个证据是,清代的苏州不只成为江苏省的两个省会之一(另一个是南京),还成为全国唯一拥有三个附郭县(吴、元和、长洲)的城市——即便帝都北京,也只设有大兴、宛平两个附郭县而已。
在清代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与苏州齐名的还有扬州。清代的扬州虽然位于长江之北,却常日被认为是一座江南城市。时云“扬州富甲天下。”清代康熙帝与乾隆帝几次南巡下江南,便都因此扬州为紧张驻跸之地。与苏州一样,扬州的繁华也与大运河有关。扬州处于长江与运河“T”字型交汇处,居于南北交通枢纽位置,加上明清两淮盐业中央设在此地,便使其成为沟通南北东西贸易的“四汇五达之衢”,成为长江下贱地区最主要的商品集散中央之一。广东、江西、湖北、湖南、安徽、浙江、山西等省贩子纷纭在此建立会馆。个中,浙江贩子紧张经营绸布,湖南贩子经销湘绣为多,湖北贩子以经营木材为主,江西贩子紧张经营瓷器,广东贩子经销南糖,安徽贩子经营盐业,而山西贩子则以开办银号为多。“四方豪商大贾,鳞集廩至,侨寄户居者不下数十万”,遂为“东南一大都会”。
然而,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扬州因大运河而兴,也随大运河而衰。清代中期嘉庆、道光年间,大运河已屡屡断航,险些到了破除的地步。同治十一年(1872 )漕运改海运,江浙沿海所产之盐也不必经扬州北上。轮船海运取代大运河的河运之后,作为贸易中转的扬州的地理上风地位已然不再。到了宣统二年(1910),北起天津、南至浦口的津浦铁路竣工后,扬州被彻底摒弃在中国南北交通要道之外,就是以屁滚尿流了。与此同时,铁路的兴起与运河运输功能的损失,也使苏州、杭州的商业地位不断低落。原来发达的苏州米市到清代后期迅速衰退,曾经十分兴盛的粮食专业批发市镇枫桥至民国初年已成“寒桥”,变得十分冷落了。
此落彼兴
不过,苏州、扬州、扬州等传统工商业城市在近代趋于衰落,却不虞味着长江三角洲的衰落——同处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上海在这一期间迅速崛起了。
坊间常说,上海原来是个小渔村落如斯。是日然是个误解。至元二十九年(1292)是上海建县之始,在此之前,上海就已成为“华亭东北一巨镇”了。在清代嘉庆年间的县志中,上海县被文人称为“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而到鸦片战役前夕,上海县已经拥有60余万人口,根据美国斯坦福大学施坚雅教授的研究,当时的上海是全国第13大城市,与天津、南昌相垺。从地理上看,上海位于长江三角洲和全体长江流域的焦点,又是中国南北海岸线的中央,具有广阔的经济腹地,并以其优胜的地理位置吸引着各地客商的到来,个中以闽、粤、浙、鲁等地为主,“逐日满载东北、闽粤各地土货而来,易取上海所有百货而去”。
当然,对付鸦片战役之前上海县的发展,倒也不能评价过高。无论如何,它只是一个松江府辖下的三等县城。嘉庆年间的上海县志,承认“方言同是吴音而视府城稍重”,同期间的松江府府志则说,“府城视上海为轻,视苏州为重。”总而言之,此时的上海,不过是大苏州光环下的小上海罢了。
1908年,俯瞰杭州。
到了鸦片战役之后,上海作为第一批条约口岸开埠通商,原来广州一口对外通商的局势被冲破,长江流域的货色沿江而下,集散于上海;浙江的丝、茶也大都销往上海转运出口而不再运至广州。于是广州逐渐失落去了在全国进出口贸易中的紧张地位。从输往英国的出口货值来看,1844年广州出口的货值是上海的7.7倍,而到了1852年则上海出口的货值反而是广州的1.7倍。正如马克思在1858年所说,“五口通商和盘踞喷鼻香港仅仅产生了一个结果:贸易从广州转移到上海”。
但若仅此而已的话,充其量上海不过是个贸易口岸。上海开埠十年后,城区人口仍旧只有55万,不能望苏州之项背。便是一个例子。近代上海之以是能发展成为一个人口达数百万的大都邑,要归功于移民的涌入,所谓“街头巷尾皆吴语,数祖列宗半外乡”便是指此而言。造成这一情形的直接缘故原由,便是19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战役。长达十年的战役,使人烟一向稠密的江南地区变得荒凉不堪,很多城镇在战火中变为废墟,庐舍化为灰烬。比如杭州城就从一个近百万人口大城市跌落到只剩下20 余万。
唯独上海在租界的庇护下成为例外。大量的官员、贩子、地主、士人、手工业者以及下层劳动者从战役波及的苏、杭、扬等城市向上海聚拢。1860年上海租界人口激增至30万,1862年又增至50万,一度还曾达到70余万。这些移民的大规模涌入为上海供应了资金、劳动力和需求市场,而这正是近代城市发展必需的要素。当太平天国战役硝烟散去之后,上海已成为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中央城市,而原来的中央城市如苏州却反而降为上海的从属城市了。到1949年,上海城市人口已超过500万人,成为无可争议的全国及长江三角洲的第一大城市了。
光阴又过去了70多年。如今,长江三角洲已经成为全国大城市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在超大城市上海之外,杭州、南京已跻身特大城市的行列,乃至昆山、慈溪、义乌这样的县级市也跨过了大城市的门槛。正所谓“江山代有秀士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作为生产者的人,是区域开拓的主要劳动力资源;而作为消费者的人,又须要有一定的社会财富供其消费。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口每每是衡量一个特定区域开拓能力和经济水平的主要指标。随着人口的不断聚拢,历时上千年的长江三角洲的城市“接力”,仍旧是个进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