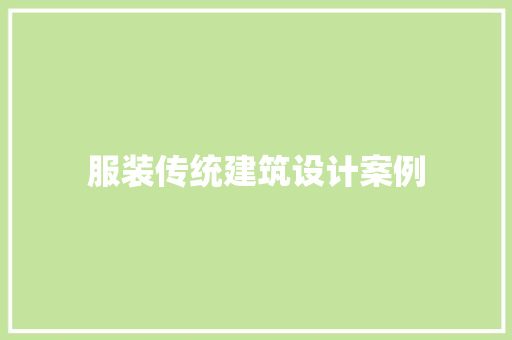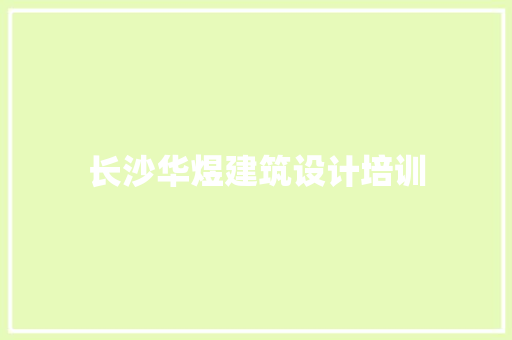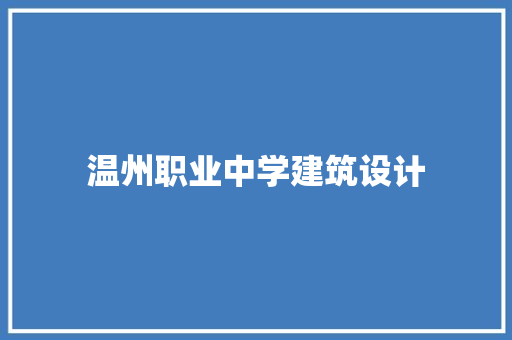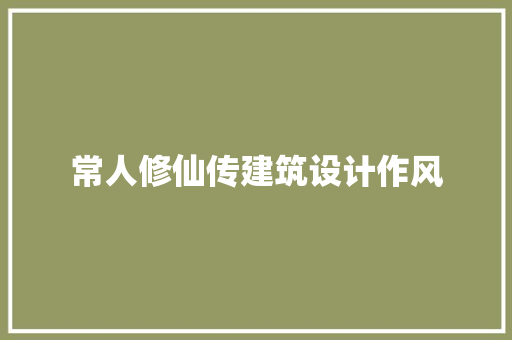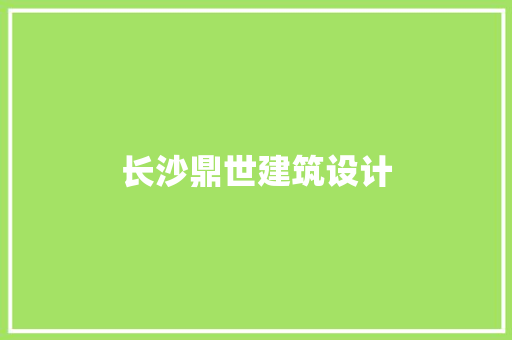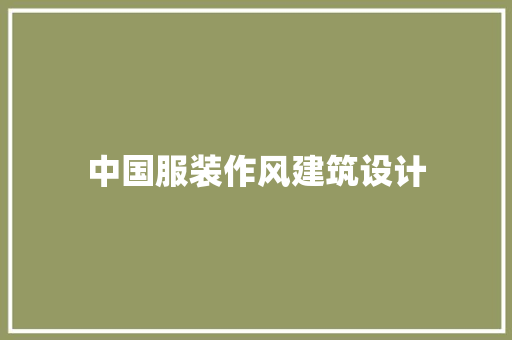一、“自下而上”历史不雅观念和研究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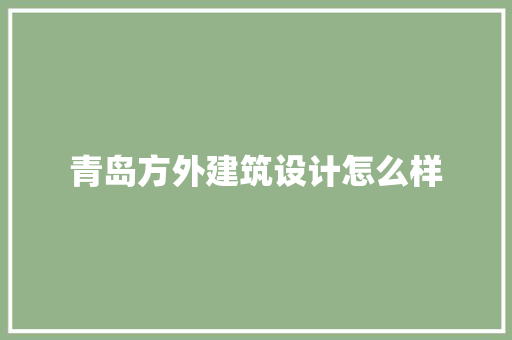
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以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拉斐尔·萨缪尔(Raphael Samuel)等为代表的英国史学家掀起了一种社会史研究新思潮。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辅导,环绕人类历史创造的主体与客体及其与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接管其他社会科学的新不雅观念和新方法来研究英国历史,于70年代逐渐形成了新社会史学派。他们批驳性超越法国传统总体史思想(如年鉴学派)和英国社会史研究传统(如屈威廉“打消了政治的公民史”和托马斯“以公民为中央”的社会史研究),构建了“自下而上”揭橥社会形成与发展之间普遍联系及其存在意义的综合与全方位剖析与研究历史的新方法,真实而全面揭示普通大众或下层民众日常生活(劳动和日常生活条件、生活办法的特点、物质和精神文化)的历史,反响下层广大公民群体作为社会发展推动力量的历史贡献。纳春英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不雅观为辅导,从整体史出发,改变以前只从文化或社会生活角度研究衣饰的碎片化研究方法,采纳“自下而上”研究视角,以考古学和文献学为根本,重点梳理隋唐平民衣饰材质、构成、装置本钱和禁忌及其历史演化脉络,考试测验建构隋唐平民的历史。她的研究具有多重意义:一是将平民群体衣饰及其变革作为不雅观察隋唐社会历史的一个主要视角,更新了隋唐历史的方法论,提出了一个新颖的研究范式,由于“下层历史代表了一种决议,由于它通过关注大众或人民的生活、活动和经历,把人们的把稳力从精英或统治阶级身上吸引开来。”二是这种整体性的“自下而上”视野在传统厚重的“自上而下”中国历史研究范式下,自然而然地有了相互结合的意愿与习气性行动,呈现出一种多视角的研究路径,考试测验展现平民通过衣饰参与并贡献于唐代衣饰文化发展和社会生活培植“微”与“著”的史学不雅观念与历史实践。三是“自下而上”历史不雅观念和整体史学不雅观念辅导下的平民关注既是作者选择的一种研究方法,也是作者作为一名隋唐史研究专家关注且主动选取的一个独特研究领域。以马克思唯物史不雅观为辅导的史学研究传统让作者研究隋唐平民衣饰时应然确然地提到了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与剖析方法,如“剥削阶级”(14页),再如对平民生存困难(275页)之同情,这些出于阶级的剖析也为全体研究注入了新活力,也试图让那些普通公民被历史抹去的声音该当被听见、让他们的历史浸染和贡献被认识。如作者所言,“实在平民的存在对历史期间的社会物质的增加和生产技能的提高,都产生过直接而积极的推动浸染。”(第3-4页)
二、“自下而上”整体稽核平民衣饰之新见
隋唐期间,作为社会秩序和等级制度表征的衣饰经历了北朝胡汉交融繁芜形态之后迎来了整体性制度回归与统合,平民衣饰在这一期间文化领悟大背景下如何研究?平民作为少见于史载的下层群体,其整体或个体生活形态被淹没于浩瀚史海之中,作者选择这一处于隋唐社会金字塔等级构造下真个群体,通过衣饰管窥其生存状态和社会环境,既有创新性学术意义,更有史料阙如和论述进路选择的寻衅。显然,作者回应了这些寻衅,以透物见人见精神和马克思主义新社会史整体不雅观念与“自下而上”不雅观察视角,通过莫高窟养活人透视隋代平民衣饰、将唐代平民女子日常衣饰与暴露女装分类谈论、唐代平民男子衣饰分唐初期和中晚期进行谈论。在这些通论根本上重点磋商平民礼服、衣饰材质和色彩、平民置装本钱、衣饰禁忌等“微不雅观”话题,末了触及平民的真实生活层面,并阐发平民男女困难生存状态的根由。纵览全书,既有隋唐期间的通透感,也有平视普通百姓过程中的深描与聚焦。
莫高窟唐代壁画
笔者将全书总结为以下七个方面的紧张特点:
第一,在资料搜集上,“竭泽而渔”。研究隋唐衣饰,考古资料实证颇为主要。作者采取了大量考古实物与图像资料,引用古籍、著作、论文等共计160余种。有了如此丰富的资料作根本,其立论言之有据,再加上科学的研究方法,研究成果令独著印象深刻,正如杜文玉教授所说:“纳春英的这部书不是一时的著作,而是长期的持续的研究结晶,据我所知前后持续的韶光不下十年,作者在这一期间陆续揭橥了不少阶段性的研究成果,做了大量的准备事情,参考和借鉴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这一点从此书的绪论中可以获知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杜文玉《序》)由于作者在搜集资料时文献材料与考古资料并重,因而“图文并茂”成了本书的一个显著特点。
第二,在研究方法上,作者看重实证主义的治学方法。作者指出,“衣饰在古代社会承载的社会功能极其强大,与之发生联系的不仅有社会生活、各种制度,还包括经济、法律、国际影响等各个方面,这就须要研究者在详细研究中,既要看到其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变革发展,还要发掘其与社会其他方面所发生的联系、所起的浸染以及所承担的功能等等。”(《绪论》,第3页)可见,作者的思路是“从总体史的视域出发,力求在主干清晰的情形下,多角度、多侧面研究隋唐衣饰”(杜文玉《序》),而其研究方法,则是实证主义的治学方法,这是在传统考据法根本上又借鉴了西方兰克学派的治学精神而形成的治学方法。
第三,在章节构造方面,布局合理,重点突出。全书共分十章,分别为“隋平民衣饰研究”、“唐代平民女子日常衣饰研究”、“唐代女装暴露征象研究”、“初盛唐平民男子衣饰研究”、“中晚唐平民男子日常衣饰”、“隋唐平民礼服研究”、“隋唐平民衣饰材质与色材研究”、“隋唐平民置装本钱研究”、“隋唐平民衣饰禁忌研究”、“唐代平民的生存状态与衣饰研究”。在这十章中,研究隋唐平民衣饰造型占了五章(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可谓重点突出;而其他五章,涉及平民衣饰的材质、置装本钱、礼服以及唐代女装暴露征象的历史背景与成因,可谓构造合理。
第四,看重礼服研究,也是本书一大特点。中国自古以来便是礼仪之邦,礼在古人的生活中霸占主要地位。从大的类型来分,礼分为吉礼、宾礼、凶礼等。作者在第六章专设“随唐平民礼服研究”,从“平民冠礼法服”“平民婚礼法服”“平民凶礼法服”三个方面对隋唐平民在成人礼、婚礼、丧礼(凶礼)平分歧礼仪场合的礼服进行了研究,指出隋唐平民礼服紧张分三大场合穿着:冠礼法服(包括笄礼法服)、婚礼法服和丧礼(包括殓服)礼服。
第五,“平民衣饰置装本钱研究”,立意新颖。在这一领域,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紧张集中在夏布、葛布、绢帛等的价格方面,而对这些原材料制成之衣饰的价格研究极少。鉴于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极少,可资借鉴者不多,这方面的研究便成为有一定难度的课题,具有创新性,正如杜文玉教授所说:“棉花栽种在唐代并不普遍,但在敦煌、西域地区已有栽种,各种棉布的价格也见于敦煌文书,根据这些记载与正仓院实物记账的记载,此书详细地研究了唐代棉布制作的各种衣物的价格。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这一章在研究平民衣饰本钱时不是笼统地说代价多少,而是分别就衣饰的各部分进行了研究,如头部、上身、下身、脚等部位不同的衣饰和鞋袜的价格情形,不仅增加了研究难度,而切还提高了研究的学术代价。”(杜文玉《序》)
第六,对“唐代女装暴露征象”研究,结论允当。作者对“唐代女装暴露征象”研究,从“唐代女装的袒露问题”“唐代女装袒露的流变过程”“唐代女装袒露的缘故原由”三方面对“唐代女装暴露征象”进行了剖析和研究,其结论是“唐代女性的袒露是中国衣饰史上的极度事宜之一,也是唐代女装的标志之一……所有溯因追源的事情都不应忽略南北朝以来女性不惜以妒妇形象涌现的平权努力,以及佛教《大云经》中佛陀将化女身救世的预言和武氏为其政治野心所做的平权努力。”(第85—86页)填补了我们以往认为“唐代女装袒露与唐代开放干系”的单一而局限的认识。
第七,对隋唐平民衣饰禁忌的研究,与以往比有所打破。以往的研究紧张集中在“服妖”方面,从民俗禁忌的角度研究不多。作者认为中国古代“禁忌”来源宽泛而不愿定,或源于上古先民的生存办法,或源于日常生活的技能局限,或源于法律禁制,或源于儒家礼制约束,这统统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平民衣饰。此书“从平民礼服中的禁忌、丧服中的禁忌、日常衣饰中的禁忌(包括韶光禁忌、方向禁忌、颜色禁忌、贵色禁忌)、女子头部禁忌、男子头部禁忌、足部禁忌等方面,对隋唐期间平民衣饰禁忌的各个方面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这方面已经大大地超约了古人。”(杜文玉《序》)
三、不仅仅“自下而上”:衣饰史研究的一些反思
前述本书的七大特点亮点及其对隋唐史、衣饰史研究的贡献之后,笔者不揣冒昧,提出一些值得反思和商榷的地方,并简述个人肤见。
(一)观点界定与材料选取之间存在一定的间隙。作者将“平民”观点限定为与官员和权贵相对的群体,包括隋唐社会中统统没有官职、爵位和封号之人,也包括富余庄家、大贩子和耕读传家读书人在内的富余阶层。特殊强调不包括贵族的侍女、佣仆、宫廷和贵族家养的伎乐、方外的比丘、羽士、道姑及娼妓等(第14页)。除了文献记载的官方性之外,隋唐墓葬及其陪葬物皆为国家丧葬制度界定下按照墓主人官秩位序安排的官方组合性系统配置,从“事去世如事生”儒家丧葬伦理仪轨或文化影象(纪念)传承功能来看,所有俑像器用皆为墓主人做事系统成员或元素,构成广义上奴隶侍卫体系和个人化的生活做事系统,有直接或间接的人身附属关系(尚需进一步研究)。按照作者“平民”观点,这批俑像所代表的、以做事墓主人为目标的个人化赞助系统显然不属于作者界定的平民序列,但作者却多处利用墓葬资料。如湖南湘阴县大业六年墓巾帕罩头的女侍俑(21页)、唐墓壁画宫女图(第69页懿德太子和永泰公主墓)与女伎乐(执失落奉节墓,78页)等不属于平民的“侍女”或宫女为何又能作为证据呢?北齐墓葬侍卫、武士(27-28页)和唐墓壁画出行图中马夫驼夫(98页)也能成为例证呢?乃至还有被作者打消在外的僧侣(123页)呢?
(二)细节或个案谈论有待进一步深入。作者敏锐地创造隋代贵族女性披袄子的时尚(42页)源于北朝夷族风尚,一贯延续至宋,西域、中亚也有将皮裘做袄子的征象。作者特殊强调袄子多为穿在身上,只有外披于身上的才称“披袄子”。姜伯勤认为这种披衣的穿着办法来源于西亚和中亚的风格。也有人认为披襖子来源于汉代袍服,承载了一部分宫廷隐晦生活礼制化的功能,属于中原王朝的宫廷秘辛。显然,作者仅仅关注到这个独特征象,并未进一步穷究。实在这一分外衣饰内涵和渊源极为丰富或繁芜。笔者曾有文章谈论过北朝至隋唐墓葬中俑像所披两袖空垂袍服的草原游牧和波斯渊源,应是一种身份地位象征,而非平民衣饰。而且披袍不仅仅限于女性,北朝至隋唐墓中大量男子俑像披袍,格局和功能呈现出由族性、礼性向装饰性和符号性演化的时段性轨迹。
(三)平民衣饰与时期共振的胡汉交融元素有待进一步挖掘。作者认为隋代平民女子衣饰经由魏晋南北朝期间民族大领悟后涌现了新变革,如上衣下裳等细节变革明显,她强调隋平民女子衣饰对朝鲜半岛衣饰的影响(第33-34页)。还该当磋商的是隋唐平民衣饰中继续北朝以来既有胡汉杂糅传统(北齐或北周)以及表示隋唐大一统创新性衣饰文化底层特色,或者随着时期变革新来的他乡元素,如是否存在像马夫驼夫一样将袍服下摆挽至腰带处的装扮服装,或者便于劳作将裤腿扎起来或挽起来的装扮服装(见于湖北湖南一带隋唐墓,可做参考),这些异于传统儒家“衣冠整洁”礼仪的奇装异服渊源何在?隋唐男子通用的幞头、窄袖圆领或翻领(单翻领或双翻领)与靴子套装如何随着胡汉交融潮流而变革乃至被定型?广义的胡服,还是狭义的胡服?
(四)其他一些细节问题。本书的个别用语也值得商榷。如说丧礼时有“哀子哀孙”一词,倒没有大的问题。但在屯子生活过的人都知道,在办丧事时,相訇把丧主的嫡系支属称作“孝子孝孙”,因而从准确性来说,似可变动为好。
上述四点反思可谓“瑕不掩瑜”,由于历史研究具有当时性和相对性,办理了自己预设问题的同时也总会提出一些值得连续研究的问题或方面。总之,本书材料宏富,视角新颖,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新社会史“”自下而上”历史不雅观念和研究方法在隋唐衣饰史领域的一次有益探索,而且“就内容的广度与深度而言,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以往的论著,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杜文玉《序》)杜师长西席的评语,可谓中允!
(杨瑾,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张维慎,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