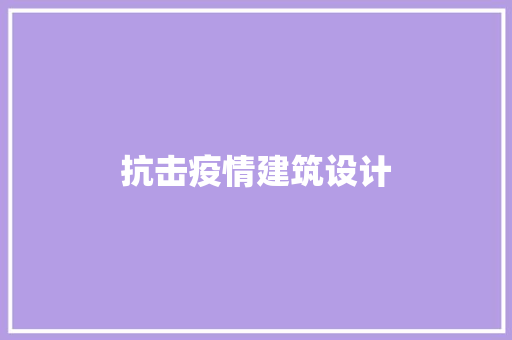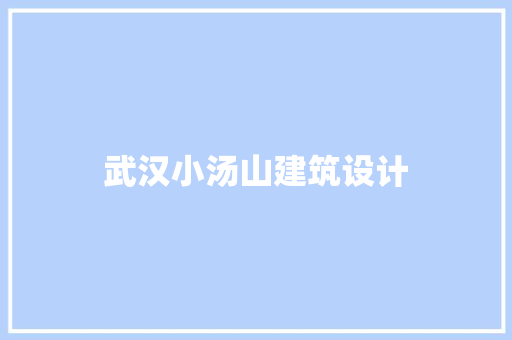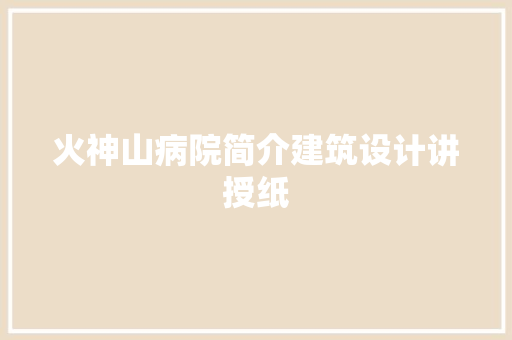1984年黄锡璆在比利时鲁汶大学留学时在住处前留影。
重新启用的小汤山医院。新华社 鞠焕宗摄

人物小传
黄锡璆:1941年生,籍贯广东梅州,归国华侨,中国著名建筑学家,2012年第六届“梁思成建筑奖”得主。2003年非典期间,黄锡璆曾带领团队设计北京小汤山医院;2020年担当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支持武汉火神山医院培植技能专家组组长。
见到大家口中的“博士”,正值一个阳光残酷的午后。透过办公室的门往里看,坐在书桌后的黄锡璆正拿着一个放大镜细细地查看图纸。见进来,已经79岁的先生长西席不顾腿脚未便利,立时起身相迎,并为房间的无处下脚而“道歉”。
作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医疗建筑博士,黄锡璆已在中国机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下属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中元”)事情了一辈子,职业生涯中主持设计了200余所医院。如今,虽已退休多年,但被返聘的黄锡璆仍每天早上8点半定时上班,他说,“我便是想再做一些事情……”
“碰到这样的大事,就该当贡献自己的力量”
“虽然这儿有不少博士,但‘黄博士’是独一无二的,我们都这么叫他。”有位“孙女辈儿”的同事悄悄见告。黄锡璆虽是大家,但一向随和,年轻设计师们不论做什么设计,都会让履历丰富的“博士”提提见地。
不仅仅是团队须要黄锡璆的见地——今年1月23日13时06分,有着小汤山非典医院设计履历的中国中元收到了一封来自武汉市城乡培植局的加急乞助函,要求对“武汉市培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应急医院”进行技能支持。当日14时22分,接到乞助函一个多小时后,修订完善的整套小汤山医院图纸就投递对方。
23日当晚,黄锡璆彻夜难眠。当年设计小汤山医院时的场景历历在目,“每张图纸,都印在心里”。24日一大早,他手写了一份设计建议,交给火神山医院的设计团队。“小汤山医院设计中有哪些难点,我得全部见告他们,并和大家一起谈论办理,希望火神山医院能够设计得更科学更人性化。” 黄锡璆说。
通过微信群,黄锡璆一贯和火神山医院设计团队磋商设计细节,完善设计方案,并根据前哨传回的资料,先后供应了三份详细建议书。火神山医院设计完成后,设计团队发来感谢信:“感谢以黄锡璆为代表的各位专家,你们展示了高超的业务水准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更令人敬佩的是,23日,黄锡璆就向单位提交了一份请战书:“鉴于以下三点:本人是共产党员;与其他年轻同事比较,家中顾虑少;具有非典小汤山实战履历。本人向组织表示,随时屈服组织召唤,随时准备出击参加抗疫工程。”
“家人担心您怎么办?”“老年人传染风险更高,被传染了怎么办?”……面对持续串的提问,黄锡璆轻言细语地说,“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是跟新中国一起发展起来的,碰到这样的大事,就该当贡献自己的力量。”
言犹未尽,黄锡璆又加了一句,“跟前哨的医务职员比较,我做得还远远不足。”
“这点苦不值一提,跟施工职员比条件好多了”
若问黄锡璆职业生涯中设计的最为分外的医院是哪一家,答案一定是小汤山医院。
韶光回到2003年4月22日,北京市决定建立小汤山非典定点医院。当时作为总设计师的黄锡璆恰逢眼病初愈,在家休养。但他依旧临危受命,当晚10点赶到单位,急速组织工程设计职员连夜投入事情。
集体谈论、分工勾画、群策群力……为争取韶光,黄锡璆和团队仅用8个小时就把总体方案设计方案拿了出来。很快,近6000名施工职员赶赴现场。这项分外的建筑工程进入了边设计、边施工的阶段,黄锡璆与其他设计职员一起战斗在一线。
从隔离层、混凝地皮基、箱式板房,到离地面架空一定间隔的病房、通道专用的隔离防护窗,都是黄锡璆和团队设计方案中须要考虑的关键点。“在院内总体布局中,首先要明晰功能区,把稳医疗区内各建筑物间的合理间距,处理年夜大好人流物流利道,办理好洁污分区,做好透风系统和采光等。”黄锡璆说。
四间只有桌子和床的大略单纯办公室内,他和设计师们“连轴转”地战斗了七天七夜。在指挥部命令设计师撤离前的几个小时,黄锡璆还坐在路边的台阶上,优化方案补充设计。在他看来,“这点苦不值一提,跟施工职员比条件好多了!
”
设计小汤山医院的困难前所未有,但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一座高标准的非典专科医院在短短7天韶光内拔地而起。
小汤山医院建成当日深夜便开始吸收病人,终极共收治了全国1/7的非典患者,治愈率超过98.8%,上千名医护职员无一传染,被世卫专家称为“医疗史上的奇迹”。这个中,科学严谨的医院设计功不可没。
凭借对中国当代化医院培植的卓越贡献,2012年,黄锡璆荣获中国建筑学界的最大声誉奖——第六届梁思成建筑奖。
“该读的书实在太多,不能摧残浪费蹂躏韶光”
1941年,黄锡璆出生在印度尼西亚的一个华侨家庭。从记事起,他就深深体味到内心对“家国”的渴望。1957年,16岁的他绝不犹豫地放弃印尼国籍回到中国,满怀激情亲切地投身国家培植。
回到祖国后,黄锡璆参加了高考,接管高档教诲,并在改革开放后作为公派职员留学外洋,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医疗建筑博士。
在比利时鲁汶大学留学期间,他险些把所有韶光都放在学习上,学校乃至给了他自取图书馆钥匙的“特权”。“实在,我也会倾慕同学们躺在草坪上晒太阳谈天,但是该读的书实在太多,不能摧残浪费蹂躏韶光。”1988年,黄锡璆学成归国。他说:“国家花了这么大代价培养我们,就该当赶紧返国做点事情。”
刚返国时,海内医疗建筑的设计理念还比较掉队。黄锡璆到偏远地区找业务,从几千平方米的小项目开始做,一干便是一辈子。如今已近耄耋之年,他仍齐心专心扑在专业研究上,还时常叮嘱晚辈:“医院不是别的建筑,是要救人命的,千万不能涌现问题。”
事情之余,他爱好不多,除了带老伴儿出去旅游,他把大量精力放在学习最新的专业知识上。他说:“我想完成写本书的欲望,踏踏实实把专业知识系统地梳理一下。”
手记
画笔勾勒家国梦
采访中,黄锡璆谈到成绩时总是说,“原来可以做得更好”;面对赞赏,他说的都是“我跟一线的医护英雄比较,差远了”。
60多年前,他离开亲人从印尼辗转归国;30余年前,他放弃国外优渥的条件毅然返国;17年前,他战胜视网膜脱掉队尚在规复期的病痛,一笔一画勾勒出小汤山医院的设计草图;如今,79岁的他在抗击疫情之时再次写下昼,为火神山医院培植贡献力量,让人不禁感叹和敬佩。可以说,每一页图纸,都承载着黄锡璆的家国梦想,每一所坚固的医院,都表示着他的工匠精神。(魏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