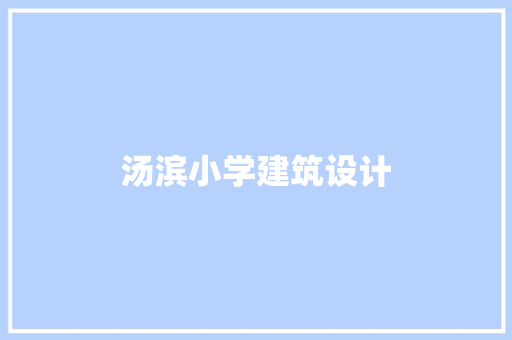武山县龙台镇青山村落有一处古老的旧宅。几百年前,这里曾是当地一位大户人家的厅房。古色古喷鼻香的四门八窗浮雕精美、雕工博识、手腕细腻、设计独特。装饰图案充满吉祥的寓意,寄托着主人的喜好和情怀。精良的雕刻,玲珑风雅、生动惬意,充满了人文气息,使整座大院古典持重。也是在青山村落,还有一处当地人称为“青山王”的府邸,殿堂虽已迂腐,梁枋雕刻却很精美,牡丹寓意富贵,莲花寄托和谐,暗八仙形象生动。
省级非遗武山木雕传承人康旭日就生活在这片氤氲着文化气息的古老地皮。五十年前,康旭日十六岁的时候,由于父亲是黄埔生的缘故,不能连续学业,走上了木匠的行当。康旭日拜邻村落的马应祥为师,学习三年,节制了屯子木活:民用建筑、民用家具的制作。康旭日随着马师傅在马村落干活,自己无法记工分,影响生存。他又拜本村落龙泉康家庄木匠康新正为师。康新正与马应祥同出师门,康旭日为艺依然以屯子活为主。康新正与马应祥师从马智贤,马智贤师从魏清云。武山清代武进士康岐的康进士大院、王家大院、“青山王”府以及龙泉寺等武山数一数二的建筑,都出自魏清云之手。1974年,武山县成立龙泉大队建筑队,其时,康旭日所在的康家庄是武山县龙泉公社龙泉生产大队的下属生产队。已经干了几年木活的康旭日进入建筑队,做了木工。甘肃省地质部门的一支水文队驻在武山龙泉。龙泉大队建筑队成立后的大业务便是给水文队培植蓄水举动步伐和库房。康旭日因此结识武山水文队的木雕师傅赵国祥,并向其学习木雕技艺,赵国祥成长于河南木雕世家。木雕是个辛劳活,不仅要耐性,还要有天分。“既然想学木雕,就得从各方面下功夫研讨,美术、书法都得会。”康旭日说。1992年,他又随武山县一中美术西席、后为中国美协会员的康云海学习当代美术画法。至此,艺道浑成,美术画法与木雕技艺交融贯通,逐渐形成都雅大方、厚重淳厚的技艺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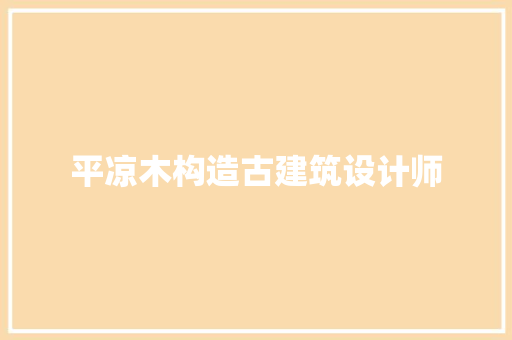
古建筑、古家具,都有精密的鲁班锁。所有榫卯之间的奥秘,既是木匠匠艺领域的诀窍,也是国粹。康旭日学艺、走艺的过程中,碰到了很多难题。一次,在拆除一座寺院时,门脸部分的木构造严丝合缝、环环相扣、无人能解,拆除过程面临难度。末了,挑头的人只能敕令用缆绳拉倒全体木构造。这次拆除过程令康旭日十分心痛。勤奋好学成为康旭日开启木雕艺术大门的一把钥匙,在几代木雕师傅的精心传承及自己的努力下,他终极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手艺人。
康旭日老家洛门镇向北5公里,坐落着天下最大的摩崖浮雕——拉梢寺摩崖浮雕大佛,这个建于公元559年前后的渭州仙崖,浮雕面积约1000平方米,高40余米,是丝绸之路大佛东渐一颗残酷的明珠。1987年,政府启动对摩崖浮雕的保护工程,在浮雕顶部加装一组遮雨棚。工程投入只有两万多元,康旭日当时所在的武山县第三建筑公司不想接这个活。康旭日捉住机会主动出击,接了人生第一单属于自己的公家活,“三建支持设备,我以私人名义干。”康旭日打了“第一桶金”往后,辞掉了三建的事情,从此转入仿古建筑行业。1992年起,他开始组建团队,先后承接了张家川宣化冈、麦积区马跑泉清真寺、华亭县玉佛寺、平凉崆峒山、兰州法幢寺等仿古建筑的木工工程。
武山水帘洞石窟群是国保单位,有名遐迩,在设计混元门的时候,他就考虑了它的影响力,大手笔设计,两层双重檐,个中称绝确当是八仙贺寿、牡丹、蝙蝠、葡萄、松鼠等木雕构件,涵盖着浓厚的传统文化意蕴。艺术创作,并不是闭门造车,始终是要走向大众,面向市场的;更要留下经典,走向未来。他的雕刻工艺与时俱进、日趋博识,面对每一份材料,都要精心构思设计,只管即便表示不雅观赏性和实用性,在设计和雕刻中融入自己的艺术感不雅观,大到桌椅、屏风实用类,小到工艺微雕不雅观赏类,尽力做到造型都雅,让群众喜闻乐见。
手握刻刀五十年,从木雕学徒到省级非遗传承人,他深刻懂得传统文化艺术在传承上的困难。默默坚守几十年,他尽情施展镂雕、透刻、浮雕和镂、刮、镂空等雕刻技法,浩瀚木雕作品还原着历史的风貌,让人们重温着残酷的文化,在不雅观赏的同时,给人以美的享受,并将博识的技艺传授给徒弟。匠艺负责,为人和蔼,技艺和人品都为康旭日赢得了好口碑,大半个县城的寺庙、牌坊、殿宇都被这位老木匠承包了,康氏木艺在武山木雕行业独树一帜,成为武山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一张响当当的名片,康旭日的艺名早已远播陇上。
传统木雕工艺精雕细琢,耗时耗力,“我前前后后建筑的仿古建筑大大小小不下220座,个中民宅20余座,也就收了20多个徒弟,由于这门手艺太费精力,而且出活慢。”作为武山木雕省级“非遗”传承人,康旭日深感任务重大,他的儿子从小学了绘画,一贯做仿古建筑彩绘,这几年进入木雕领域,进步很大。儿媳妇倒是对木雕很感兴趣,全程随着他学木雕。“年轻人不愿意学这个,我就让儿媳女儿半子学,我们作为传承人,有任务将这门技艺一代代传下去。”对付武山木雕的保存与发展,康旭日有着自己的深刻理解:无论是何种民间文艺,大多是与“传统”这个关键词相挂钩,“口口相传和父子师徒相承”的办法,是这些文艺最原始,也是当前仍在延续的传承办法。新时期,文艺的传承模式、发展办法,都面临着加快转变的境遇,如果还是抱着传统的办法和模式,势必使民间文艺越来越走向封闭与没落。抱着这一武断的想法,康旭日积极投身于民间文艺的抢救、保存、传承奇迹中。
来源武山县融媒体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