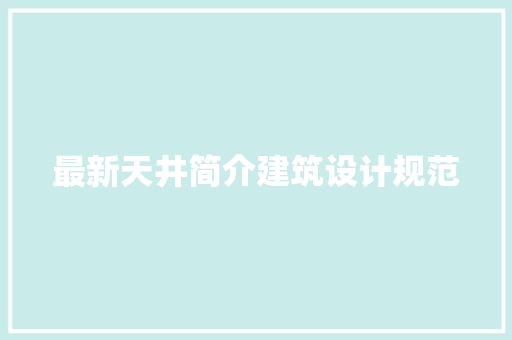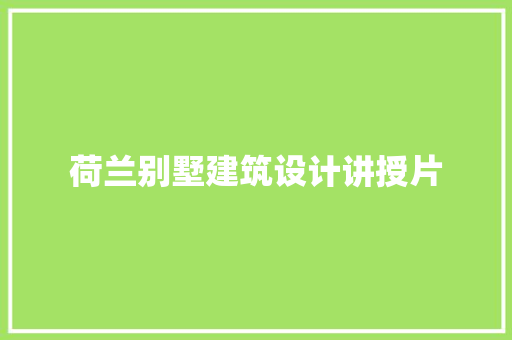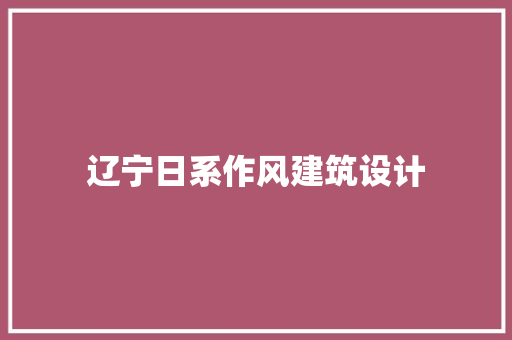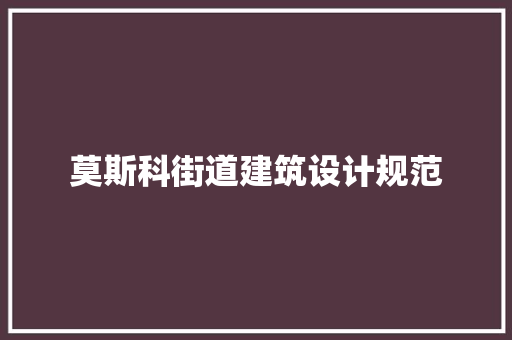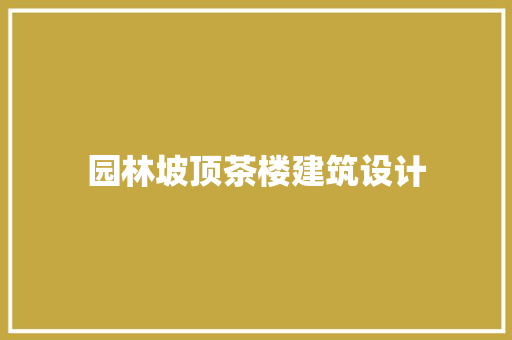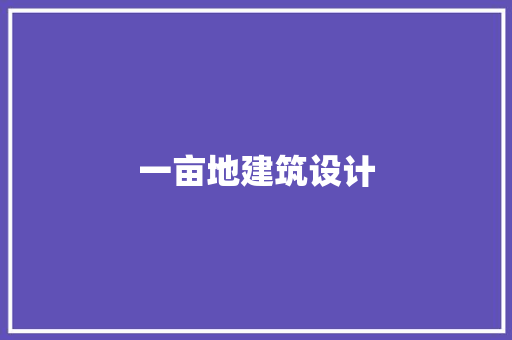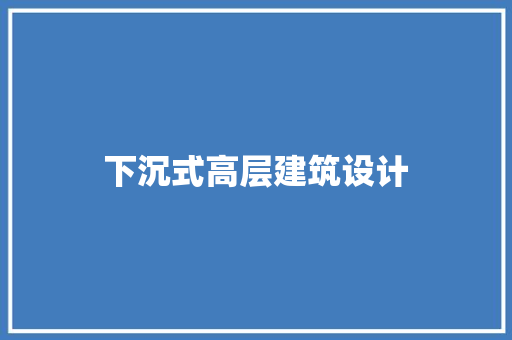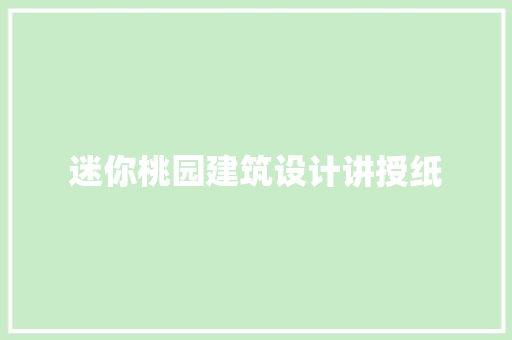彼得·德·霍赫 荷兰庭院 69.5×60cm 1658-1660年 布面油画(美国华盛顿国家美术馆)
17世纪的荷兰小画派因成本主义的发展而不断壮大。荷兰在17世纪成为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由新兴的资产阶级掌权,加尔文教与其他宗教原谅并蓄,公民开始意识到自身代价,传统的圣经故事与神话故事类绘画失落去市场,风尚画、风景画、肖像画逐渐成为主流。《荷兰庭院》是范例的风尚画,这类绘画在内容上向市民生活靠近,且装饰性与商品性更强,常日挂在市民居住场所,因此尺幅也较小,更具生活性。虽然这类画只是挂在普通市民家中,但画中所蕴含的艺术代价远非普通装饰类绘画可比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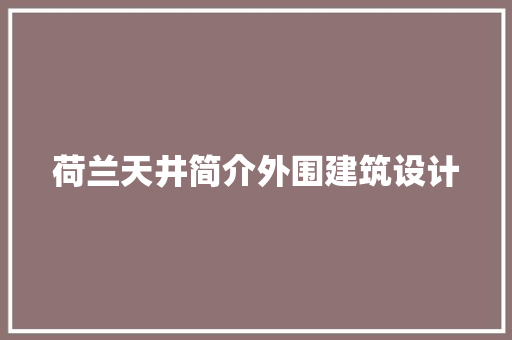
当我们细不雅观《荷兰庭院》,吸引眼球的必定不是画中的人,而是画面中柔和奇妙的阳光与纯粹的色彩。画面描述的是一个常见的饮酒游戏,每个参与者都必须要喝到玻璃杯上的一条圆线才算达到哀求,画中妇女手持葡萄羽觞,小心翼翼饮酒的样子容貌逗笑了那两位男士,而在角落里,怀里揣着炭盆的女孩脸上充满忧郁。这些动作都发生于一瞬间,迅速而又充满戏剧性,但人物的故事情节从不是德·霍赫描述的紧张目的,画家更乐意去表现一个真实而充满诗意的场景氛围。纵然这些人喝完酒离开了庭院,也并不影响整幅画带给不雅观者的冲击力与传染力,画家不遗余力描述繁琐的细节,大到洞开的门窗,小到木板上的裂痕,这些物体发挥着它们在光与色上的代价,他用这些眇小的细节添补着朴实的画面,以达到他所期望的氛围感。
德·霍赫喜好描述多变的光芒,柔和的阳光充斥着《荷兰庭院》这幅画。明净的光芒洒满了全体庭院,他把在圣卢加工会所学的知识结合自己对付色彩的敏感度融入这幅画中。因庭院受阳光的照射,画家竭力表现不同质感的物体对光芒的反射,如右下角女孩的蓝色裙子上,他利用鲜亮的黄色来表现裙子的光泽,妇女裙摆上大面积的赤色通亮但不刺眼、锐利,画中所呈现的鲜亮的颜色与厚重的笔触与之前的油画创作有很大差异,虽谈不上创新,但确实让人线人一新。
若提及构图,画中的那扇门或许也同样引人瞩目,这是范例的“德·霍赫”式构图,有人称它为“see-through door”。在庭院尽头有一扇洞开的门通向后面的花园,花园中的树干与画面上方的树叶刚好衔接,增加了空间的延展性。通过左侧的台阶穿过树木茂密的院子,便可以看到左侧远景代尔夫特的新教堂(Nieuwe Kerk),但我们并不能确定这个庭院的详细位置,由于画家常用虚构的办法组合建筑来达到画面构图的完全性。
荷兰小画派独特的地域性注定其不能成为欧洲绘画的主流,《荷兰庭院》这类绘画被尘封许久,直到19世纪后半叶众人才重新创造了它的艺术代价,画家用独特的光影与构图再现了时期的面貌,朴实而又充满诗意的绘画唤起了不雅观者的共鸣。
来源:美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