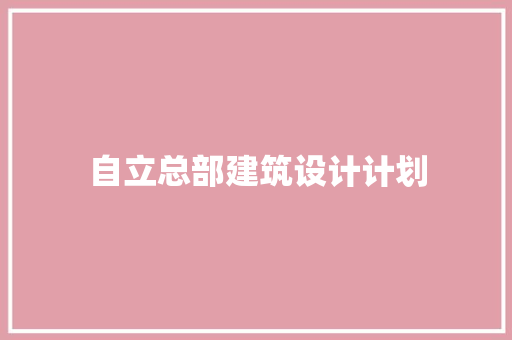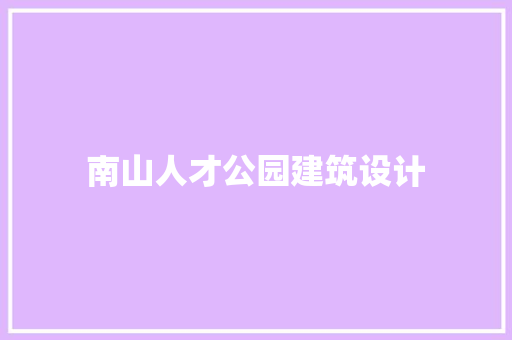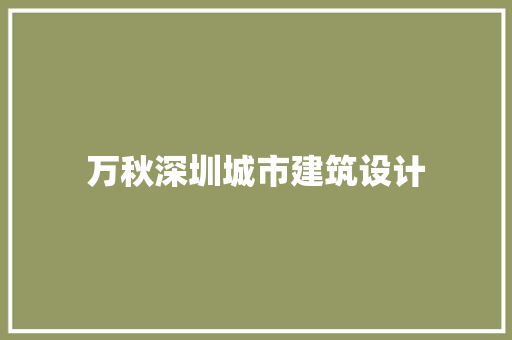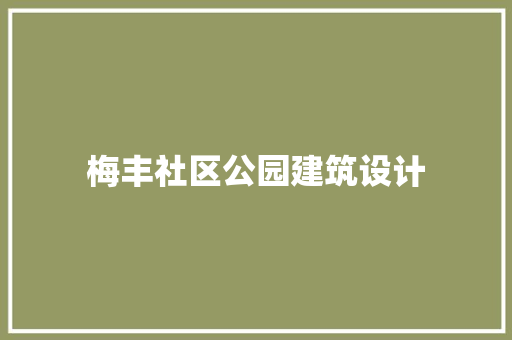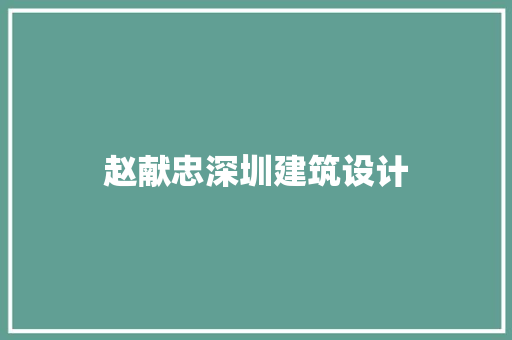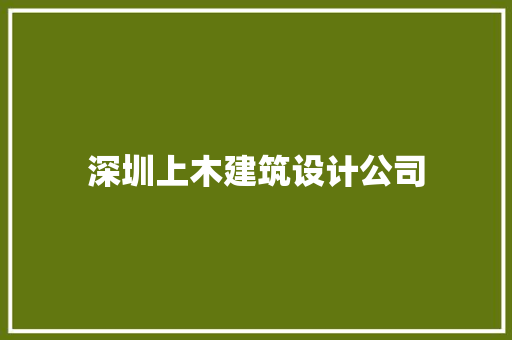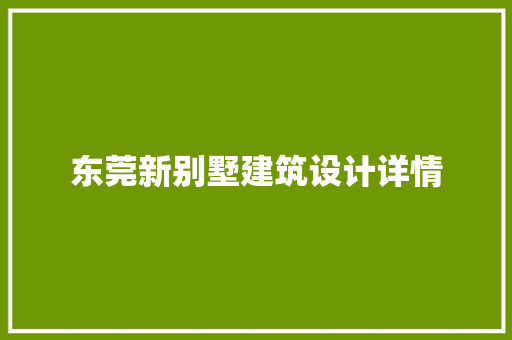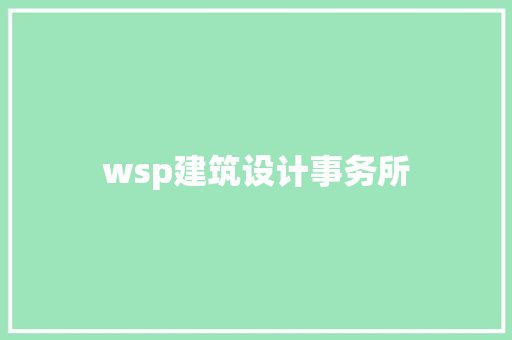8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40周年纪念日,周顺斌终于等到了这一天。早上6点,他起了个大早,手握相机,独自一人坐上地铁2号线,一起向西来到蛇口港。
原来这统统都是操持好了的,他打算记录“深圳24小时”。先去蛇口那块“韶光便是金钱,效率便是生命”的广告牌下,拍下太阳升起落在深圳湾的第一缕阳光,再乘坐双层不雅观光巴士绕城拍摄,末了晚上十点半在市民中央参与纪念日直播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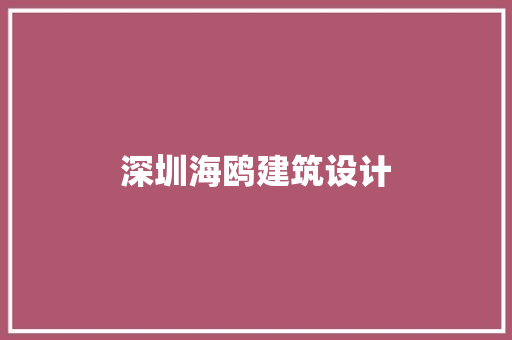
退休后周顺斌从来没有像本日这么劳累而又充足。虽然平凡日子里,他也会外出拍摄,但大多时候,他都扎在深圳广电集团老干部活动中央那间铺满他拍照作品的屋子里,戴着老花镜,对着电脑一张张整理、放大底片。
照片里有20世纪80年代初荒漠一片的深圳火车站,有“三天一层楼”国贸大厦下的塔吊指挥员,也有那群脱下军装上夜校的基建工程兵......周顺斌的镜头记录了深圳从边陲小镇到大都邑的蜕变,还展现了这座城背后拓荒人的那段真实、激情、笑中有泪的历史。
一支军队一座城
周顺斌
周顺斌1953年生人,深圳拍照家协会顾问。16岁参兵,上世纪80年代初,随两万多基建工程兵来到深圳,被称为“横跨40年的深圳影像记录者”。
16岁参军,周顺斌的青年时期是在辽宁鞍山基建工程兵部队里度过的。靠近30岁,正值壮年的他在一声军令下,随两万余名基建工程兵来到深圳,再也没离开过。他和他的镜头陪深圳一起走过10年、20年、30年,再到如今的40年,他也迈入了老年。
谈到近40年来自己记录的宝贵镜头时,周顺斌彷佛在讲述自己疼爱的孩子。他不偏爱谈一些壮不雅观的建筑场景,而是选择一些生活气的场景娓娓道来。讲到部队初来深圳的那段艰巨岁月时,他主动指着一幅令他印象最深的照片,一名渴了在水沟边俯身喝水的战士,嗖一下的揪紧衣领说:“实在拍的时候,我的心里是收紧的、酸涩的”。
但过一下子,他又指着另一幅战士们收工后,在营地一处自挖的水井旁洗沐的照片,笑着说:“你看,洗去一身尘土,是他们最惬意的时候”。本便是工程兵出身的周顺斌熟习战士,更体恤战士。
周顺斌最出名作品《升》的拍摄工具邹洪涛记得,他常常能在工地上的烈日下见到周顺斌到处“瞎转悠”。在特区培植初期最为艰巨的时候,周顺斌是部队卖力宣扬的宣布员,他常常会踩着一辆背后拴着相机包的五羊牌自行车,一声不响地奔波在各种建筑工地上,找题材、找灵感,光自行车就骑坏了三辆。
《升》
提及拍摄《升》,周顺斌要感谢老战友邹洪涛。1984年的某个炎酷暑季,参军队转业进入电视台的周顺斌,仍旧一大早就背着相机在施工地上跑,一次在红岭大厦找角度拍摄,邹洪涛闯入了他的视野。昔日老战友也已转业褪下军装,穿着一件蓝色背心正在指挥“大吊”。
“拍照师的直觉见告我这是个好素材”,周顺斌立即叫邹洪涛站到两栋对称大厦三层高的基建上,重新指挥一次塔吊。但此时早已不像在部队,存在合营之说。就在数月前,1983年9月15日,是两万基建工程兵集体脱下军装的日子,那天他们被集体转业,兵改工的邹洪涛随大多数战友分到了深圳第一建筑公司,他们培植的城市,从此也成了他们的家场地点。
特区建成的第二个年头,蛇口就挂上的“韶光便是金钱,效率便是生命”广告牌,现在“邹洪涛们”成了这句广告语的践行者。邹洪涛答应了拍摄但也说了句“等活儿干完拍”,可没想一等,等到下午两点,“差点儿错过好的光芒”,周顺斌说道。
于是相片中32岁的邹洪涛身着蓝色笠衫,头顶太阳,站在两栋大厦之间,昂首挥臂,愉快地做了个“文革”期间自己学习的舞蹈动作,随后吹响的哨声连同相机咔嚓声一起定格,阳光下大厦拔地而起,邹洪涛结实的肌肉也展现出壮实的线条。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南海画了一个圈,但这个圈到底怎么画圆的,周顺斌镜头里的特区培植者给出了答案。《升》拿下了1984年第十三届全国拍照艺术金牌,周顺斌至今还记得有一位评委说,“《升》给了中国乃至天下不雅观察特区培植的一个窗口,它属于国家影象”。
周顺斌记得,当时刚接到部队要调到深圳参与培植的时,他根本就没听说过“深圳”,不知道究竟是在哪里。在舆图上费力半天,才在喷鼻香港的阁下找到一个叫“宝安县”的地方。而他当时所属部队在辽宁鞍山,与深圳相隔3000多公里,隔着大半个中国。
一声令下,在1981年的隆冬,周顺斌离开了生活10年之久的部队营盘,随基建工程兵先遣队南下来到深圳。历经5天4夜的闷罐火车,他们在一个小雨的清晨,抵达“沙场”,顾不上温差,来不及脱掉身上冬装,就得背着背包,提着行李急匆匆赶赴驻地搭建竹棚屋。
“杂草丛生,蚊虫肆虐,还到处都是尘土飞扬。”周顺斌以为当时的深圳就像一张白纸,没法跟原来部队所在的钢都鞍山比。“很荒漠,什么都没有,但一旦开动培植后,又像放鞭炮,这里在动土,那里在竣工。”全都是大工地,大家日昼夜夜、红红火火地在干。
随后的两年里,中心军委从全国各地调集了8个团共两万余名基建工程兵进驻深圳,参与培植。周顺斌的《大军南下》就拍摄了这样一个画面,在深圳火车北站,一个初冬的清晨,一列列军人从捆满小推车的货运车里跳下来,列队进站,他们戴着军帽,穿着棉裤棉衣,背后还背着折叠成方块的被褥,这个中就有邹洪涛。
《大军南下》
来深圳之前,周顺斌在部队一贯做着通讯员事情,虽然当兵时不满17岁,也只有初中文化,但他靠着在部队里的历练加上自学中文,早已能胜任笔墨宣扬事情。但来深圳后的一次实行接待中心电视台采访工程兵培植任务时,他的职业生涯被一句话击中,“除了笔墨,你们还可以给特区培植者留下些影像资料”,从此周顺斌便有了个新目标,学拍照。
实在那时候的周顺斌别说摸过摄影机,连看都很少瞥见。说干就干,认定了学拍照的周顺斌,怀着忐忑的心情向部队领导请示,该当给配相机用于记录部队在深圳经济特区的事情。令他没想到的是,部队立马托人在上海花了160块钱,买了一台双镜头的海鸥牌照相机回来。
“这是很奢侈的”周顺斌说,当时上午领到相机,下午就有拍摄任务。回忆起自己第一次拍照就碰上“临危受命”,周顺斌至今还心有余悸。“没办法!
不懂也只能硬着头皮顶上。”一吃完午饭的周顺斌顶着烈日匆忙骑上自行车,来到了新华书店,找了半天才找到一本拍照指南。
周顺斌拿手比划着,“四四方方”的那本“拍照指南”实在便是一个硬纸板做成的傻瓜式转盘,用于仿照相机光曝组合。“室内5.6的光圈加1\60秒快门,室外8-11的光圈加1\60秒快门”周顺斌一边心中默念着,一边用手一直地皮弄着转盘,按下快门,咔咔一卷12张的照片就完成了他第一次拍摄任务的义务。
可当周顺斌当心翼翼地拍完了,冲洗照片又成了新问题。80年代初的深圳城里只有一家拍黑白证件照的摄影馆,不仅质量不能担保,人多还要排队。不甘心的周顺斌自己买来了冲洗照片的显、定影粉,把部队食堂旁储粮仓库改造成暗房,照着书,开始一点点配制药水,从起初会涌现稻草似的干纹到后来完美无瑕地洗出照片,周顺斌用了不到两个月。
就像特区一栋栋高楼从无到有,拔地而起,周顺斌学拍照完备是半路出家,从零开始,但特区人独占的艰巨奋斗精神让他也拥有了“深圳速率”。
周顺斌总结自己走上拍照这条路就跟特区搞培植一样的思路,全靠引进“外资”,是学习对面喷鼻香港履历。80年代,拍照和这座新城一样,什么都刚在起步阶段,加上海内3年才举办一次全国拍照大赛,周顺斌除了珍惜每一次“喷鼻香港履历”的互换,大部分韶光还是自学。
和周顺斌一样,转业后大部分基建工程兵存在文化知识水平不足的短板。“每个人都是被时期年夜水所裹挟的一分子,我们来到深圳的两万多基建工程兵也不例外”。对付“文革”延误读书,之后当了兵的邹洪涛深有同感。
但当兵后,邹洪涛从没中断过文化知识的学习。和他一样的还有一大群战士,他们会在炎酷暑季边用凉水泡脚解暑,边坚持学习文化科学知识,也会在简陋竹子棚的图书室里挑灯夜读。1983年起,深圳政府为办理特区培植中人才转型的阵痛,开设了一批夜校补习班。
转业进入电视台后的周顺斌就参加了深圳市总工会举办的夜校拍照培训班,和他一起上夜校的人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人,多数是工程兵战友。邹洪涛也靠着自学,顺利在刚脱下军装后完成了军转工职业技能晋级考试。“市场化,就要不断精进自己本领”,让邹洪涛感到有差距的是一次公司引进的意大利塔吊,“他们能一次50米吊3吨,而我们只有30米吊1吨的”。
周顺斌《光腚娃》展示的便是当时部队转业后,一位母亲带着孩子上夜校的情景。这次拍摄给周顺斌带来很大震荡,他以为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看到了城市日月牙异的变革以及知识对自己事情、生活的主要性时,就抓紧统统机会去参加学习。“虽然起步晚,但是人的后劲大”,周顺斌说道。
《光腚娃》
退休后不愿放下摄像机的周顺斌,选择做了职业拍照师,有了更多韶光学习PS。但对付一个仅有初中文化又不太懂电脑的老人来说,困难程度可想而知。拿着老花镜对准基线一张张修复、扫描再到放大,每次拍摄后,周顺斌都要在电脑桌前忙活半天,直到深夜。
从胶片时期到数码时期,拍照已经进入大众化时期,周顺斌很欣慰,也会偶尔感慨。年近7旬的他,除了体力大不如前外,遇见需繁芜扫码进的景区,他也常常会由于“弄不好”导致拍摄操持泡汤。
周顺斌以为“老去”的困境无法逃脱,他全都接管,唯一让他惦记的是自己作品的“教诲代价”。这几年,原来该过着沉着祥和退休生活的他,反而愈发紧凑地参与到一些和基建工程兵干系的影展活动。除了看到老一代拓荒牛们前去返忆青春,周顺斌更乐意看到一位位中年家长带着自己孩子前来看展,讲述那段快被遗忘的历史。“争取再陪深圳扛个十年二十年”,周顺斌并没有打算放下摄影机,那些“疾”与“呼”都在他的作品里。
随着题材拍摄的广泛,如今周顺斌会逐步走出深圳这座城,走进了川、湘、云、贵,但每次最能给他抚慰的还是导游那句“来日诰日我们就要回到温暖的深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