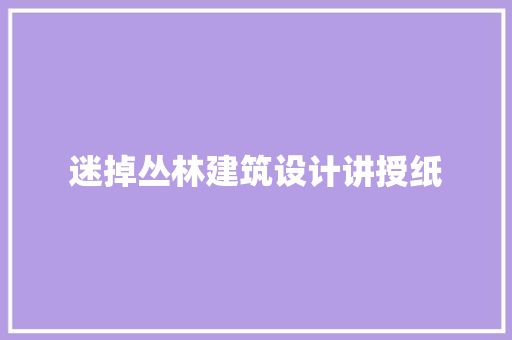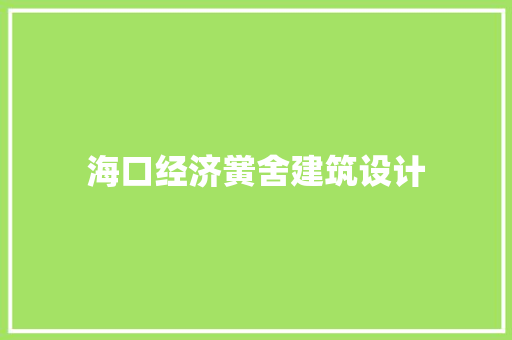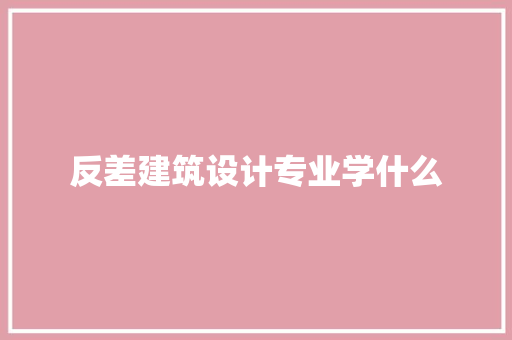考上初中百口人该当是高兴的,可看的出父母仿佛喜中有忧。缘故原由是初中的学费、书杂费加起来须要几十块钱,这让父母很难堪。六年前家中遭遇失火,烧的片瓦未留,一家五口人,去世的去世、伤的伤,加上我又到了入学年事,学校已经连续三年免除了我的学杂用度,现在不好意思再找老师哀求减免了。
哥哥看出了父母的苦处,于是找到基建队队长陈如义(我们叫表哥)说:“我弟弟考上了初中,立时要开学,要交25元学费和书杂费,父母为此愁的茶饭不进,无奈求队长你帮忙,给司帐安排一下,从我劳动工分中预借25块钱,办理我家燃眉之急,让我弟弟能够上学”。

陈队长的大儿子陈占比我大一岁,和我是同班同学又是好伙伴,陈队长对我们家的情形也是管窥蠡测,哥哥这棒劳力在他部下干活踏实卖力,令他很满意,再说表哥表弟的,毕竟多少还是有点亲情,于是,他即刻安排司帐李安(我的堂姐夫),想办法给我哥哥借支了20元。
当天晚上,李司帐就把20元钱送到我家,并让我哥哥在借据上签上名字。李司帐说,基建队财务上只有这20元流动资金了,还差5元钱,你们自己再想想办法吧。父亲接过这20元钱,对陈队长和李司帐的帮助解困表示非常感谢,想着孩子的学费大头有了,长出了一口气。
第二天,父亲丁宁我到三姐家看看能不能凑上几块钱,由于三姐家上个月母猪下了一窝猪仔,现已满月,该到卖猪仔的韶光了。
我到三姐家解释来意后,姐夫说是卖了四个猪仔,但两个是欠账,一个给了二升玉米,家里也只有10元钱了。我说只借5元就够了,姐姐说都拿上吧,途经大队药铺给咱娘买几块钱的止痛片。
初中和小学在同一校址,只是分小学老师、中学老师。就彷佛是铁路警察一样,各管一段,老师也是跟班走,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算是送走一批,然后再回到一年级吸收新生。
我带着一家人东借西凑的25元钱,再次来到学校,找到了门上贴着“初中一年级新生报到处”,交了学费,领取到书本作业,然后到月朔的班级教室(老戏楼改建)报到。
接待我们新生的是刚从县城调来的楚成佑老师,看上去年龄在50岁旁边。瘦瘦的身材,慈祥的面孔,三、七分发型,上身着蓝色四个口袋的中山装,下身配玄色登草绒裤(条绒),显的有文化、有精神。
楚老师先是把新生排队点名,然后按高低个头排好坐位,并就新学期把稳事变,学习操持和哀求等等做了开学强调,然后便是全校大肃清,要让新学期有个新面貌。
上初中后,课程、作业明显比小学要多,学生的学习压力有所增加。同班同学家庭状况也有很大差距,经济好点的同学穿着、用饭明显高于我们穷苦学生,仅从穿衣着装就能表示出,富余家庭的学生大多穿的都是在大队缝纫组量身定做的衣服,上衣左胸前都有一个小口袋,用来插钢笔用的,口袋上方用别针固定一个毛主席纪念章,显得很帅气、时尚。
他们中午带的干粮多数是白色(白面馍),最差的也是“白加黄”(白面和玉米面各半),还时时时有油饼、麻花之类的,老远都能闻到喷鼻香味,比较之下我的炊事就差太大了。
我冬季、夏季的服装仍旧以妈妈纺线织成的粗布为主,且都是由妈妈或者姐姐手工缝制的,上衣最多缝一个口袋,裤子大多还是传统的黑腿白裤腰大裆裤,腰带基本上都是布条代替。
生活上就更无法比较了,我依然是蒸红薯,烧红薯、红薯叶子烙馍,柿子面烙饼(成熟的柿子加入豆秸拌制、晒干、磨成面,味甜)。一样平常午饭吃干粮,我都是一个人单独开饭,反面他人共餐。可恨的是那些拿着白面馍、麻花、油饼子的同学总是在我面前晃荡,烦人!
初中时期也很抵牾,既要保持较好的学习成绩,为考高中打下坚实的根本,又要有足够的物质根本做保障。毕竟买学习资料、笔墨纸砚,钢笔、羊毫等的学习用具,都须要有一定的经济支柱,可我的家庭状况始终没有明显提高,或者说变革不大。父母有压力,动不动便是“咱家穷得很,不上学了,在家放牛、干家务、挣工分吧”。
为了不放弃学业,不再放牛,要想连续上学,就必须学会自己挣钱养活自已,至少在购置学习用品上不问父母要钱,减轻家中经济包袱,这才是能否连续上学的关键。
以是,对付我,每周一至周五是学习韶光,周六周日便是抓经济的最佳时节。我多数是和同学陈占、李有、范双有等一块上山拾像壳、像籽,摘孔雀、挖血参、秸更、苍术(中药),采摘回来按照哀求加工凉晒好,再拿到大队医药、当地货部出售,换取块儿八角作为当时紧张的经济来源。
卖钱多一点的是卖窑木,这要看自己的力量大小。直径粗些、直些、长些的,一根能卖一块八到两块钱,但太累。木头又细、又波折、又短的一根也便是不超过一块五毛钱,就这样以质论价,多劳多得调动着每个赢利者的积极性。
这个钱既不好赚,风险也大,每每都是起五更爬半夜的。由于都是偷着干的,一但被生产队创造,这属于盗伐林木,是要挨批的。以是必须赶在天亮前把木头背到木材站内,才算放心,待事情职员量好直径、是非付款后,心里一块石头才彻底放下。然后拿着钱到智朝饭店饱餐一下,买一碗粉汤和半个锅盔,共花二两粮票两毛五分钱,哪个喷鼻香啊一辈子都忘不了。
山区挣钱的道路不多,平时除了靠出笨力挣几个毛毛钱,再便是每年秋季核桃下来,是家家户户愿望的进钱期间。核桃同样因此质论价,卖到大队当地货部,三毛至五毛不等,有些家还要留一点过年给孩子吃,或者给县城里的亲戚、朋友送点,这是山区的特产,城里人很奇异。
我家祖祖辈辈都是山里人,和城里无缘,没什么亲戚。以是不考虑送人,但会留一点到鲁山县归北石(军工厂)去换些衣服、鞋帽等物品。那个工厂都是正式工人,有钱人多,每每把穿旧了的事情服、劳保鞋、手套、棉帽等用来换核桃。我们也挑一挑,看看哪些能穿、能用,然后与他们讨价还价,用最少10个核桃,最多50个核桃不等,换取不同的物品。用现在话说便是学着做生意做生意了。
也便是在那里,我们第一次见到卖冰棍的,是一个自行车后坐上放着一个用棉被包着的木箱,里面用各种彩纸包着一个个长方形,一头露着一节木把的东西。热天看到吃的人很多,不知道啥味,很想尝尝,问多少钱一个,卖冰棍的大爷回答:”二分钱一个,也可以用核桃兑换”。我和范双有商量,每人换两个尝尝,实在也就像俺家冬天房檐上冻的冰柱一样,只不过有点甜味罢了,这是范双有和我第一次吃冰棍。
这次去兵工厂拿核桃换服装鞋帽,是我和范双有商量已久的一次操持。实在,把握机遇,顺手牵羊,每人能带回一根两米长、大母指粗的无缝钢管是此行的主要目的。
我俩在换鞋帽、吃冰棍的同时就把稳不雅观察周围情形,锁定目标(钢管)。在一个车间院子里搭建的大略单纯棚架上,创造了几根最空想的“宝贝”,棚子下面是一个用来修车防雨、防晒的专用场地,园地中间挖有一个宽约一米、长两米多、深两米多,砖砌起来的地坑,用来维修、保养汽车底盘,操作方便。
白天人多眼杂,加上还有一台车正在掩护保养,不利于下手,我俩决定在夜深人静时行动。
做了一天“买卖”,却没钱买饭吃,我俩除了用核桃换的两个冰棍和一个碗大的西瓜充饥外,其它什么也没吃,但由于想着晚上有“事情”要干,以是精力还是很充足的。
锁定了目标后,我们就盼着天快点黑,我俩背着换来的几件破衣服和两双旧鞋子,在一个南北大桥上来回转悠。不一会桥上的路灯亮了,天也逐渐黑了,心想我们该“上班”了。
为了保险起见,我们决定还是多等一会再动手。于是躲在不远处不雅观察到车间宿舍里一盏盏灯都息了,我们才按照白天踩好的点开始干起来。
说真的,这种活一次没干过,实在是履历不敷,加上特殊害怕,闻风丧胆,也是判断有误,业务不闇练,刚捉住一根钢管往回一抽,另一头因失落去支撑,钢管落空,只听“咣当”一声钢管落地了。
附近宿舍工人听到声音,冲出门外朝着我俩大声喊:“谁!
干什么的”?接着打开了院子的路灯,看到地上的钢管,彷佛明白了这俩小子是干什么得了,便扯着嗓子大声吼叫“抓贼呀,有小偷啦!
”
瞬间,各宿舍的工人、干部都出来了,把我俩围在中间,我的乖乖,就这样我俩被活捉了。有的说要报公安局,有的说交给派出所,这时有个年事稍大一点的人(彷佛是车间主任)对我们进行逐一盘考,先问年事,又问住址,再问偷这钢管是干啥用?我们诚笃交待了家乡、年事,说要这个钢管紧张是做个吹火筒,吹火做饭用。
车间主任听了我们的坦白交待,又看看我们用核桃换的破衣烂衫,多少有点同情,决定不送我们去公安派出所,就在他车间内部处理,一听说不送公安,我俩非常感谢,并表示服从他所说的内部处理。
主任叫来一个修理工,并提来一个水桶,把我俩叫到修车的地坑边说:“看你俩认罪态度较好,本主任决定从轻惩罚,今晚上你俩把这地坑里的污水清理干净,倒到指定位置,不许偷
我俩接管任务后,便开始干起来。好在这不是厕所的污水,但半坑全是机油、黑油和洗车的稠浊脏水,我俩撸起裤子,一个在坑上,一个在坑下,一桶接一桶轮翻作战,直到东方发白,才算完成“组织上交给的任务”,经主任验收合格后,我俩迈着怠倦不堪的步伐,迎着初生的太阳,朝着回家的方向挺进……
初中三年有很多事,影象忧新。学校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宣扬队”,这是我的强项。卖力编排的导演是张凤仙老师(按辈分是我侄儿)和我七哥张朝明老师,演唱曲目以自编自演的“对口词”、“三句半”和样板戏选段、选场为主。
我主演的曲目有“老俩口学毛选”(和王双凤搭挡),我扮老头他演老婆,经由扮装打扮后,我们俩还真像那么会事。道具是两把椅子一张桌,两本《毛泽东选集》。
幕布拉开,我俩在音乐声中开始唱道:“收了工,吃罢了饭,老两口儿坐床前,咱们俩个学毛选“
”老头目“
”哎“
“老婆子”
”哎“
”你看咱们学哪篇“?
”我看咱就学这篇“
”阶级仇敌总想着来变天,咱们贫下中农一定要擦亮眼……”
这属于当时耳熟能响的地方小调,彷佛全首都在学唱,很受欢迎。
后来,县剧团下乡演出一部反响地主压迫穷汉,穷汉翻身斗地主的当代戏《收租院》,很有教诲意义。大队长刘长有和支书马邦俊到学校与校长商量,以学校现有演员为主,大队声援为附,并给于服装、道具的经济帮助,把这部戏排练出来,参加公社春节汇演。校长当即表态:有大队的人力、财力、物力的支持,我们有信心有决心完成任务。
这部戏里我是男一号,扮演一个白发瞎子老翁,女一号是双凤,扮演我的孙女,我俩在台上多数因此苍桑、悲哀的表情和演出呈现给不雅观众。
我在“孙女”的牵扶下出场,开唱:“手拿一张卖身文,不由老汉疼在心,刘家有地千万倾,咱穷汉没有半毫分……”
这部戏拍成后,首先是在大队公演,约请大队干部和不雅观众同时不雅观看,以便听取社员群众对戏的评价和见地,整场戏用时一小时四十分钟,期间,响起多次耐久不息的掌声。从干部、不雅观众和师生的讴歌声中,可以看出此剧的上演如同一道文艺大餐、精神食粮受到广大群众的喜好。
为了拍戏、学习两不误,学校哀求参加节目演出的学生必须住校,白天上课,晚上拍戏,也挺辛劳的。
与学校一墙之隔的邻居是住户范章定,他家的晒棚上堆放着好多柿子,品种有牛心、艳国红、和京面,味道真叫个甜。白天不雅观察好地形,晚上排完节目,夜深人静时,就爬上院墙,小心翼翼的挑选几个自己爱吃的回去充饥。结果还是做贼心虚,业务不熟,一脚踩空险些摔下。晒棚下面是范家寝室窗户,这一脚响声惊醒了房中主人,他朝着柿子棚上大喊一声:“谁!
干什么的?”吓得我是连滚带爬跳下柿棚。
1970年冬季征兵事情开始,哥哥是征集工具,哥哥和今年夜队东庄村落周胡兰一同参加体检,俩人身体均康健合格。经由祖宗八代的政治、社会关系审核,他俩符合条件,阳历年前换上军服,在大队送兵大会上披红戴花作了表态发言后,在锣鼓声和村落民们的护送下哥哥踏上从军的征程。
哥哥当兵走时,母亲重病,母亲拉住哥哥的手说:“你放心去吧,甭担心我的病,我是烈火炼成的。你也老大不小了,出去当个兵,咱家便是军属户,大概能给你说个媳妇,改变人生,当兵是个很好的出路……”
我和哥哥相差6岁,兄弟俩感情很好,我每天象个跟屁虫,哥哥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这次哥哥验上兵要出远门,我更是难舍难分,形影相随,白天陪他去告别亲戚,晚上还要钻到他的被窝里,特殊是哥哥换上军装后,我跟在他身后心里美的屁巅屁巅。
按大队民兵营长的哀求,一个军属家中可以去一个亲人送行到公社,由于家中母亲卧病在床,父亲要照顾母亲无法脱身,以是我来承担送兵任务。
到了乡里,乡武装部长把全体新兵凑集在一起,列队点名后向接兵首上进行了交卸。之后新兵便上了一辆“老黑头”卡车,临上车前,哥哥搂着我,眼泪巴巴地叮嘱:“兄弟呀,哥哥本日参军是我20年的欲望,哥心里很高兴,唯一放心不下的是咱娘重病在床,生活不能自理,父亲年迈,你又年幼,为给娘治病还欠下那么多债务,父亲既要照顾母亲又要挣工分,你一定要好好上学,还要帮家里干些家务,给娘请医买药、端茶喂饭就全靠你了,你年事又小,哥哥很不忍心,我最不放心的便是娘的病,不知能否等到我退伍回来”。说到这哥哥再也说不下去了,他把我牢牢地搂在怀里,泪水点在了我的脸上。
哥哥走后,娘的病很不稳定,时好时坏,请年夜夫看看便是打个屁股小针,再给几粒去痛片,并给父亲讲该准备后事了。正月十五过后,母亲险些就措辞不清、茶水不进,坚持到正月十八,娘终于走完了她的生平,临终前拉着父亲和我的手,断断续续喊着哥哥的名字“长顺、长顺……”
娘去世,村落里来了一些亲戚和邻居,还有大队民兵营长,营长代表大队向军人母亲逝世表示哀悼,对父亲和我表示慰问,同时安排生产队干部帮助我家办理母亲后事。
由于家中贫穷,母亲后事办的再大略不过,就差没用芦席卷了。家门口有一棵直经不到30公分的泡桐树,队长安排木匠李根有(我的表哥),将此树伐倒,锯成2公分半厚木板,用钉子钉成一个木匣子。表嫂和二姐把母亲平时穿的那几件带着补丁的旧衣服给母亲穿上后就装棺起灵,打墓坑的也是队上派来的人,母亲就在我家住房墙头入土为安了。
母亲丧事办后,有亲戚说给哥哥发个电报,或写封信把妈妈去世的见告哥哥一下,免得往后哥哥生气。当时我一个小孩也不知咋办,还是听父亲的吧,父亲长叹一声说:“孩子刚到部队才两个月韶光,又远在四川,三个月的新兵演习都没结束,给他讲了只能给孩子带来悲痛,会使他分心、伤心,影响军训,还是先不见告他吧”。
后来再给哥哥写信,就都是这样一封封“娘的病情有所好转”、“父亲的身子骨壮实”、“我的学习进步很大”等“安然”家书。这些”善意的谎话“一贯持续了三年。
哥哥是个屯子兵,能吃苦爱研讨,学文化、学技能苦练基本功。三年荣立两次三等功,第二年就加入了党组织,我家也常常收到哥哥部队寄来的立功喜报,现在想起来哥哥所取得的成绩,与我和父亲的“保密”事情有一定关系。
三年后的春节前夕,哥哥来信说按部队规定,当兵满三年可以探亲,他已请好探亲假,春节前回来同百口过个团圆年。并说连来带去有40天韶光,听到这个,我和父亲又喜又忧,喜的是愿望三年的父子、兄弟就要见面了,忧的是哥哥回来见不到母亲怎么办?如何面对这个现实?
说话间尾月二十三小年到了,哥哥探亲也到家了,未进门哥哥就放声痛哭,嘴里一口一个娘啊娘的叫着“娘啊,你怎么不等我回来呀?我给你买了很多好吃的,还有入口的止痛片,我归心似箭赶回来看你,你在哪呀?娘啊……”
原来哥哥刚下车就遇上了我家后屋表婶,表婶把我娘去世的见告了他,“你当兵走不到三个月,你娘就去世了,你爹怕你分心、影响事情一贯瞒着你”。
现在想起来还真有些对不住哥哥,不该骗他那么永劫光。此时此刻哥哥又像三年前那样把我牢牢地搂在怀里,泪水再次滴在我的脸上。
作者简介:
张朝利,男,汉族,河南省汝阳县人,1956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1978年3月参军从军,服兵役于新疆军区陆军第八师(36141部队),1983年退伍,转业至新疆生产培植兵团第七师一二四团事情。先后担当连长、布告、社区主任等职。2018年8月在新疆乌苏县124团果喷鼻香里社区支部布告岗位退休,现居新疆乌鲁木齐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