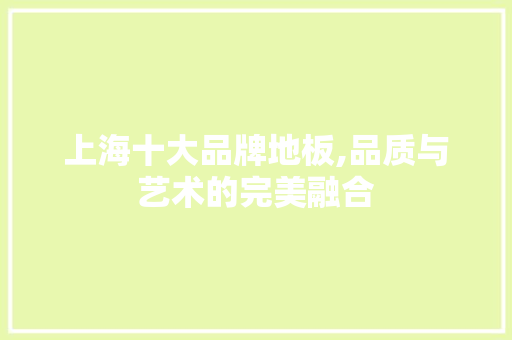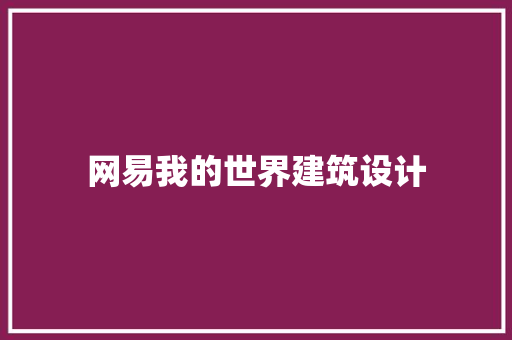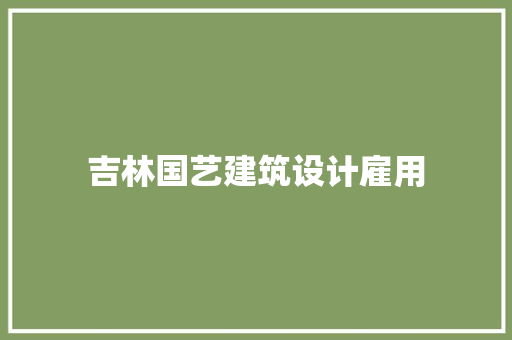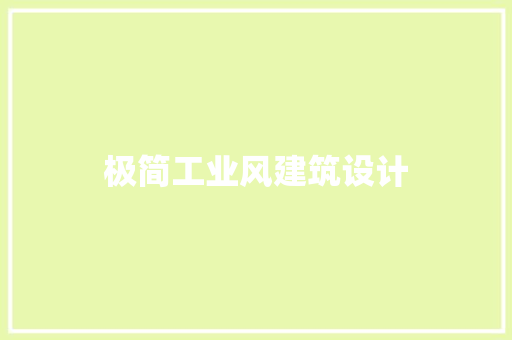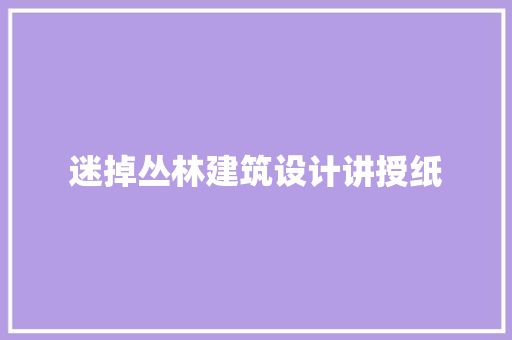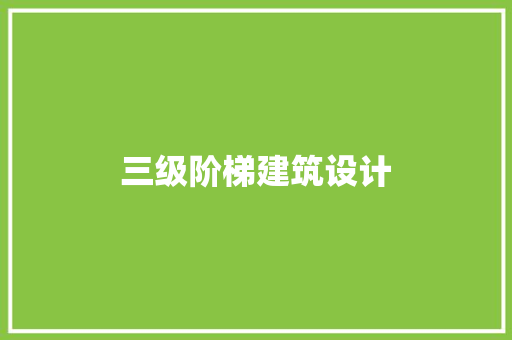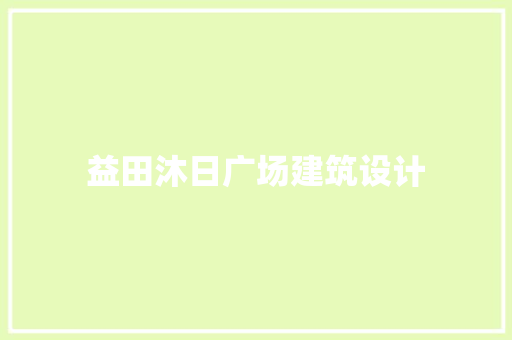“中心的柱子改成带有许愿池的纪念碑,背后刻有建筑师的小说片段。环绕着它,有台阶,柱廊,带壁炉的舞台,作为阳台的玻璃包厢。可以有鲜花,咖啡,一点酒,爱情,八卦,宠物,脱口秀,溘然一曲阿尔罕布拉宫的回顾以及即兴的探戈。繁盛热闹繁荣,欢畅以及隐蔽的妒忌。”俞挺谈上海历史博物馆满坡栗咖啡馆
“影象既不是短暂易散的云雾,也不是干爽的透明,而是烧焦的生灵在城市表面结成的痂,是浸透了不再流动的生命液体的海绵,是过去、现在与未来稠浊而成的果酱。” 这是伊塔洛·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的沉思,放在上海最有名的建筑师俞挺的语境中,它不可避免地唤起了罗兰·巴特对意义深入探索的回顾:上海不仅仅是一个城市;它是一个双刃的象征,一个开放的容器供无尽的解读,又是一个富含建筑、美食、不雅观念和蔼象的实体。这是一个不断重新定义自己,走出自身阴影的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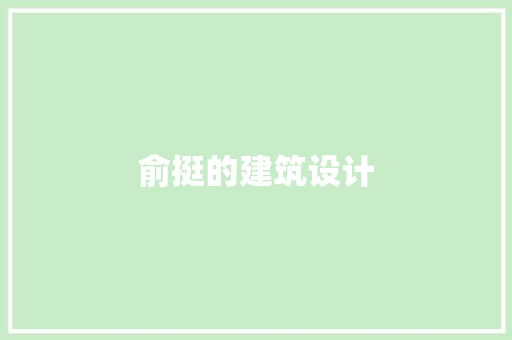
上海书城
新的上海书城是对这一理念的致敬。它那巨大的玻璃立面吸引着每一个路人的目光,阳光在其上演奏,照亮了里面的每一个角落。这个地方不仅仅关于书本;它是一个艺术的避风港,充满活力的地毯勾引你沿着蜿蜒的楼梯向上,每一层都是更大故事中的新篇章。只管它一开业就引起了相称大的轰动及争议,但这家书店证明了俞挺对“地域特性”这一观点的奥妙把握,他利用这一术语超越了纯挚的地理观点,捕捉到了一个地方的精神和上海的有形及无形实质。
上海书城内的空间
保罗·戈德伯格将建筑与其环境之间的对话比作一首小诗,俞挺也以对本土传统和遗产的敏感度来打造他的建筑。这一不雅观点支撑了他的设计,这些设计深受他对付社会学的深入理解——将建筑视为一种实践,不仅考虑它自身具象的美学表现,同时还十分看重与城市的互动、契合人的需求和社会的变迁。这种双向运动是深刻的,建筑物在俞挺的创作中,既是梦想的表示者,也是功能的实现者。
上海历史博物馆内的满坡栗咖啡馆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俞挺“创新二元性” 的缩影。它回溯到上海咖啡馆作为社交中央的起源,并试图将那失落去的社交性重新引入当代城市构造。通过将内部转变为反响欧洲广场的样式,俞挺供应了对公共空间的重新诠释,既尊重城市的社交遗产,又战胜了历史保护的限定。
上海历史博物馆内的满坡栗咖啡馆
“我并不想把上海性和生活性固化成一个可见的化石,我希望把它抽象出一个可以为非上海人,非中国人都可以接管或者理解或与之感叹的东西。”俞挺说。
“2023年,我重新访问微光之宅,非常感谢业主保持的如此之好,一如4年前初建成。在外人看来,微光之宅是我设计作品中不范例的一个案例,但却是符合我这个双子座主要的特色,在鼓噪中总能为自己保留一个不为人所知的独处。在这个业主和我达成共识的独处之中,我展现了我真实的另一壁,轻,节制,有些犹豫,低吟浅唱,骄傲也有些谦卑,想想会微微一笑,以长舒一口气的办法用墨色微微渲染了一个复苏但沉默的生活在闹市中得意的态度。我赞颂这不完美的天下,还有,迷途知返的,柔光。”俞挺说上海市中央200平方米老房改造“微光之宅”
按俞挺自己的话讲,“每个人都是自己的镶嵌品”。每个人的经历造就了自己,再与新的经历一起连续改变未来的自己。
曾经在上海东北部那个充满张力的区域度过了童年少年,在清华园度过了青年时期,又在伦敦、意大利游历多时,俞挺被地中海的强烈阳光所打动,它从天空涌向大地。光像雕刻一样,“打穿”了很厚重的、坚固的万神殿建筑,这种强大的觉得让俞挺难以忘怀。“我瞬间感到光的力量,光可以冲破统统阻碍,可以激发生命的力量。”他当时溘然想到墨客佩索阿的一句诗:我们活过的霎时,前后皆是暗夜。那一刻,激起了他对人生繁芜的情绪,也重新塑造了他对建筑师创新的理解。
在这里,俞挺所理解的创新是双重的。一方面是“刚性创新”——想想勒·柯布西耶的作品——一边把一半的发达国家的人装进了钢和玻璃的盒子里,一边极大改变了艺术、设计的审美面貌、乃至生活办法。另一壁是个人创新,对已知知识进行奇妙的改造,正如安藤忠雄在混凝土中所做的那样。
然而,这两种创新形式都须要“建筑化”——一种转变,考虑了方案、法规和建筑的实际细节。“从地铁站出来一起步辇儿,穿过老旧但干净的街道,来到里弄的铁门外,还没有看到任何不同的迹象。倒是街区本身,与我多年前生活的上海老城区比较已经有了些许变革,特殊是星星点点几栋更新过的建筑,在尺度、色彩和细节上,都表现出与街区的折衷,又不失落当代感和设计感,看得出来上海在历史街区更新上是下了功夫的。更招人喜好的是站满长街两侧的梧桐树,把机动车道变得优柔。没有灯红酒绿,没有熙熙攘攘,街道的色彩在清淡中略带温暖。只有密密麻麻不肯入地的电线、变压器以及电线杆子十分惹眼,但也不算讨厌,倒是有点和历史街区的繁芜性与历史感相得益彰的意思。”
这是4年以前,俞挺走向那幢位于市中央200平米的老宅前,记录下来的细微感想熏染。这显然是个人创新——对已知知识进行奇妙的改造的一次极佳佐证。
微光之宅内部
在这座桑沧老城区内并不算起眼的小楼中,俞挺实践着建筑师授予空间生命的义务。正是这种义务感,俞挺认为是他事情中最突出的特色,尤其是在如前所说的上海这样一个充满活力的具有“能指”和“所指”交织彼此的城市,他希望的不是将这座城市的风格固化为静态的视觉艺术品,而是将其充满活气的生活转化为一种超越文化障碍的措辞。
这种追求与罗兰·巴特的哲学探索和量子力学的繁芜性相同等,这两者都深深地影响了俞挺的设计方法。巴特对文学内涵的深入探索与俞挺在建筑空间中探求叙事线索的追求相呼应。就像量子物理学颠覆了我们对宇宙的确定性预期一样,俞挺不断地寻衅着传统设计的确定性限定。
“我决定在徐家汇书院建立一个来源于中国传统的子奁盒的‘中国套盒’构造。任何室内设计都是建筑设计,去积极触动城市。徐家汇书院是个区级图书馆,不算严格意义的研习型图书馆。它更面对社区居民,有一定的社交性。以是徐家汇书院不应该是个封闭内向型的文化场所,它更该当是开放的,不仅须要吸引读者,更须要吸引原来不怎么阅读的人。”俞挺说徐家汇书院
在徐家汇书院内部,俞挺进行了一次变革。他将原有的书院建筑保留,但在其内部增加了一个全新的空间。这个空间像一个中国套盒,由一个个的小盒子组成,每个小盒子都有不同的功能和风格。有的是阅读室,有的是咖啡厅,有的是展览馆,有的是事情室,有的是寝室,有的是花园。这些小盒子可以自由组合,形成一个个的空间单元,每个空间单元都有自己的主题和蔼氛。这里有古典的,有当代的,有中式的,有西式的,有文艺的,有商务的,有安静的,有热闹的。这里是一个既具有上海性又能承载多元性的空间,是一个既适宜阅读又能促进互换的空间,是一个既有历史感又能展现创意的空间。这个案例,让我们更深入地区理解俞挺是如何通过创新将建筑视为办理问题的媒介的。他阐明道:“我认为建筑是一种社会学的实践,它不仅要考虑空间的形式,更要考虑空间的功能,空间的功能又要考虑人的需求,人的需求又要考虑社会的变革。”他将这种思维利用到自己的设计中,通过对空间的重新定义,办理了一系列的问题,个中包括如何利用有限的空间,如何知足多样的需求,如何平衡历史与未来,如何引发创意与学习。
这就意味着,对付俞挺而言,建筑设计的创新既是宏伟的“观点”,也是细致的“详细”。建筑物所要承担的职责,既隐喻着承载城市生命的魔幻,又陈述了芸芸个体日常思久的现实。正是这种双面性使得俞挺的作品在其“网络红人” 外表下抱有年夜志壮志,在实在际主义底色下进行超现实主义的实验——它不仅表示了功能,也构建了梦想。
俞挺的问题办理方法不仅展示了他的社会学洞察力,还反响了他对建筑哲学的寻思。让我们明确一点——他不是一个为了形式而坚持形式的建筑师。他更像是一个创造办理方案的工程师:“我设计是为理解决问题,而不但是为了制造好看的东西。”这让人们在空间中感想熏染到了问题的办理,并在问题中感想熏染到了空间的创造。
不难明得,就这种双重性而言,每个建筑师都在梦想着他们的“埃菲尔铁塔” 时候——当埃菲尔把他的铁塔算作是一件严明的、合理的、有用的东西,与此同时,人们却还给它一个伟大的、奇异的梦想,这个梦想极其自然地达到了非理性的边缘。
当然,将俞挺的作品与埃菲尔铁塔相提并论还是过分了,但他那种“超现实主义”的等待确实值得尊敬。这种等待和行动可能会引起更多的辩论。与音乐、文学和美术这些更为“飘渺”的艺术形式比较,建筑可能看起来“太随意马虎”了,由于它太依赖于功能。但纵然与看似“随意马虎”的电影比较,不雅观众仍会为一个故事踏实的电影欢呼,纵然它并未实现他们所有的梦想;然而,没有人会仅仅由于建筑物正常运行就给建筑师起立鼓掌。勤奋的建筑师真正的难题来自于须要在崇高空间所扮演的舒适角色中添加大量的理性力量。否则,他们可能就会创造自己身处"大众年夜众舆论的热椅上。
但所有这些鼓噪险些不会触及俞挺情绪的表面,更不用说动摇他的信念了。由于他是那种不会被小事所困扰的建筑师,绝不畏惧地等待着将所有一寸一寸噜苏的空间,末了汇聚成韶光的年夜水。“就像《我的天下》里所展示的那样,用最大略的办法去构筑繁芜的天下,从根本开始,层层叠加,创造出丰富的画卷。这便是一个繁芜系统的成长过程,杜绝了建筑师无法谢绝的、伟大叙事的诱惑。” 俞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