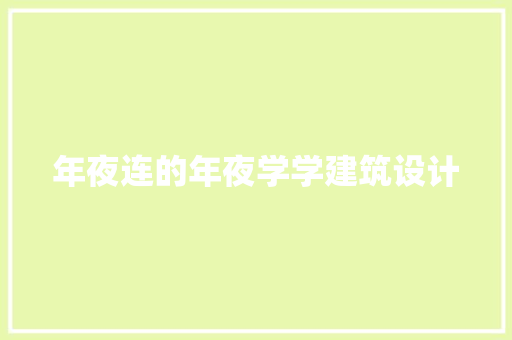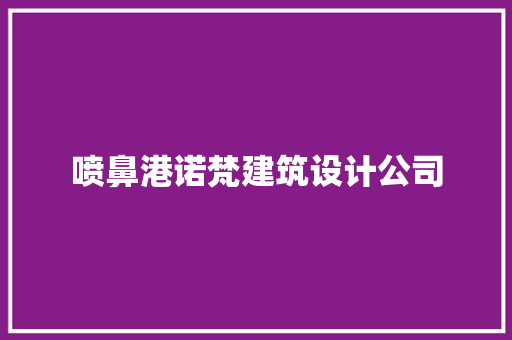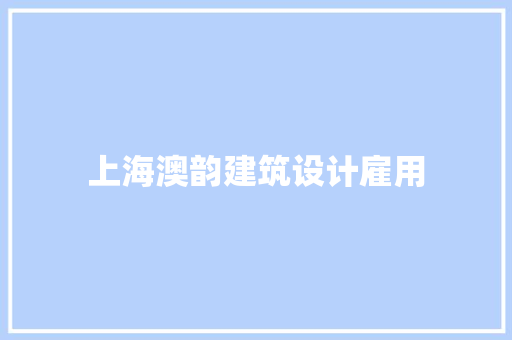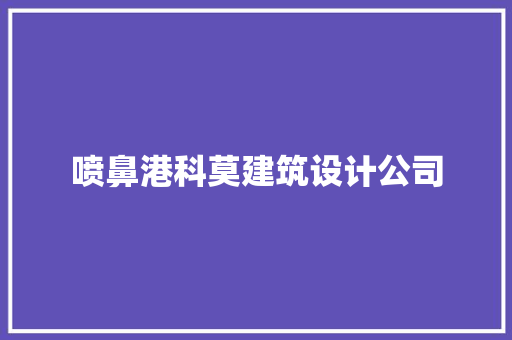他用艺术拯救生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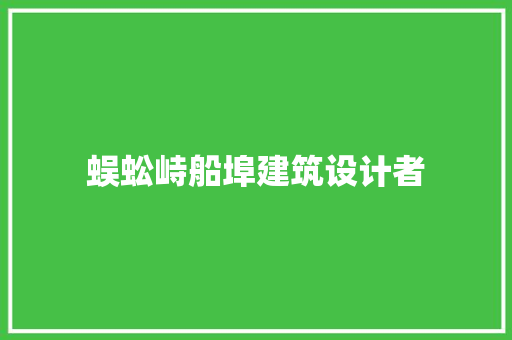
10年前,新华社在全国推出“十位共和国同龄人”,朱仁民是浙江省唯一的代表,也是全国唯一的艺术家代表。
当时,《光明日报》头版头条这样先容:“他是沃土上的一棵艺术大树”。
从出身名门的画家到“中国生态修复之父”,朱仁民弯曲盘错的人生像一部厚厚的长篇小说,也是共和国的一个缩影。
我的父母
1949年我出生在浙江宁海。在世人眼里,我的家族风光无限,成长在这个艺术世家,我的人生必定鲜衣美食、一马平川。
实在不然。 3岁那年,父亲被发配到普陀沈家门。拎着一只破皮箱,父母带着我和哥哥搬家海岛,举目无亲。
母亲读过五年小学,还是跳班和旁听的,大家知道她是潘天寿的女儿,让她在普陀中学总务处事情,兼教美术。母亲睿智且好学,她自费跑到外公担当院长的浙江美术学院学习,没用学校一分钱,自编了美术传授教化课程。
父亲是个大才,擅英语,通文学,但他没资格事情。家里太穷,没一分钱收入,5口人全靠母亲每月30来块的人为养活。
没有事情的父亲在充满鱼腥味的渔镇东头——荷叶湾渔业队开起了文化补习班,每天晚上开课。石屋梁上挂了几盏汽油灯,课桌是渔民家里的各种木头小方凳、八仙桌。我也似懂非懂地混在里面听他上课,没听几句瞌睡儿虫爬上来,每次都不晓得父亲是什么时候抱我回的家。当父亲将这个班办成了“沈家门中学”时,他被革职了。
我的学历
8岁那年,我报名上了学。学校在戚家湾,一排毛石底白粉墙,原来是台州同乡会老屋。学习小组在我家,每天下午卸落门板,一头搁在板凳,一头搁在水缸,四五个孩子趴在门板上做作业。小学五年级,我已经捧着父亲的字典通读了中国四大名著。
从有影象开始,我就在画画,还以为全中国孩子的外公都是画画的。 10岁那年,舟山行署举办第一次美展,我稀里糊涂获了一等奖,行署专员王家恒奖给我一本书又给学校写信,说“培养出冒尖人才来了”,学校给了我很高的名誉,也是一项“特等待遇”——上课可以画画。虽然从来没有上吊刺股、凿壁偷光之类的业绩,但好几次在文化部、中国美协举办的高等别国展中入选获奖,画画可能是我与生俱来的本事吧。
家里没吃的,我想劫富济贫,总以为梁山豪杰的后代还在梁山。13岁那年暑假,我按连环画上的林冲造型制作了红缨枪、酒葫芦,肩上一扛瞒着家里找梁山去了,当然,没几天哇哇哭哭被遣送回来,家里、学校居然都没惩罚我。
15岁初中毕业,我报考浙江美院附中,华东地区考了第一名,但因父亲的问题落了榜,那时外公还当着浙江美院的第一把手呢。我剧烈意识到自己原来低人一等,心里很伤心。
为减轻母亲包袱,我初中就开始在这个岛上打工:晒鲞、打铁、教书、画画、出海捕鱼、当拍浮池救生员,一贯到舞台美术设计、文化馆美术干部……
一缕阳光
1978年,全国农业学大寨,我犹豫满志租了个拍浮池,用拖把开始创作300米×3米的超巨幅作品《大道海天篇》。我都不知道这是中国第一幅水墨行为作品,墨光飞溅地弄到1980年底,裱画时从脚手架上摔下,年夜夫断言:“再也站不起来了!
”
天塌下来一样。
病瘫几年住不起几块钱的农人房,朋友背我到普陀山上倒闭的破庙隐修庵居住。断壁残垣、老鼠松鼠,梁上还横卧着一条大蛇,学生递我一把菜刀,我盯着蛇鼠,时候准备搏斗。
我家沉重的黑门被时期的飓风呜呜地吹开一道缝隙,漏进一缕阳光——家里平反了,母亲带领姐弟几个将现值百亿的外公作品全部无偿捐给了国家,国家给了25万元奖金,那时这些奖金能买半条街的门面房,母亲姐弟又将25万也全捐了,设立基金会为中国美院、树人大学等穷苦学生供应帮助。母亲握着捐款具名单问我:“你看行吗?”我瘫在床上,连最少的生活费都没有。
外公去世前说过,他的作品属于民族的。江泽民几次接见百口,我家被赞誉为“爱国的、高尚的、无私的”“文革后第一次精神文明样板”,上了报纸头版头条。
我的腿爬爬弄弄居然奇迹般地规复了知觉。我拄杖下山,揣着借的300元公民币开始闯荡天下。
我云游欧美,辗转十几个国家,打工、讲课、办展,学习当时海内尚未兴起的景不雅观设计生态修复,我感到这个时期艺术该当有其革命性的变革,艺术家肩上该当有新的任务。
常常有人问起,你怎么会用30多年的韶光、上百万笔墨的著作、近千亿的工程投入量来做生态修复奇迹?大概由于从个人家里都是类似的人:外公潘天寿是创办中国美术学院的当代艺术泰斗,舅舅潘公凯是中心美院、中国美院两院院长,表弟是著名建筑师,北京西客站、中国美院南山路本部所有建筑都是他设计的。全体家族热爱艺术,喜好哲学,为祖国、为天地立命的不雅观念根深蒂固。
我的艺术转型可能与家族、个性和当时的教诲环境都有一定关系。我自幼从书里知道屈原、岳飞、林则徐、袁崇焕等民族英雄,对这些英雄的崇拜超过任何人,那个时期的人受的是“生当作人杰,去世亦为鬼雄”“留取赤心照汗青”“先天下之忧而忧”“向雷锋叔叔学习”之类为祖国民族立命的品质熏陶。
拯救生态
这个时期不缺金钱,我也不屑于架上纸上的涂鸦和唾手可得的辉煌。城市缺水、河流污染、湿地消逝、雪山融雪……我看到生态修复对人类的意义,我想用自己对艺术天生的敏感和创造力,以它山之石建立我生态修复学科的堡垒。
一个崭新的学科“人类生态修复学”由此而生。建立“心灵生态、自然生态、艺术生态”的理论与实践,成为我人生的奋斗宗旨。
这是一个乌托邦式的万里征途,也是一个唐吉诃德式的英雄主义行为,我必须在百万字的论点、论据中,得到无可辩驳的论证。
我开始探求被人类毁坏过的荒蛮地貌,将生态、GDP、就业率、文化艺术取得齐头并进的实践效果,达到理论和实践的完全性。
就像我1992年独自摇船去的莲花岛,当时叫“菜花山”,它像一尊浮在莲花洋上的不雅观音卧佛。1996年,我自费买下该岛的利用权,没路、没电、没水、没码头、没航线,20余年的奋战,几千万元的投入,不管如何困难困苦,我硬是为家乡留下一个永久免费的生态经典作品——普陀海洋雕塑公园。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天下粮农组织以及天下主要名校,它的存在掀起过听者一阵阵的震荡。
也像朱家尖蜈蚣峙码头那巨大的裸崖改造一样,我用最少的投入,以舟山海岛民居的元素建立了世上独占的地标性建筑。有人说它像布达拉宫,那是对舟山渔岛民居至高无上的赞赏,无论是东极、白沙还是浪岗,大海上天人合一的建筑都是这样,它成为舟隐士文文化的一个主要载体。
这30多年,我跑的多是荒蛮之地,荒岛、荒沙、荒滩、裸崖、矿坑……所有范例地貌全都干了一遍,用近千亿的生态修复工程量来证明我的理论。
永无止境
我多次在联合国总部、天下粮农组织演讲,我在斯坦福大学、伯克利大学、纽约大学、罗马艺术学院以及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心美术学院宣扬“用艺术拯救生态”的理念,所到之处,掌声热烈,这样的人文精神和艺术手腕让听者深受震荡。
意大利国家美术家协会主席Gabriele Altobelli评价:“朱仁民师长西席‘用艺术拯救生态’和‘心灵生态、自然生态、艺术生态’的理论和实践,让我们看到文艺复兴以来艺术和创作办法的更高层次,他是中国的达芬奇。”
在粮农组织总部举办的艺术展上,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达席尔瓦师长西席动情地说:“原来艺术可以如此的辽阔!
我们会将朱仁民的作品永久悬挂在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大厦内。”
国际IEED生态环境设计同盟在米兰世博会中国馆中付与我“中国生态修复之父”名誉称号。
……
我以为很替祖国长脸。
一个原来画几张画的人,我会做什么?我该怎么做?我惊不了天动不了地,我做不了民族脊梁,做根鱼刺也好。
我有幸成长在这个时期,有幸吃了家乡那么多的鱼虾,有幸坐上这趟希望野外上的火车,哇哇叫着,随着时期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