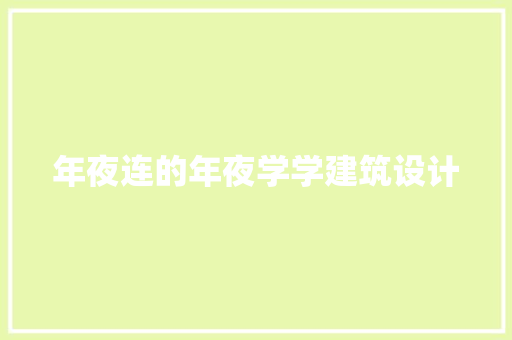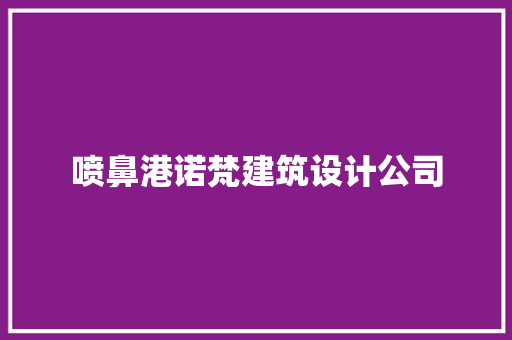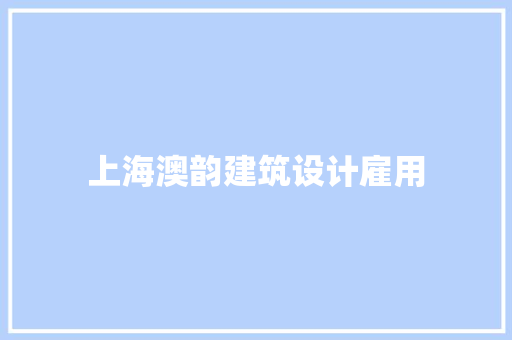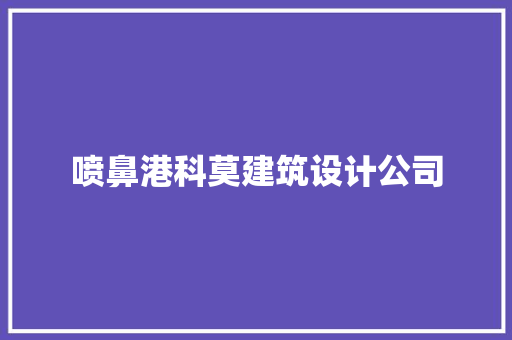J·R·布朗的《被他的小说人物环抱的狄更斯》,这幅画符合孙毓修所述的“于厥后头”,但是无“云烟蓊尉之状”,孙毓修很可能是将它与巴斯的《狄更斯之梦境》(B06插图)搞混了。
林纾译狄更斯小说《风趣外史》与《块肉余生述前编》封面,均为1914年商务印书馆版,是商务印书馆常年脱销书之一。

狄更斯《德鲁德之谜》中的插图,描述伦敦东区烟馆里的情景,把稳图中那个目光迷离、口角呆笑、正沉溺于鸦片烟中的中国人,这也代表了狄更斯对这个老大帝国的个人印象。
险些每一个以文为生者,都有着自己隐秘的希望:只消手中笔杆一摇,那些活灵巧现的文学人物就像被符箓招摄一样平常,群聚而来,附于笔端,随着作者的心意,在纸上幻化出各类引人入胜的精妙故事。借使有一位文人能拥有如此令人艳羡的法力,恐怕非狄更斯莫属。这位全球有名的19世纪文豪下笔如神的玄机妙法,在他辞世43年后,被欧亚大陆另一真个一位叫孙毓修的中国人洞察玄机,他在1913年4月的《小说月报》(第4卷第3号)揭橥的评论文章,对狄更斯驾驭小说人物的神妙手腕称颂不置:
“迭更司每一摇笔,则一时社会上之人物之魂魄,自奔赴腕下,如符箓之役使鬼物焉。尝有画师,写迭更司著书之画,于厥后头,作云烟蓊尉之状,中有各类之男女,老者少者,俊者丑者,容则醉饱者饥寒者,冠则大冠者小冠者,衣则新者旧者,其忧则各忧其所忧,喜其所喜,得意其所得意,失落望其所失落望,是皆迭更司小说中之主人也。是即天下众生之行乐图,无古无今,悉为此老写尽矣。呜呼!
”
孙毓修所描述的那位画师的画作,很可能指的是英国画家巴斯(Robert William Buss)那幅家喻户晓的名画《狄更斯之梦境》(Dickens'Dream),也可能是J·R·布朗(J R Brown)的《被他的小说人物环抱的狄更斯》(Dickens Surrounded by his Characters),这两幅画的共同点,都是狄更斯正安坐椅子上昏昏欲睡,而他小说中的人物便借此机会纷纭出场,围拢在他们的造物主身边,进入角色,卖力演出——无论孙毓修看到的哪一幅画作,在这双来自东方古国的玄色眼珠的注目下,这些狄更斯笔下活灵巧现的928个小说人物,正从纸上纷然跃出,簇拥着他们已经身处天国的主人,捋臂将拳,去俘获他们的中国读者。
愉快的先容人和不情不愿的访客
狄更斯初次“上岸”中国的韶光,是1907年,确切的日期是8月15日,或者按照东道主中国的计时方法,是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七。此时间隔狄更斯的肉身安卧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墨客角湿润的泥土下,已经由去了足足37年。就在这一天,他的《尼古拉斯·尼克尔贝》(Nicholas Nickleby)被移译为六卷本的中文,由当时中国最负盛名的出版公司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恰如狄更斯时期的英国批评家对这部小说的评价,“英语天下里最风趣的小说”,本书的译者林纾也一定深深嗅到了原著中呛人的荒诞诙谐感,因而舍弃了这本书让国人一望不知所云的原名,而冠之以一个既相符主旨,又足以吸引同胞眼球的开门见山的书名《风趣外史》。
“迭更司,古之伤心人也”,在卷首作为译序的长篇短评中,林纾对狄更斯一锤定音,这彷佛意味着这部名为“风趣”的小说又将会是一本像他翻译的第一本泰西著作,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一样“断尽支那荡子魂”的悲情故事。然而接下来,他又写道:“按其本传,盖出身贫贱,故能于下流社会之人品,刻画无复遗漏,笔舌所及,情罪皆真,爰书既成,声影莫遁,而亦不伤于刻毒者。”于是这本书又成了一本状述下层疾苦的底层小说。“以此等人既有此等人,则亦不能不揭此等事示之于世,令大家有所警觉,有所备豫,亦禹鼎铸奸,令人不逢不若之一佐也”这段描述,又给读者一种警世小说的不雅观感。
以一部小说,兼具风趣、悲情之感,既深入底层,又警觉众人,在林纾看来,狄更斯的作品如一座巨轮,满载着太多的情绪和意旨,如今既然在中国港口靠岸,当然应将船上琳琅满目的货色逐一卸下,交由中国读者点数查看。作为查验货色的第一人,林纾认为这艘“风趣外史”号上对国人来说最宝贵的货色,该当是狄更斯的笔法,特殊是他描写尼古拉斯母亲“丑状”的那一节:“淫耶?秽耶?蠢而多言耶?愚而饰智耶?乃一无所类。”——林纾创造自己所节制的传统中国的润色辞藻中,竟找不出一个得当的词语,来恰当地状摹狄更斯笔下的这个人物(实际上,英国的评论家也同等认为尼古拉斯太太是这部小说中最讨喜的风趣丑角),在狄更斯强大笔墨功力碾压下,林纾不由惊叹道:“左、马、班、韩,能写庄容,不能描蠢状,迭更司盖于此四子外别开生面矣!
”
狄更斯借使能听到这位中国译者这番至心赞誉,想必内心定然十分受用,尤其是他这个泰西作家竟然以一己之力技压被中国文人奉为文宗的左丘明、司马迁、班固和韩愈四大文豪,更会让他甘之如饴——在喜好奉承这方面,狄更斯与他的维多利亚同胞一样对赞颂和掌声有着无与伦比的希望。更何况林纾的这段以抑己扬人为代价的赞誉,还知足了狄更斯内心中暗藏的一个偏见:他对林纾的祖国中国的意见。
用“不友好”这个词来形容狄更斯彼时的中国不雅观可谓轻描淡写。如果将狄更斯厌恶的事物列成一张单子,中国的排名该当相称靠前。纵然他的屋子表面就挂着一串(所谓的)中国灯笼装饰这一点,也拯救不了他对中国的刻板偏见。“可能有一个野蛮怪异之国,在地球上的某个地方,它总是对自由意志说不,把自己和天下其他地方隔绝开来,决心不随大家一同向前”,1851年,在参不雅观了大英万国展览会后,狄更斯如是写道。这个自我隔绝、谢绝进步的“野蛮怪异之国”正是他在参不雅观了中国展品后对这个国家的意见。
十九世纪中国最丑陋的一壁,也恰好被狄更斯敏锐地捕捉到了,那便是对鸦片病态的沉溺,以及因此导致的无可救药的堕落。在狄更斯末了一部未完成的小说《德鲁德之谜》(The Mystery of Edwin Drood)的开篇,他就描写了伦敦东区一个专为中国人和印度人开设的大烟馆里邋遢腌臜的情景。
可以想见,如果让狄更斯和林纾坐在一起商榷译介问题,两人末了一定会闹得不欢而散。一方带着19世编年夜英帝国如日中天的高傲气焰,视昔日的天朝上国堕落为夜壶屎尿之邦;而另一方只管深感内外交困、国运蜩螗,对时弊国病也并不掩饰笼罩,但出于朴素的爱国生理,也难以接管对方颐指气使地直戳痛处——狄更斯自然不愿踏足这个贰心中弥漫着鸦片烟愚蠢桎梏的落日帝国,林纾也不会喜好一位恶意的讽刺者带着骄矜的嗤笑撕开祖国的伤疤。
更何况林纾还触碰了狄更斯一个最敏感的禁忌:版权问题。作为从社会底层胼手胝足的有名作家,版税霸占了狄更斯日常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只管一本书被盗版肯定是出于读者对它的至心喜好,但这些名声在狄更斯眼中肯定抵不上实实在在的金钱。在1844年1月的那场指控出版商陵犯其《圣诞欢歌》的官司中,他将那些盗版书商骂作“海盗”,得意洋洋地声称“这些海盗被修理得很惨,鼻青脸肿,遍体鳞伤,倒地不起”,这场官司持续打了五个月,直到那家出版商关张倒闭为止。借使狄更斯仍旧在世,他一定会对林纾不加奉告便私下翻译其著作的行为穷追猛打,哪怕林纾为他说再多的好话,给他的名声开辟了再广大的外洋市场,也难以抵挡这位小说家接连射出的愤怒之火。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狄更斯没有在他生前最辉煌残酷的时候上岸中国,乃是一桩幸事。他不必为是否要履足这片地皮而疑虑重重,也不须要卷入一场很可能会旷日持久的跨国版权官司,而他的去世亡也恰到好处地使他不必面对欧亚大陆另一端中国读者的指示批评——无论这批评是好是坏。而作为中国一方,没有原著者的聒噪唠叨,没有日后令人烦忧的版权问题,有的却是泰西新式印刷术的引进和推广,以及一批渴望呼吸新鲜空气的读者,此时正是泰西小说大举上岸的第一个黄金时期,自然也是翻译家大显技艺的时期。只不过作为狄更斯的译者的林纾,也有他自己的问题。
林纾的翻译:狄更斯的中国外套
“予不审西文,其勉强厕身于译界者,恃二三君子口述其词,余耳受而手追之,声已笔止,日区四小时,得笔墨六千言。”
在狄更斯的第一部中译小说《风趣外史》出版一个月后,林纾在他新译的狄更斯另一部小说《孝女耐儿传》(今译《老古玩店》,The Old Curiosity Shop)的媒介中如此写道。作为20世纪初中国最著名也最具个性的翻译家,林纾老实地承认他实在对任何一门中文之外的措辞都一无所知。但他又举例证明,自己只管不通英文,却可以与作者心领神会,一如身处静室中聆听室外脚步声一样,韶光既久,“户外家人足音,颇能辨之明晰,而余目固未之接也”。正是由于这种自傲,使林纾在移译狄更斯的小说时,可以放心大胆地加以点评。
必须承认,从《风趣外史》到《孝女耐儿传》,到被他许为“近年译书四十余种,此为第一”的《块肉余生述》(今译《大卫·科波菲尔》,David Copperfield),到《贼史》(今译《奥立弗·退斯特》或《雾都孤儿》,Oliver Twist),再到《冰雪分缘》(今译《董贝父子》,Dombey and Son),林纾在译序中的点评都切中剀要,他一而再、再而三夸奖的狄更斯描摹人物的风雅笔法、长于设伏埋线的奥妙构思,以及对底层社会的深切关照,不仅与狄更斯同时期批评家的不雅观点东西相合,直到本日,狄更斯的读者仍会承认,林纾的这些点评仍可谓不易之论。他在《块肉余生述》译序中将狄更斯构造笔法喻之为“锁骨不雅观音”,诚可谓旷古绝今的生动妙论:
“古所谓锁骨不雅观音者,以古皮钩联,皮肤腐蚀,揭而举之,则全具铿然,无一屑落者;方之是书,则固赫然为锁骨也。大抵文章开阖之法,全讲骨力气势;纵笔至于灏瀚,则每每遗落其细事繁节,无复检举,遂令不雅观者得罅而攻。此固不能为文者之病,而精神终患弗周。迭更司他著,每到山穷水尽,辄发其思,如孤峰突起,见者耸目,终不如此书伏脉至细,一语必寓微旨,一事必种远因,手写是间,而全局应有之人,逐处呈现,随地关合;虽偶而一见,不雅观者几复忘怀,而闲闲着笔间,已俯拾皆是,读之令人斗然影象,循编逐节以索,又逐一有是人之行踪,得是事之来源;综言之,如善奕之着子然,有时一下,不知后来咸得其用,此以是称为国手也!
”
经营构造,设伏埋线确实是狄更斯的善于之处,毕竟他的这些长篇小说在开始时都是杂志上的连载故事,在以读者口味为市场导向的写作环境下,作家如果谋篇不周,写后忘前,就不能怪读者们始读终弃,另觅新欢。林纾自然对这一背景毫无知晓,他的参照物是中国传统的章回小说。章回小说的特点是着花散叶,各表一枝,每一回即是一个独立故事,回与回之间未必需要前后呼应,“且听下回分解”所设下的伏线不会绵延数里,它所预期的读者群不是在等待下一期连载时焦灼度日的订户,而是一群听完即走的散客。泰西长篇小说与中国章回小说是两种不同社会文化下生发出的迥异的文学形式,当林纾手持中式规尺,丈量堪称泰西小说典范的狄更斯作品时,自然会对其累累如贯珠的绵密构造惊为天人妙笔,而视《水浒传》之类的章回小说为粗糙之作。
狄更斯书中所描写的各类19世纪英国社会之丑恶、法制之弊端、商贾之贪婪与士绅之伪善,在林纾看来,也当成为一壁来自西方的镜子,用来彻照彼时中国的丑陋现实。恰如他在《块肉余生述》译序的最末所殷殷期望的那样:“英伦半开化时民间弊俗,亦皎然揭诸眉睫之下,使吾中国人不雅观之,但实力加以教诲,则社会亦足改良,不必心醉西风,谓欧人尽胜于亚,似皆知良能之彦,则鄙人之译是书,为不负矣。”
这段评述赤裸裸地彰显了林纾为何如此热衷翻译推崇狄更斯作品的缘故原由,这既包括他个人的爱好,同时也是社会的须要。晚清以改良改造自命的文士有种分外不雅观念,认为小说具有改天换地的伟力,攸关社会进退与国运隆衰。在本日看来,这种不雅观念与相信一部电视剧可以旁边国策制订一样稚子纯挚,然而晚清时人却近乎固执地认定此说为社会改造的终南捷径。这一方面很可能是古代中国“文以载道”思想在晚清的进化变种,另一方面则是中国文士对他们的泰西同行在国家里扮演的贵显角色艳羡与认同。
最早创造小说巨大浸染的人是大名鼎鼎的梁启超,1902年11月14日,他揭橥那篇引爆后世称为“小说界革命”的宣言《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时,他尚因四年前那场失落败的政变而流亡外洋。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历数中国国民迷信愚蠢、趋炎附势、奴颜婢膝、寡廉鲜耻、轻弃信义、权略诡诈、苛刻凉薄、轻薄无行、沉溺声色,终极“义和拳者起,沦陷京国,启召外戎”,各类掉队劣迹,罪魁只有一个:“惟小说之故”,因此“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悛改小说始。”他在四年前揭橥的《译印政治小说序》里,又将欧洲变革的缘故原由,指为小说的巨大力量:“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每每以其身之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每每每一书出而全国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宦海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
只管仔细查考各国政治史,很少有哪些实例证明小说在政治变革中起到了何种浸染,与其说是小说匆匆成时势,倒毋宁说是时势造就小说。以狄更斯为例,他的小说只管揭破了英国社会制度中阴郁丑陋的一壁,但这些揭暗中射实在对英国的改革政策影响盖寡。譬如他在《小杜丽》(Little Dorrit,最早的中译本为1910年薛一谔、陈家麟合译的《亚媚女士外传》)对英国的官僚制度大张征伐之前,著名的《诺斯科特-特里维廉报告》已经提出英国公务职员办法的改造方法;英国的狱政改革也早在《块肉余生述》之前,就已展开。很多狄更斯取材现实并运于小说中的黑材料,正好是改革过程中将过去的问题曝露出来的结果,然而狄更斯为了达到自己的艺术效果,宁肯将这些过期的材料当作社会的真实写照加以夸年夜讥讽。
从这个角度上讲,当林纾在《块肉余生述》译序将这一期间称为“英伦半开化时”,也可以说是大错特错。就在《块肉余生述》连载完的次年,大英万国展览会举行,全体英首都沐浴在进步时期的荣光之下,当然,那个被狄更斯讥讽为谢绝进步的“野蛮怪异之国”的中国人对此一无所知。
因此,林纾心心念念的译泰西小说以救中国弊端的愿景,可以说是本末倒置。然而这并不妨碍他手持中国规尺,按照中国办法为狄更斯裁剪一身中国外套。为了让他亲手为狄更斯裁剪的中国外套更加合身,林纾乃至还替狄更斯改动思想。
在《风趣外史》的译序中,林纾责怪狄更斯全书的关键人物,那位以虐待学童为能事的多斯博伊斯学堂(Dotheboys Hall,意译为“坑人子弟学堂”)的教习史奎尔斯“其事大悖常理”缘故原由是“为中国所无”,以是“可以不论”。林纾辩称,在中国,教习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恰好颠倒过来“中国今日之教习,正患不能得生徒之欢,又何敢施其威福?中国学生之语教习曰:‘汝奴隶,待饲于我,我不特意,汝立行,汝妻子亦立馁!
’而教习又多寒士,一见学生,已胆慑不敢出,其正派之言,讲堂之上,一听之学生,而教习特同木偶,即间有匡正,已哗然散学,必屏逐此教习然后已”。
在抱怨完一通中国学生如何飞扬跋扈欺凌老师的恶劣行径后,林纾慨叹“惜中国别无迭更司,别著一书,为学生正其谬戾”。
考虑到此时林纾正在京师大学堂执掌教鞭,而就在他为这本书写译序的一个多月前,无法无天的学生们,刚刚以暑气天热为由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罢考运动,据北京大学所藏档案记述,这群沸反盈天的学生“连日聚众礼堂,登台演说,鼓噪哄乱,并逼令监督撤去考试之谕,以至暑假,亦竟不考而即散学”,因此不难明得林纾站在老师一方义愤填膺为之辩白的缘故原由,然而这种以己之意点评批驳原著作者意旨的行为,很难说不是一种故意的冒亵。
狄更斯的中国种子
只管林纾给狄更斯强套上一件中国外套的行为对原著是一种捆绑和束缚,但他最少给那时的中国读者供应了一个不那么碍眼的阅读工具。他们大可以将狄更斯想象为泰西的司马迁和曹雪芹,毕竟从林纾的译著上来看,那些生活在伦敦的士绅淑女们口中吐出的,都与中国文士习气的孟役夫和蒲留仙的措辞所差无几,只不过名字冗长一些罢了。
从林纾翻译的《风趣外史》开始,到《孝女耐儿传》《块肉余生述》《贼史》《冰雪分缘》等五部林译小说,再到1910年薛一谔、陈家麟合译的《亚媚女士外传》,1913年到1914年,狄更斯另一部最著名的长篇小说《双城记》也被林纾的互助者魏易翻译出来,并连载在发起“小说界革命”的改良家梁启超主理的《庸言》上,题为《二城故事》,1918年,狄更斯的成名作《匹克威克外传》(The Pickwick Papers)也以《旅行笑史》之名与中国读者见面,这样,除了《巴纳比·拉奇》《马丁·朱述尔维特》《荒凉山庄》《困难时世》《远大出路》和《我们共同的朋友》外,狄更斯的长篇小说中的代表作险些被一扫而空。而狄更斯最受欢迎的短篇小说《圣诞欢歌》在1910年代有了四个译本:《鬼语》(《小说月报》,1912年3卷2号)、《钱虏后悔录》(《墨海》,1913年12月1期)、《悭人梦》(《小说时报》,1914年1月21期)、《耶稣诞日赋》(《小说月报》,1915年5卷10号)——狄更斯的种子已经在中国播下长成,是等待读者摘果品尝的时候了。
撰文/李夏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