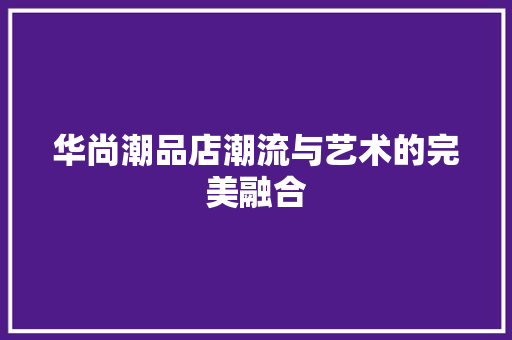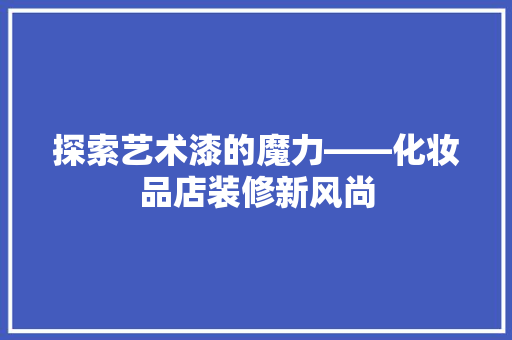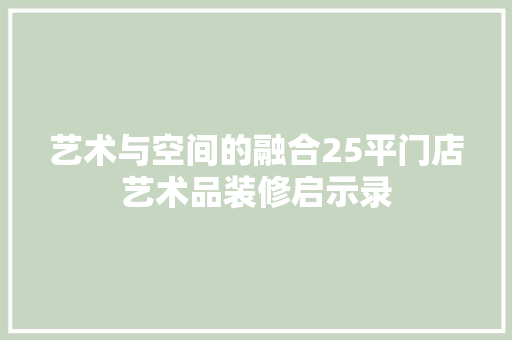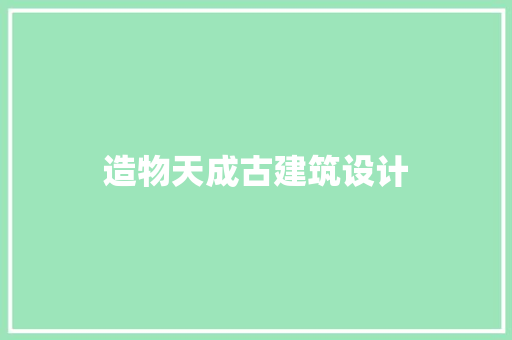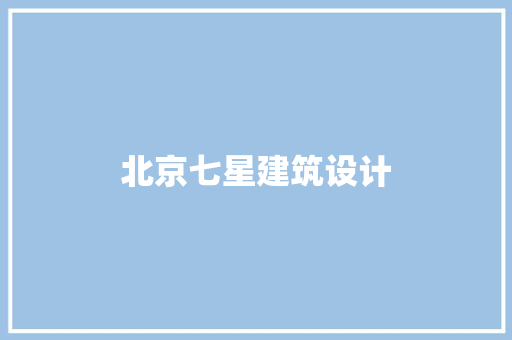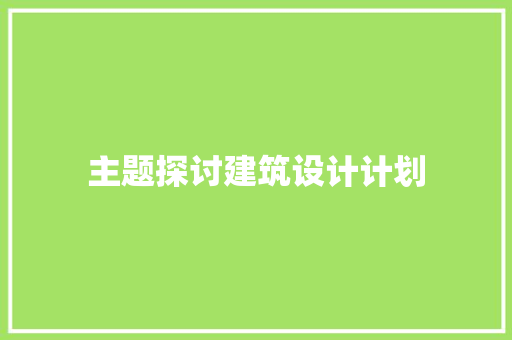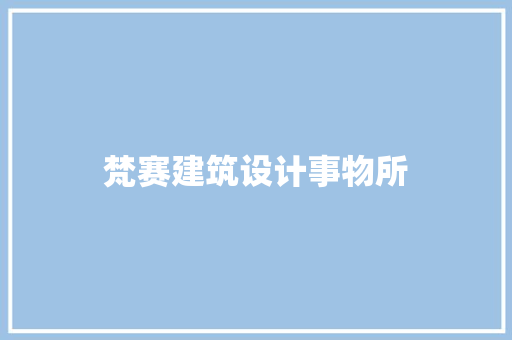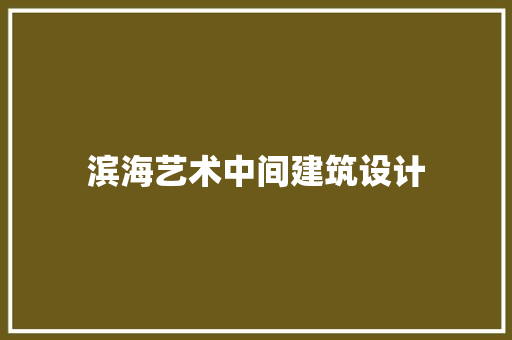【陈波编语】石韵媛的作品《66段书写》是一系列深入磋商历史、文化和身份的作品。这个作品通过不同的书写办法和材料,如纸面铅笔和地面水写,对历史进行了“重写”。作品的紧张灵感来源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梁思成和北京城墙的历史,旨在磋商和追忆这段无法抹去的悲哀历史。作品中,66段历史见证者的陈述对应了事宜发生后的66年,这些陈述通过不同的书写办法被呈现出来,创造了一种纪念性的、能够引发社会对话与反思的空间。
石韵媛的作品不仅仅是艺术创作,更是一种对文明的记录,通过艺术的办法创造出一种可能成为历史的唯一决议,使艺术真正具有了当代性姿态。《66段书写》的批驳性实践使她沿着古城墙遗址进行着书写行为,她试图重新体验历史的存在和话语态度,将事宜带入公共视野的同时也带入了公众年夜众的评判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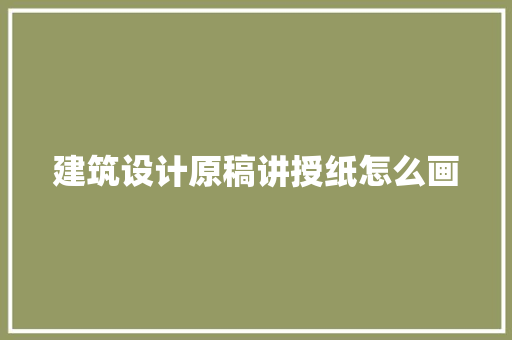
此外,石韵媛的作品在艺术界也得到了认可,她的《66段书写》得到了第三届中国美术奖的银奖,这标志着她的作品在艺术领域的造诣和影响力。
第三届中心美术学院“靳尚谊青年西席创作奖”获奖西席作品展于中心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幕。设计学院西席石韵媛作为四位获奖青年西席之一,在展览现场呈现出其创作《66段书写》。经由这件作品,艺术家通过挖掘“书写”这一行为本身在不同场域尤其是公共空间的力量与潜力,表达出艺术如何参与社会议题乃至更广阔的历史社会文化语境。
目前在中心美术学院设计学院任艺术治疗方向西席的石韵媛,从中心美术学院设计学院毕业后,就读于芝加哥艺术学院艺术治疗专业。她的研究涉及艺术与美学疗愈代价及其生理学运用机制、书法与正念、留恋与文化认同等等。在个人创作领域,石韵媛展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遂将中国传统的“书写”行为,纳入其创作中,并由此出发延展并建构出一系列环绕书法、冥想、身份和疗愈之间关系的研究与创作。在接下来的采访中,石韵媛与艺讯网分享了有关她的个人创作动机、作品脉络的简要梳理以及她在作品背后对付社会与文化议题的思考。
艺术设计《66段书写》获奖评语
《66段书写》通过集体影象共同书写了北京城墙拆迁历史,66段陈述涵盖的不仅是66年来不同身份的亲历者和非亲历者的话语片段,更是对城墙所承载着的物质与精神的追忆。
作者沿着城墙遗址“以水为墨”书写着历史,字迹因蒸发而逐渐消逝,犹如城墙的消散,这种“纪念性”的行为背后,透射出作者试图探寻历史及话语态度的存在。作者约请有着共同影象的社区居民参与个中,用他们的口述历史重构档案的同时,也是集体对其共同生活空间的追忆。
此外,作者操持性书写了16个城门遗址的史料记载和与之干系的历史影象,并以此作为“重构城墙”的信息。残余的城墙经由自然侵蚀与后期的修护,由上到下呈现出不同的颜色与肌理。密密麻麻堆砌起的笔墨宛如这厚重的城墙,笔墨在这里成为了一种视觉符号,其阅读性不再成为主体目的和功能,而是意在通过书写的情怀往返复中兴意象的城墙建筑形态。已建的视觉档案重筑了消散的古城文明,所有文献被挤压成一块城墙砖大小,物质化了这些无形的影象。城砖是构建城墙的最基本元素,作者把研究思考等所有行为凝聚在一块纸城砖中,使之作为一种超过时期的影象载体,其意义超越了老城砖所勾勒出的历史轨迹。(中国美协平面设计艺委会)
艺术设计《66段书写》创作谈
作者:石韵媛
北京城对付我而言,是一本永久也读不完的大书。北京是“城”,又是“京城”,它拥有连续800多年的“京城都城史”和一个近乎完美的封建帝都城市格局。初次来到北京时,我惊异于这里的“门”之多,只管这些门大多已经“徒有浮名”(被拆掉了),它满载着的物质与精神的厚重又使其永垂不朽。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被梁思成称作“一串光彩耀目的缨络”的北京城墙作为一种封建象征被历史抹去。这些古老的城墙和城门,虽然度过了800多个风霜雪雨,但终极还是成为了“当代城市”方案的捐躯品。“五十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缺点的,我是对的。”梁思成上世纪50年代初的一句话一语成谶。几十年过去了,如今巨大的北京城变得拥堵不堪,却又“摊大饼”似的不断层层扩展。当所有人都认为这样的北京才是发展的北京,才是当代化的北京时,便无形地将一座拥有无限可能性的城市置于一种两难的田地中。在资源环境压力的空前逼迫下,2015年7月,政府决定在通州建立北京行政副中央。
在《66段书写》的创作中,我试图理解和判断文化的符号性、话语态度、权利动态以及集体回顾对付一种文明发展的持续性影响。对历史的“重写”,也使其在当下天生了新的“历史文本”。这件作品中,笔墨被还原为一种最朴素的叙事载体,我在现场的书写,拓展了它在地面、空间和场域中的表现力。
整套作品分为三个系列——《墙|类砖书》《1-16/2016原稿》《砖》。作品创作的媒介手段为两种书写办法——地面水书写和纸面铅笔书写。作品中,“砖”的观点被延伸放大。墙面水墨作品的单元尺寸以及类砖书的尺寸均与实际城砖尺寸相仿。
在这一系列作品中,我以一种“纪念性”行为在旧城墙遗址(今北京二环)的16个城楼节点处书写了与城墙、与拆城事宜干系的口述故事。书写内容为自1950年北京城墙拆除以来,66年内不同陈述者对付该事宜的回应。通过拜访梁思成故居、北京明城墙遗址、北京市档案馆、国家图书馆、北京市方案展览馆,我获取了相对详细和有效的史料信息。我选取了每一年度的一段代表性口述,陈述者涉及学者、建筑师、政府官员、、作家、老城居民、商贩……
城墙的存废关涉市民生活和社会各阶层民众的文化影象与情绪,因此,在这场辩论中的见地和方向具有非常主要的历史代价。我尽可能去还原和再现真实的过程、真实的历史。我用地面水写的办法在黑砖上书写出这些或尖锐、或平和、或感性、或理性的口述笔墨,水迹会因蒸发而逐渐消逝,字迹的消逝犹如城墙的消散,人们的辩论和回应也随韶光逐渐远去。现场的书写行为过程充满了许多不愿定性,期间有时地碰着了许多形形色色、不同身份的人并产生了不同态度的有趣的对话,我把原来带有争议的历史话题引入当代市民的生活语境,遗憾的是,他们当中很少有人能够关注到书写笔墨背后的指向——历史、城墙。
该系列是在操持性地走完北京二环16个城门遗址点后创作出来的。老北京旧城共有“内九外七”16座城门,它们各自有不同的名字、用场和特色。《原稿》书写的内容吻合每一个城门的史料记载和与其干系的历史影象,并以它来作为“重构城墙”的信息。残余的城墙经由自然侵蚀与后期的修护,由上到下呈现出不同的颜色与肌理。密密麻麻堆砌起的笔墨宛如这厚重的城墙,笔墨在这里成为了一种视觉符号,其阅读性不再成为主体目的和功能,而是意在通过书写的情怀往返复中兴意象的城墙建筑形态。
这一系列展示了两块砖。一块是真正的老城砖,另一块是我用艺术创作手段融铸的一块城墙砖。这块纸砖里承载的所有研究资料、草图、文献、照片等都用以表达我对城墙和这段历史的怀念,以及复原它的欲望。城砖是构建城墙的最基本的元素,我把研究思考等所有行为凝聚一块纸城墙砖中,某种意义上,我认为它比原材料的真砖还要沉重、有代价。
当我逐日拎着羊毫来回于东南角楼、护城河、过街天桥和无数个十字路口时,当我看到永定城楼放学轮滑和放鹞子的孩子们的笑脸时,周恩来总理那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薄暮”该是多么遗憾的美。我希望通过《66段书写》重新勾勒这段厚重历史,并致敬那些为中华文明添砖加瓦的每一代劳动人民。
作者简介
石韵媛,生于河南郑州。2016年取得中心美院设计学院学士学位。现就读于中心美院设计学院国家形象视觉研究方向,同时攻读美国芝加哥艺术学院艺术治疗与咨询硕士学位。
石韵媛认为游戏和玩具反响着更广泛的社会变革
靳尚谊青年西席创作奖 | 石韵媛:以“书写”探索疗愈的可能性
韶光:2021.11.23
编者按:2021年11月18日下午两点半,第三届中心美术学院“靳尚谊青年西席创作奖”获奖西席作品展于中心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幕。设计学院西席石韵媛作为四位获奖青年西席之一,在展览现场呈现出其创作《66段书写》。经由这件作品,艺术家通过挖掘“书写”这一行为本身在不同场域尤其是公共空间的力量与潜力,表达出艺术如何参与社会议题乃至更广阔的历史社会文化语境。
目前在中心美术学院设计学院任艺术治疗方向西席的石韵媛,从中心美术学院设计学院毕业后,就读于芝加哥艺术学院艺术治疗专业。她的研究涉及艺术与美学疗愈代价及其生理学运用机制、书法与正念、留恋与文化认同等等。在个人创作领域,石韵媛展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遂将中国传统的“书写”行为,纳入其创作中,并由此出发延展并建构出一系列环绕书法、冥想、身份和疗愈之间关系的研究与创作。在接下来的采访中,石韵媛与艺讯网分享了有关她的个人创作动机、作品脉络的简要梳理以及她在作品背后对付社会与文化议题的思考。
石韵媛
中心美术学院设计学院艺术治疗方向西席
芝加哥艺术学院艺术治疗文学硕士,中心美术学院设计学院国家形象视觉研究方向硕士、视觉传达专业学士。美国艺术治疗协会专业会员,国际创造性艺术教诲与治疗协会专业会员。
研究涉及艺术与美学的疗愈代价及其生理学运用机制、书法与正念、留恋与文化认同等。曾在移民与难民做事中央、养老机构、匿名戒毒组织、分外学校事情,策划并开展10余项、超过1000小时认证的艺术治疗实践项目。个中为失落智症老人开拓的《艺术乐高》干预操持获美国Hilgos基金会专项帮助,《水书法:本土艺术治疗实践的人种学研究》获芝加哥艺术学院艺术治疗精良研究项目。
受访人丨石韵媛
采访 | 艺讯网
艺讯网:石老师您好,首先请为大家先容一下您在“第三届中心美术学院‘靳尚谊青年西席创作奖’获奖西席作品展”的参展作品《66段书写》。
石韵媛:《66段书写》是我从2015年到本日持续创作的作品,也是我过去几年来进行艺术治疗实践的紧张线索之一。我从小学习书法,因此书法与书写成为我创作与表达的“母语”。和我的许多其他作品近似,“写”这一动作是我作品中的“核心”,我也希望经由书写,在艺术中探索更多对话与疗愈的可能性。
《66段书写》,2016,综合股料,尺寸不一
这件作品的创作,基于我对付北京古城墙的历史研究。个人希望在这一研究中考试测验某种诗性的叙事表达,并通过书写来营造某种纪念性的、能够引发社会对话与反思的空间。因此,在作品中我对不同书写材料、办法和创作场域进行了实验,将我作为艺术家的个体叙事融入到更广阔的历史社会文化语境中,以探索书写行为本身在不同场域的力量与潜力。环绕这件作品,后期我也延续和展开了一系列有关书法、冥想、身份和疗愈之间关系的研究。
《66段书写》,2016,水书法,3780 x 1320mm
《66段书写》,2016-2021,水书法,9240 x 1320mm
《66段书写-原稿》, 2016,铅笔,1950 x 1080mm
艺讯网:从2016年《66段书写》到2020年《66 Unanswered Questions》的手工书,谈一谈您的作品这一脉络之间的联系与变革。
石韵媛:不论从创作实践、思辨研究,抑或是艺术治疗的角度,我的作品之间都有某种脉络可循。除了我对书写本身的兴趣与探索,引发我创作《66段书写》的另一个缘故原由,是我在2016年看到了一篇有关北京迁都操持的新闻宣布。当时北京行政副中央即将迁至通州,恰好我个人一贯对梁思成的城市操持研究和实践深感兴趣,也阅读过很多干系的书本文献。看到北京的迁都操持,我即刻便想到1950年梁思成向市政府上书的北京新城市方案两全方案。从1950年到2016年,构成了我作品中“66”的来源,即希望通过纪念66年,环绕北京古城墙历史的不同社会话语谈论,以反思有关城市方案发生的社会征象。
《66段书写-砖书》,2016,水书法,220 x 420cm,内页
《66段书写-纸砖》,报纸,纸浆2016,220 x 420cm
《66段书写-砖书》,2016,水书法,220 x 420cm
创作《66段书写》时,我把水当作墨汁,把大地当作画布,沿着北京二环路的古城墙遗址完成了全体书写过程。书写过程中,我通过拍照的办法,留下这些书写的水迹。水与我创作的主题有很强的符号对位:在创作的过程中,水迹因空气和韶光而蒸发、消逝。通过水的物理属性,以形成本日人们对付一种文化消逝或是一种声音弱化的反思。这件作品启动了我作为艺术家的独立思考,同时也促进了我个人创作措辞的初步建构。
我对中国传统文化一贯抱有强烈的好奇心,不论从精神层面、技能层面还是目前研究的艺术疗愈功能层面,我都希望能够尽可能地通过研究和探索来拓展中国传统文化的代价。2020年创作的《66 Unanswered Questions》是我环绕艺术治疗的系统研究的一件作品,这件作品关注了艺术治疗在东西方“跨文化”转译过程中碰着的多少寻衅和困境。当时,我在美国学习艺术治疗,一方面,把艺术治疗这一学科带返国内,并做出新的考试测验和发展成为我面临的问题和创作初衷,另一方面,我也很关注文化符号和自己的文化身份——二者对付作品和作为创作者、研究者的我而言非常主要。因此,我选择以书法的逻辑和办法呈现我的对付艺术治疗的研究。
《66 Unanswered Questions》,2020,学术论文+手工书,植物纤维、亚麻、棉、颜料,210 x 150mm
《66 Unanswered Questions》,2020,手工书,过程,210 x 150mm
《66 Unanswered Questions》,2020,手工书,内页,210 x 150mm
艺讯网:您如何在作品中处理设计干预与社会情状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详细的人与社会问题之间的关系?或者说,经由作品,您希望传达若何一种艺术理念?
石韵媛:我的创作一贯以来都比较关注社会问题。我认为设计本身便是一种有目的的行动和干预,也希望通过艺术和设计的办法,考试测验探索办理社会问题的新方案,这与艺术治疗的“艺术干预”实质是同等的。例如,在艺术治疗的研究中,我们会探索艺术更多维度的代价和意义——艺术如何促进个人的身心发展、提升社会公正和福祉、缓解社会创伤以及如何通过艺术深化教诲等等。我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创作,让艺术被更多人看到和欣赏,能够让更多人受益。
《二手书操持》展览序言,2014,粉笔,装置,5 x 6m
《二手书操持》展览序言,2014,粉笔,装置,5 x 6m,局部
在我进行艺术治疗的研究和实践、教诲时,很少能给自己留有一个完全的艺术创作的韶光,以是近期我的创作多以短期、即兴的形式涌现,创作办法也更倾向于参与式。在艺术治疗的事情中,我们要和病人,和不同的事情群体一起通过创作达到疗愈效果,以是团队协作的创作更多。
艺讯网:您在中心美术学院设计学院担当艺术治疗方向的西席,作为中心美术学院名副实在的“新动力”,请谈一谈您在艺术传授教化实践中的方法和理念,以及如何看待西席与创作者两种身份间的关系?
石韵媛:艺术治疗是一门较新的跨学科专业,它凑集了很多学科的知识和实践方法,比如艺术学、生理学、认知与神经科学、社会学、教诲学以及康复等领域。在传授教化中,或者说在学科方案中,我们会非常看重学生跨学科思维的演习,让学生既能够感性的体验艺术,又能够理性、科学的理解和运用艺术的功效。
作为央美的青年西席,我会在未来不断努力发展艺术治疗这一领域。在传授教化过程中,美院的艺术传统和精神对我有着巨大影响。我的艺术治疗研究中,依然会延续我对中国文化、本土艺术实践与疗愈代价的研究。艺术治疗在中国,尤其是在美院这一学术场域的发展非常可不雅观,也带给我非常可不雅观的启示。早期西方艺术治疗的学科发展,更多基于生理以及临床领域学科知识之上发展而出,我认为央美拥有如此丰硕的艺术传统和精神,必定能够帮助我们探索更加具有中国和中心美术学院特色的艺术治疗学科方向。
《焦虑处方》,2020,电子文件
艺讯网:得到“第三届中心美术学院‘靳尚谊青年西席创作奖’”对您的个人创作与传授教化生涯具有若何的意义?对未来的创作与传授教化有何构想和期待?
石韵媛:我非常感激和戴德老院长靳尚谊师长西席为青年西席供应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发展与互换平台。这次获奖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它意味着我作为青年西席的真正启航。在未来的事情中,我会谨言慎行,明确自己的义务和担当,努力做好学科培植和发展。为央美新百年奉献自己的青春,尽全力成为真正的“央美新动力”。
石韵媛在展览现场接管艺讯网采访[采编 | 艺讯网,现场图 | 李迪,作品图片资料致谢主理方] 陈波公益教室、陈波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