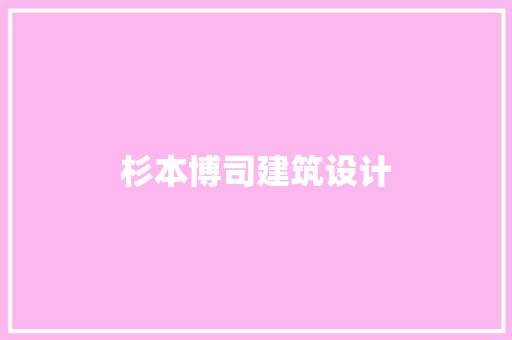如果第一次见到杉本博司的作品,一定会被这介于“绘画”和“照片”之间的图像所震荡吧——在黑与白之间以灰度来显现的图景,以绝对精妙的质感来显现;在同一幅作品中,不同物品的材质都被细腻地还原出来:大理石的质感、马赛克的质感、瓷器的质感,就连空气中扬起的灰尘,也被敏锐地捕捉,留存在底片上。比起森山大道那般粗粝狂野的风格,杉本博司选择了另一条道路:这是去除了人类中央论的、在历史产生之前的、原始意识的拍照。
杉本博司的作品,就像用细砂纸打磨数百遍后的大理石那样细润、柔和,呈现出一种精度极高的石版画般的错觉,他的拍照中有种不是用手指而是用眼睛去抚摸的触感。那么,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如此惊人的作品是怎么拍出来的呢?这些作品,不仅是拍照师本身的履历积累和美学不雅观念下的产物——杉本博司的照片们,也是他本身“技能宅”研究的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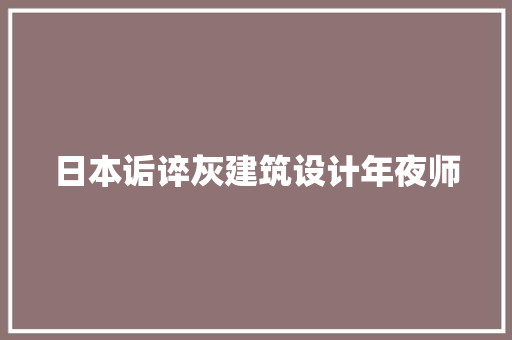
使生硬的模型变得柔和逼真
提及跟拍照的缘分,杉本博司,这位日本著名的拍照师与建筑师,在12岁时拥有了第一台属于自己的专业相机玛米亚(Mamiya)6——天下上第一款6x6画幅可变换镜头旁轴式取景摄影机,共有三款可选镜头,利用120底片,仅于1940至1960年间生产。相机原来是父亲带回来的。父亲不太会用,杉本就开始学着摆弄它,乃至在衣橱里建了个暗房。这台相机机身轻巧,一套大约1.5kg的重量让一个孩子也能轻易带着它出门。年少的杉本博司带着它四处游逛。在访谈中提及这段经历时,杉本博司笑着说他从那往后就开始自学成为一名拍照师:“当时,我只想看看表面的天下,我就像一个嬉皮背包客一样,离开了日本,良久都没有回去。”
于立教大学双修完经济学与西方哲学双学士学位后,1974年,杉本博司去往纽约,进入美国洛杉矶艺术中央设计学院学习拍照,并移居纽约。这个决定险些改变了他的生平,由于他正是在1976年于美国自然史博物馆拍摄了早期最主要的系列作品《透视画馆》。这组作品目前也在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央的“杉本博司:无尽的霎时”中展出。
杉本博司拍摄的这组相片,拍摄工具皆为美国自然史博物馆展示的模型。这些模型中有北极熊、兽群和原始人,背景也是自然博物馆中常见的史前世界先容场景。但在杉本博司的拍照中,没有详细的光源与明确的光影,模型与背景都统一在灰白的色调中。这种灰色的色调,拉近了前景模型与背景的间隔,也让这些生硬的模型变得柔和、逼真,彷佛某种真实存在过的活物一样平常。杉本博司如何做到这一点?这就有赖于在他在拍照器材和曝光韶光上所做的实验。
用相机捕捉融化的韶光
从1978年开始拍摄的《戏院》系列,是在《透视画馆》系列的根本上进行的另一次大胆考试测验。杉本博司将镜头对准剧院的幕布,调大光圈,打开快门,在两个小时的曝光后,得到了这样的一张照片:剧院的建筑细节逼真到不真实,座椅、墙面装饰乃至幕布都由于屏幕的光源折射而闪闪发光。但影幕本身则变成了一块通亮的空缺,留下的是细节。作为主题的影幕上所演出的内容,则像被切割后一样平常,从画面上消逝了。这种体验和效果,也带给他本人巨大的震荡。这是只有相性能看到的,人眼无法看到的景象。用他的话来说,人的生平,便是只有一次的显影过程:从出生睁开双眼的那一刻,到临终闭眼为止,人类的曝光韶光,也只有这一次。因此,要捕捉到人类双眼所捕捉不到的图景,便得利用相机,来完成脑海中的意象:
“我是先在脑海中形成了意象,然后再在现实天下中实现它。我以拍照来确认我的意象,作为一种证明。常日,拍照只须要非常短暂的快门韶光。但在我这里,怎么说呢?要去融化韶光,要把运动融化成某种东西,某种超出了我的人眼视觉,但相机可以捕捉到的非常独特的东西。”
杉本博司曾经向采访者展示他的大画幅拍照器材,说是装备也不为过。那是一台巨大的美国产木质老式折叠厢式相机,调度镜头时,须要把镜头赞助固定在相机底座的凹槽上。为了合营这台相机,杉本博司定制了一整套赞助拍摄装备,从滤光镜到不同焦距的镜头,还定制了海绵缓冲垫和专门工具箱用来装这套设备。拍完照的底片,会拿去自己的事情室冲洗。关于这套拍照技能,杉本自己也说过,要达到这个效果,配齐这些可不随意马虎:
“可能大家会以为显影很随意马虎,用一样平常的方法去冲洗大画幅照片,无论如何都无法呈现出均匀的画面。透明度极高,没有一丝云的画面是最难的。如果画面不足清晰均匀,那就没法说这是空气的照片了。以是我花了约十年韶光制造了一套完美的冲洗设备。”
模糊的海景是人类原初的影象
展览中展出的《放电场》系列,则是杉本博司对付底片感光效应所作的一场测试。没有利用相机而是用能产生40万伏电压的范式起电机,给金属球充进十分钟静电,另一真个负极则是一张金属台面,上面摆放有底片;充电后的金属球作为阳极,打仗作为负极的金属台面的瞬间,电流在底片上留下痕迹。冲洗后,就得到了玄色背景上闪电般的白色电光。本次展览中的另一件作品《笔触印象,心经》也是对付底片显影效果的实验。疫情过后,杉本创造许多尘封的底片已经变成了废片,便用羊毫蘸取显影液,在废弃的底片上缮写《心经》。奇妙的反应让这些笔墨显影后,保持了显影和书法笔触的双重效果。
地球在产生生命前,原始海洋被小行星和闪电反复刺激。然后,才形成了稳定的大气,海洋才开始成形,生物便从海洋中孕育而出……《海景》系列,也是杉本博司人生中最主要的作品。他以自己儿时与家人前往伊豆旅行的影象为灵感,试图讯问自己作为人类的最原始的影象是什么?答案便是海景。站在大海前,他找回了自己的原初影象。“我们该当再一次看看过去的海景,站在先人的角度思考问题,希望我的作品可以让人类毁灭自己前,反思自己的所为。”
杉本博司的海景,险些已经是一幅幅纯粹的抽象画,从白天到黑夜,海面与天空逐渐相融,变成一片激烈但静止的灰色;比起概括性的绘画措辞,杉本博司拍摄的海景中的细微之处也令人动容,这是人类之古老共鸣。海景,并非以人类中央为视点,因此地球为视点去试图靠近的画面。如果人在地面上最远能看到哪儿?那便是海平线吧。相信在展览中遇见这些作品的不雅观众,都会从这原初的海面上得到自己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