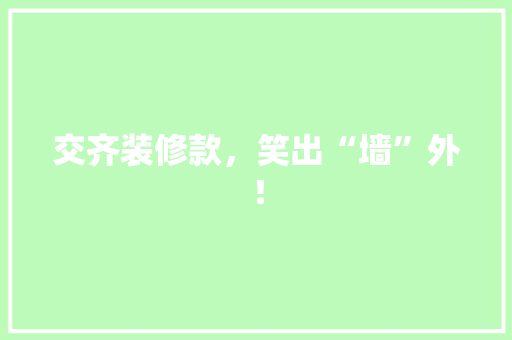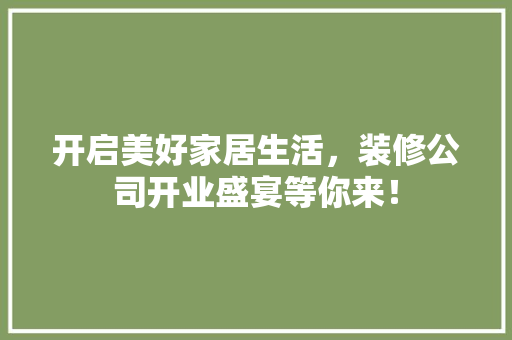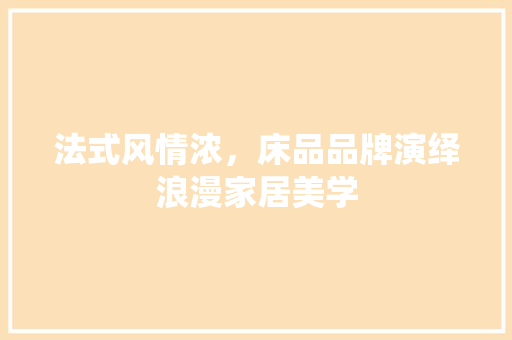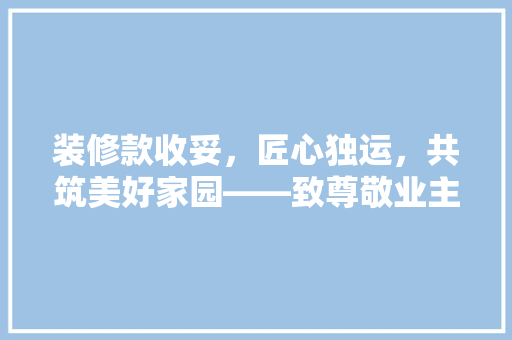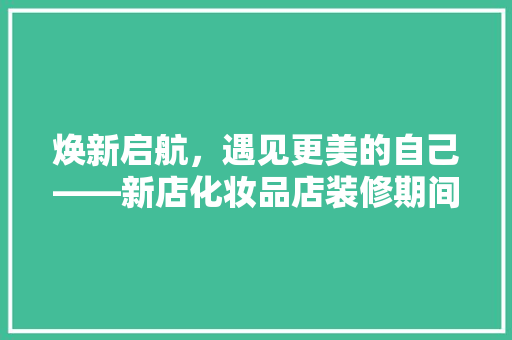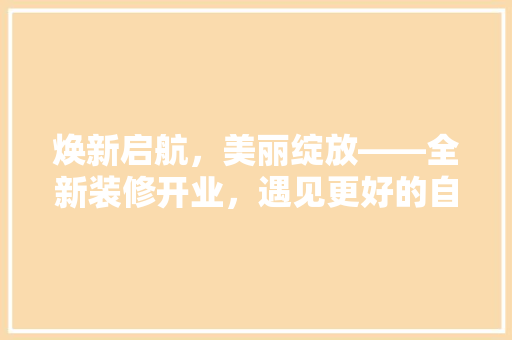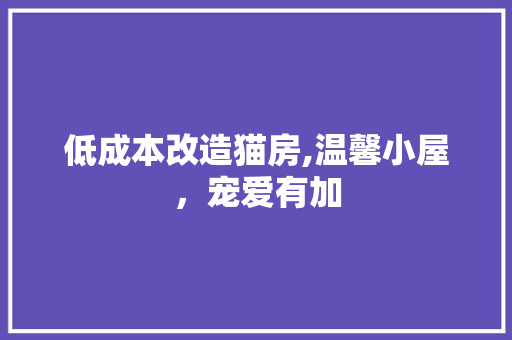哲学园鸣谢
泰纳 著 黄艳红 译

按:本文选自法国历史学家伊波利特·泰纳《当代法国的起源》(黄艳红 等译)“作者序”,吉林出版集团有限任务公司,2018年版。
……………………
1849年,21岁的我成为选民,为此我深感困惑,由于我必须选择15~20名议员,而且,按照法国人的习气,我须要选择的不仅是人,还有理论。按照别人的建议,我可以成为君主派或共和派,民主派或守旧派,社会主义者或波拿巴主义者;但所有这类派别我都不是,乃至我本人也什么都不是,有时候我真倾慕那些笃信自己已然成为某种角色的人。在对各种学说略加理解之后,我以为自己的思想中可能有某种空缺。在别人看来很有根据的情由,对我却不是这样;我不能理解,为何人们能在政治中依据自己的偏好来作决定。我所理解的那些信念武断的人,他们构想一部宪法就彷佛造所屋子,凭借的是最美好、最新颖、最大略的图纸,不过这种设计图有好几种:侯爵的私邸、市民的寓所、工人的住宅、部队的兵营、共产主义者的法兰斯泰尔,乃至还有野蛮人的营帐。每个设计者都这样评论辩论自己的图纸:“这便是人类真正的寓所,也是每个故意识的人唯一的居住地。”在我看来,这样的见地很不可靠:我认为,个人的喜好不具有威信性。我以为,一所屋子不能为建筑师而建,也不是为了建屋子而建,而是为即将居住个中的主人而建。
然而,征询主人的见地,将法国公民未来的住房图纸呈交给他们,这是显而易见的表面文章和蒙蔽手腕:在这种环境下,答案始终是由问题决定的,其余,纵然答案是非逼迫的,法国也不会比我更有能力给出答案,由于1000万个无知者依然形成不了一种认识。迫不得已之时,公民在哀求给出见地时能说出他们喜好哪种政府形式,但不是他们须要确当局形式;只有在实践之后才知道:须要韶光去考验政治寓所是否舒适、坚实、足以抵御恶劣景象,是否适应民风、不同的事情、公民的性情、他们的各种特点以及冒昧行为。然而,事实已经证明,我们从未对我们的政治寓所满意过,80年的韶光里,我们已经13次拆毁和重修它,但所有重建都是徒劳,我们依然没有找到得当的寓所。如果说别的公民更为幸运,如果说某些国家的政治寓所更为坚实并且维系已久,那是由于它们因此独特的办法构建起来的,它们以最初的厚实坝基为核心,以某个古老的中央建筑为根本,这个古老的建筑历经数次修补,但一贯保存着,其扩建也是根据居民的须要,通过反复摸索而逐步展开的。所有这些政治寓所中,没有一个是根据某种新图纸,参照单一的考量尺度而在瞬息间建成的。大概该当承认,要建立牢固的政治寓所,没有别的办法;须臾之间发明一部得当且持久的新宪法,这个任务非人类思想能力所及。
总而言之,我所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有朝一日我们能创造我们须要的那所屋子,那绝不会是按照时髦的方法创造的。我强调的是“创造”它——如果它存在的话—而不是从口头上鼓吹它。从这一点来说,我们的偏好毫无浸染,自然和历史事先已经为我们作出了选择。一个民族所能进入并能“逗留”的社会和政治形态,并非民族的仲裁者所能摆布,而是由民族的性情和历史决定的。纵然在最些微的细节上,这种形态也该当以活生生的特性为依据来塑造——它正是要利用到这些特性之上,否则它就会分裂瓦解。因此,如果我们能够找到我们的社会政治形态,那只能是在我们进行自我反省之时,而且,我们对自己的认识越准确,便越是能厘清哪些东西对我们是得当的。以是,对付通畅的办法,我们该当反其道而行之,该当在制订宪法之前核阅一下这个民族。当然,这种核阅事情比制订宪法的过程要长得多,也困难得多。这个伟大的民族饱经风霜而生存至今,为了全面准确地认识它,人们付出了多少韶光,进行过多少研究,揭橥过多少不断改动的见地,在思想和行动的各个领域内又有多少探索、付出了多少经年累月的费力!
但是,若要避免凭空推理之后的虚妄建构,舍此别无他途,至少对我自己而言,我决心只在对法国进行研究之后,再动手探求某种政治见地。
何谓当代法国?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应理解这个法国是如何形成的,最好是作为一个察看犹豫者目睹其形成过程。18世纪末,法国经历了一个变体过程,如昆虫蜕皮一样平常。它昔日的布局解体了,它自己扯碎了最宝贵的组织,堕入致命的痉挛中。接着,在几番抽搐和一阵难以忍受的麻木之后,它开始规复。但它的布局已经不一样了:经由一次无声的内部改造,新法国取代了旧法国。到1808年,所有主要特色都已终极确立下来:省、区、县、市镇;而其外部的分裂和缝合此后也丝毫未变:教务专约、民法典、法庭、大学、学院、省长、行政法院、税收、税务官、审计法院、整洁划一的中心集权式的行政机构及其紧张机关,所有这些都是一样的;贵族、资产阶级、工人、农人,每个阶级从此都有了今日我们看到的境遇、意见意义、情绪和传统。因此,新的创建既稳定又彻底,它的构造、本能和特性事先就已划定其思想和行动的领域。在这个新创建物的周围,其他的民族,无论早晚,都实现了这种从封建国家向当代国家的转变,但它们都比法国要谨慎,而且有些民族取得了更好的效果;这种缓慢孵化的进程是普遍的,乃至是自发的。
但是,无论是新形态还是旧形态,弱者始终受强者蹂躏。有的民族转化得太慢,它们的邻人却能羽翼丰满地率先从蛹中破茧而出,这样它们就只好受邻人支配了。但转变过于剧烈和迅速的民族同样很不幸,由于它难以达到内部的平衡与和谐,而且,由于其领导机构行为过度,其深层器官发生变异,其维系生命的养料逐步枯竭,因而注定会失落去理智,陷人虚弱无力的田地,而它的邻人却更为平衡、更为康健!
在法国于19世纪初形成的构造中,它的当代史的一些紧张标志线已经勾勒出来了:政治革命,社会乌托邦,阶级分裂,教会的角色,贵族、资产阶级和公民的行为办法,哲学、文学、艺术的发展、定向和偏移。这便是为什么我们要理解当前的局势时,总会把目光投向旧制度酝酿大革命的那场恐怖的分娩危急,以及孕育出新制度的那场大革命。
旧制度、大革命、新制度:我将考试测验准确地描述这三种状态。在此我斗胆声明,我没有其他的任何目的,请许可一个历史学家像自然主义者一样事情。我面对自己的课题就像面对一个昆虫的蜕变一样。其余,蜕变这一事宜本身就是非常有趣的,该当对它本身进行稽核,不必费力去排斥我们内心的想法。摆脱了各种成见的好奇心才是科学的好奇心,它会全力关注那些导致这令人震骇的事宜的各种隐秘力量。这些力量是各个群体的境遇、激情、思想和意志,我们能够认清它们,乃至能丈量它们。它们就在我们眼底下,可资我们利用的不止是暗昧的预测、臆想和朦胧的征象。由于某一特殊的幸运,我们可以窥测人本身,以及他们的外表和内在。旧制度的法国人离我们的视野还非常贴近。我们每一个人年轻的时候都能与那个已然消散的天下的幸存者往来。他们的一些寓所保存至今,里面的房间和家具还保持原样。借助房间里的支配和版画,我们可以重温当时的家庭生活,我们能看到当时人的装扮服装、仪态和举止。
通过他们的文学、哲学、科学、日记和通信,我们能够重现他们的全部思想,乃至他们的亲密交谈。30年来从公共和私人档案中面世的大量回顾录引领我们从一个沙龙走向另一个沙龙,我们将能身临其境。外国旅行者的信件和日记,则以个中立的描述,改动和补全这个社会的自画像。这个社会会商论它所关心的统统事务,除了那些它认为当时人以为乏味和熟习的东西,除了在它看来太技能化的、平庸乏味的东西,以及那些涉及外省、市民、农人、工人、行政和家务的事情。我打算补充这些疏漏,我想认识法国,而不止是那个有教养有文化的法国人的小圈子。
承蒙毛里(Maury)师长西席襄助及布塔里克(Boutaric)师长西席的宝贵指示,我得以详查旧制度末了30年中浩瀚督办、商品税税务官(directeurs des aides)、总包税人、法官、各个级别和各种类型的职员和个人的手稿文献及通信,有关宫廷各部门的报告和记录,176卷三级会议的会议记录和文稿,1789~1790年军官们的通信,宗教事务委员会数百箱文件中的信件、报告和详尽的统计资料,1790~1799年各省行政机构和市政机构与部长们的94札通信,1801年底在任的国务参事的报告,执政府、帝国和1823年之前复辟期间省长们的通信,以及其他很故意义但不为人知、实际上大革命史学尚未见过的文献。这些文献至少能向我们展现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外省小贵族、教区神父、男女修士、城市中的状师、市政官员和市民、乡间诉讼代理人和村落落的管事、农夫和工匠、军官和士兵。这些文献让我们更为贴近地详尽不雅观察普通人的生存状况,如教区神父住宅内部的陈设,修道院和市政会议的内部运转,工人的人为,野外的物产,农人的税负,征税员的事情,领主或高等教士的花销,宫廷的进出场面和礼仪。正是由于这些文献,我们能给出准确的数字,能知晓一天中每小时的事情,乃至能说出一次盛宴上的菜单、复原一个华美的装扮台。我们还知道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穿过的裙子的格局,它们按日期标示在纸上;此外,我们还能想象一位农人的衣着,仔细描述他的面包,说出制作面包所用的各种面粉的名字,并知道一斤面包他须要花几毛几分钱。借助这些材料,我们险些能够成为那些历史创造者的同代人;通过追踪档案馆中那些发黄的纸张上面的迂腐字迹,我将考试测验让这些创造者再度年夜声陈词。(1875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