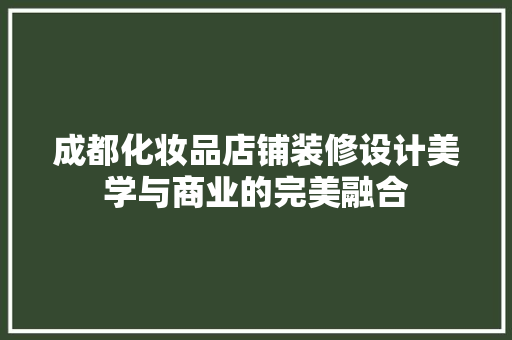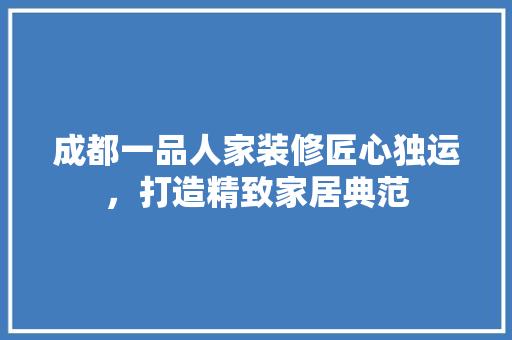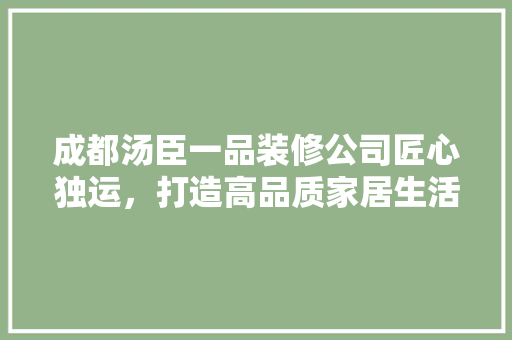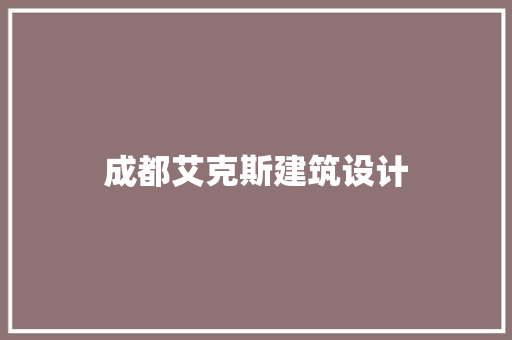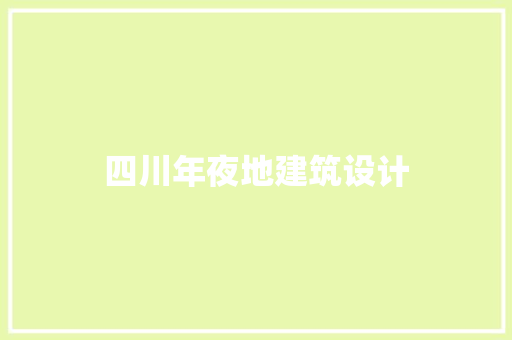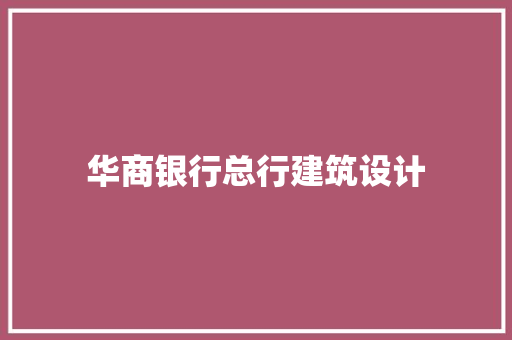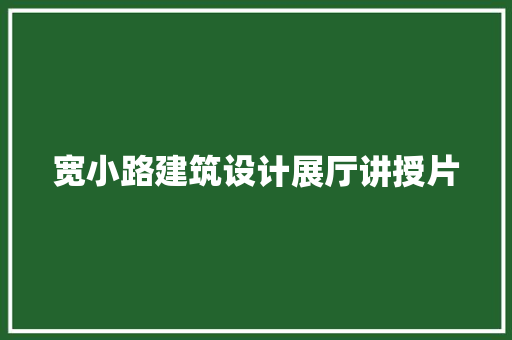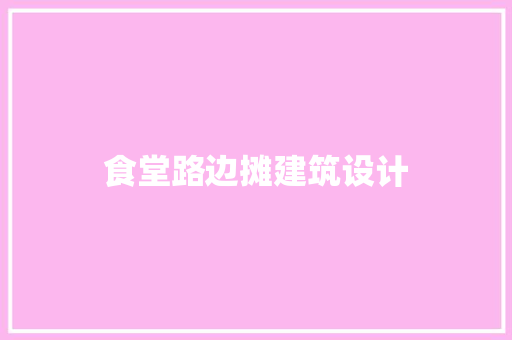澎湃新闻 王基炜 制图
我叫保罗·赛维斯(Paul Sives),来自英国,是一家工业技能公司的卖力人。1992年我以做事工程师的身份随公司到北京和成都出差,那是我第一次拜访中国。当时我们先后访问了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末了才来到中国,为成都的一家有限电视公司供应技能支持。我记得我们当时下榻在成都唯一一家五星级酒店,从酒店窗户往外看,这座城市看起来非常古老,四处是自行车,高层建筑很少。

之后,我又在亚洲生活了几年,一开始在新加坡,后来去了韩国,我的事情内容一贯与中国有关,以是常常须要出差到中国。2000年前后我回到英国,帮助总部在中国成立一家分公司,我们的团队先后稽核了上海、广州、成都,终极决定在成都落脚。然而,公司起初的合伙关系处理得并不顺利,终极我们决定买断互助伙伴,成为一家外商独资企业。
在投资洽谈的过程中,我逐渐喜好上了成都这座城市,于是,企业正式成立后,我决定永久移居到中国连续我的生活。
对我来说,成都是一座非常清闲的城市,中国的许多城市与成都比较都更加“弗成一世”。虽然现在不比以往,但这里的生活节奏仍旧让人感到十分舒适。我喜好辛辣的食品,四川的饮食习气非常对我的胃口,我还在这里碰着了我的妻子。奇迹、家庭、生活,这些都成为了让我留下的情由。
其余,川渝地区的经济环境在过去几年来也改进了很多。一开始在这里做生意,国际货色运输的不便曾经让我们非常头疼,由于西南地区地处要地本地,国际航班在当时寥寥无几,最佳的运输办法是用火车将产品运至上海后经由港口或航空港运出,非常耗时耗力。后来,成都的根本举动步伐开始迅速升级,空运也便捷了许多,货运做事能力大幅提升,办理了不少国际公司对外出口的难题。
川渝地区家当链完全、经营本钱低
传统意义上,重庆重工业更发达,成都侧重技能家当,但现在情形完备不同了,两地家当逐渐多元化,竞争关系明显增强了。川渝地区近年来的科技发展非常迅猛,以电子科技大学为首的几所精良院校,培养了一批有实操能力的电子行业人才,能在很大程度上知足川渝地区的须要。
有人认为东部沿海城市的均匀薪资水平很有竞争力,能吸引全国大批人才。但那里的生活本钱也很高,许多人在奋斗几年后会选择离开,他们会去哪儿?个中有不少人选择带着丰富的事情履历来到成都定居。这便是川渝地区的上风所在,它既能为新手入行供应良好的出发点,也能吸引中高等人才回流。
当然,我并不是说川渝地区不缺人才,好的人才永久是稀缺的。只是相对来说,川渝目前的人才缺口紧张在管理人才方面,近些年已经大有好转,往后也可以考虑通过提高职业教诲质量来办理。
川渝为什么能吸引人才?我认为这紧张得益于西南地区近20年来高速的家当发展,这里完善的家当链和舒适的生活节奏能够为人才供应更好、更稳定的奇迹发展条件和生活环境。
当初在为投资稽核时,我们创造企业在成都的运营本钱只有上海和广州的一半,这也是总部终极选择在这里落脚的缘故原由之一。现在20年过去了,虽然物价上涨,但相对来说我们的经营本钱依然是一线城市的一半旁边。这与川渝近年来逐步完全的家当链有不小关系,企业对地价和人力本钱上涨的担忧越小,就越有动力扎根在本地长期经营,并吸引高下游配套企业也入驻在附近。
坦白说,如果环球经济形势向好,川渝地区的低本钱上风大概并不明显,但一旦碰着经济衰退,情形就不同了。我定居成都后没几年就发生了2008年的金融危急,我的企业也受到波及靠近破产,在间隔破产还有不到一个月时才迎来转机。设想一下,如果我们的公司设立在上海,运营本钱过高无疑会加快我们的破产速率。这次新冠疫情中,纵然中国市场目前已经率先规复,环球经济衰退的连锁反应也会波及中国,对付企业来说,在低成本地区落脚可以减轻经济低迷期的运营压力。
10年前,我也曾担心川渝地区的地价和人口红利不会持续太久,大概几年后这里的房价也会连续翻倍,企业会被迫面临本钱提升造成的风险,人才也会由于生活本钱提高而离开。但是这些并没有发生,地方政府采纳的各项方法成功抑制了房价的通货膨胀。
这所有的统统都是一个良性循环,稳定的地价可以留住企业与人才,良好的企业生态环境能够吸引更多企业和人才加入。毕竟我们员工的薪资水平并没有与大城市有太大差别,但他们有能力在这里买房,过上品质更高的生活。
说实话,除非之后川渝地区的经营本钱上涨至一线城市的水平——虽然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我是不大会考虑离开这里的,由于企业经营还要考虑资源的可得到性问题。如果我把公司迁至东南亚或者迁回英国,当地供应商多样性不敷的问题会导致我们的运营本钱大幅提升,在成都,我们设计和生产过程中所需的电子零部件、塑料磨具、金属器材都能在省内快速获取。
政企间面对面沟通渠道有待优化
在中国西南地区做生意并不比天下上其他任何地方困难,在任何国家做生意都会碰着难题,只是不同市场对企业经营造成的困难有所不同而已。
我们目前碰着的一个困扰是与地方政府的沟通渠道不足顺畅。对付在华外资企业来说,注册手续和资格认证等方面的程序本身就比较繁芜,尤其是公司注册和股份变更这类业务,我们不得不雇佣专人全职处理这些文案事情。
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在动手办理这方面的问题,设计了专为外资做事的“一站式”做事窗口,但是这些窗口并没有让事情变得大略。大多数情形下,他们只是安排了一个会说英语的事情职员在窗口卖力收材料和问询,办理业务所需的实际步骤并未减少。提交材料之前,企业仍旧须要在政府网站查询业务办理流程,前往各个政府办公室获取符合哀求的材料。但是,许多政府网站根本无法供应最新信息,我们常常在这上面花费很大功夫。
我说的这些不但对外资企业是个问题,所有确当地公司也面临同样的困扰。重庆和成都与中国的许多城市一样,近年来一贯在努力提升营商环境,但他们真正走了多远?这一点须要多多听取企业的评价。
之前中国欧盟商会西南分会能够与成都邑市长办公室举行季度例会,这种面对面的沟通非常有用,企业在碰到制度性问题时可以与干系部门卖力人一对一沟通。很遗憾,这一机制在五年前停滞了。取而代之的是网络问政,企业在碰着经营问题时可以通过政府网站向上反响,但效果明显打了很大折扣。我和分会的同事也一贯在努力,看是否还有重启面对面沟通渠道的可能。
其余,政企沟通中的新政策解读也非常主要。中国实施的“西部大开拓”使我们受益颇多,但之后险些没有再涌现新的地区政策。不久前,我溘然听说了培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这让我非常欣喜,由于这项政策听起来能够将两城关系从竞争转向互助。
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粤港澳这样的城市群在西部并不多见,大概双城经济圈可以为西南地区带来新机遇。更主要的是,整合操持对统一区域内的法律法规非常故意义,规定的普适性可以大幅降落企业处理政府事务的本钱。年初新冠疫情后的复工过程中,我们就经历了街道、园区、楼宇复工标准不一、相互抵牾的难题,这方面的制度改革该当会受到企业的广泛欢迎。
遗憾的是,据我理解,多数外资企业对这项双城经济圈政策的详细内容并不熟习。我刚参加了在重庆举办的投资研讨会,没有人提到这项政策,我只好主动与干系卖力人联系,希望得到一些详细信息。几天后我收到了一张没有太大意义的清单,并没有解答我的迷惑。
来中国之前,我曾经在新加坡为一家大型跨国企业事情。虽然我的职责并非日常运营,但平时处理业务时我也能感想熏染到新加坡对外商的友好度很高。在建立银行账户、国际转账、企业注册、纳税等方面的程序非常直不雅观、精简、国际化,手续和政策内容的英文化程度非常高,中国如果可以往新加坡的方向靠拢,对本土的商业环境发展有百利而无一害。
任务编辑:吴英燕
校正:丁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