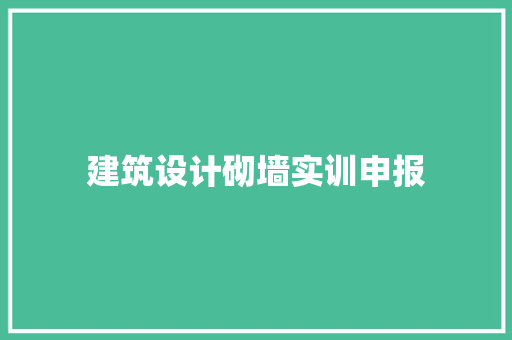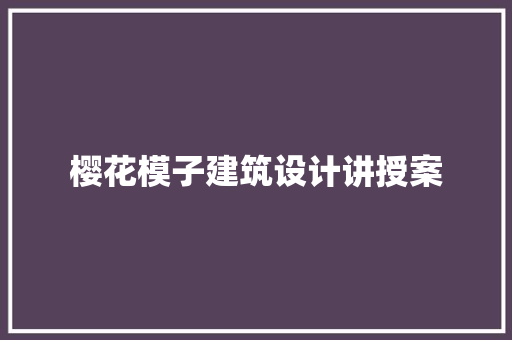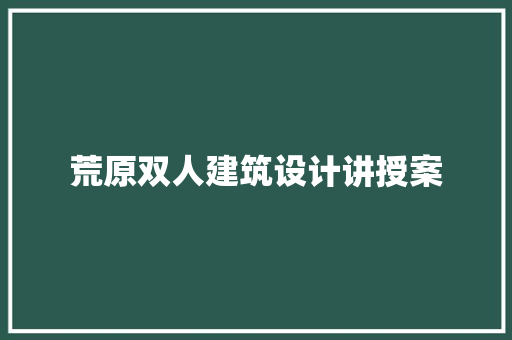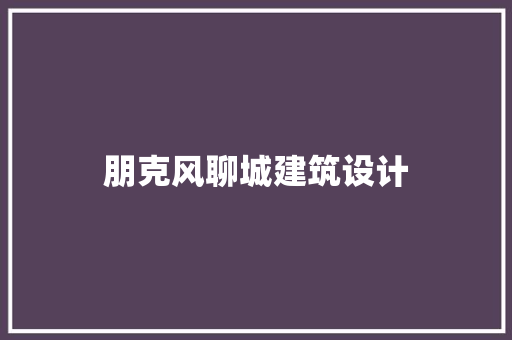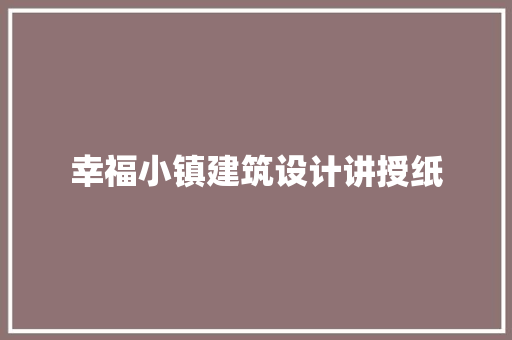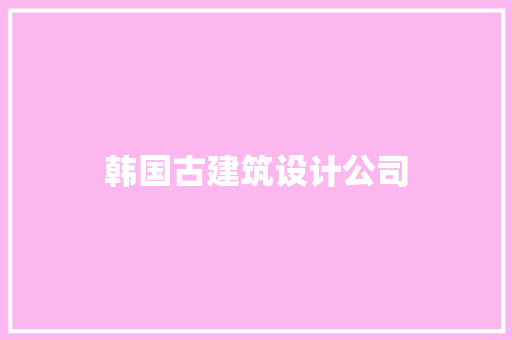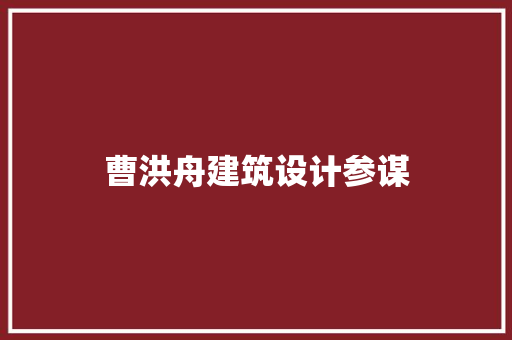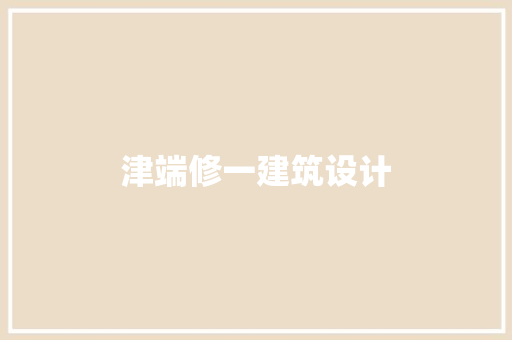一座有着65年历史的老厂房,装得下厚重的岁月,但也从不谢绝变化多端的时尚。
这处藏在机器厂里的茶空间,用茶连接起新与旧,将昔日的工业气息转化成文艺气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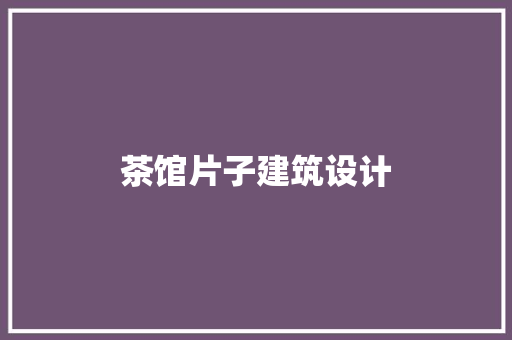
实在,电影机器与饮茶一样,皆为制造文艺。
老厂房,新文创
在充满市井烟火气的闹市区,电影机器厂彷佛很随意马虎被忽略。稍不把稳,就会走过分。
厂门前,失落去光泽的金字,就像旧衣上的标签,在韶光里逐步褪色、暗淡。
还有新绿渐浓的树荫,历历苔痕,掩映着黑瓦灰墙,缄默凝望着半个多世纪的光阴悄然流逝。
无处不在的年代感,总是会让人不禁容身去细细品读厂房的每一处细节,从砖瓦、门窗到建筑。
曾经,这里是电影机器设备的研发制造中央。轰鸣的机器,精密的图纸,盘卷的胶片,繁琐的工具,劳碌的工人……这些同黑瓦灰墙,一起构成了工业化时期的主色调。
直到有一天,机器停滞运转,厂房也成了一个时期的陈迹。繁盛褪去,然后,归于沉寂。
幸运的是,它并没有被遗忘,更没有被摈弃。
文化创意的注入,让老厂房“返老还童”,由“制造”文艺(电影)变成创造文艺,上演了一出涌当代生活的“好戏”:餐厅、咖啡馆、小酒馆、艺术家事情室,还有茶空间。
旧瓶装新“酒”,越喝越有。斑驳沧桑的陈年韵味,与新锐的时尚触感碰撞交融。温馨活泼的文艺气息和生活气息,彻底融化了机器厂重金属的冰冷与沉重,吸引着文艺青年寻寻觅觅的目光。
阿凯和壮壮,这对小夫妻,便是“驻扎”在厂里的文青。
慢活族,茶乐活
8年多前,刚从校园走出来的他们,第一次来到机器厂,就倍感亲切,以为他们“该当要属于这里”。
阿凯是武夷隐士,祖祖辈辈皆以做茶为生。他学的虽是播音,但他还是想以另一种办法延续祖业。
他们相中了个中一栋厂房,尽可能最大限度地保留原有的建筑构件,将其改造成一处可以喝茶、看书、发呆的文艺空间。
曾有一度传闻机器厂要拆迁,他们乃至都找好了新址。但,他们对这里满怀深情,不舍的是文青骨子里的怀旧情结。
建于上世纪末的厂房,为砖木构造,挑高的木质房顶和梁柱,大面的玻璃窗,都无缺地留存着原来的样子容貌,营造出敞亮大方的双层内部空间。
桌椅、橱柜的色调,以灰、褐等素朴的色系为主,力求与建筑构件的原色折衷呼应。不过,他们也不一味地强调,恰到好处地通过暖黄的灯光,来调和镇静端庄的“工业色”。
只管空间宽绰,极简主义贯穿始终,小到器物,大到茶肆,都是简洁利落的线条。
“生活很繁杂,须要做减法。”唯有减,唯有慢,方能简。这里,正是为“慢活族”而打造。慢饮茶,慢阅读,慢运动,慢生活。而阿凯也总喜好像口头禅一样把梁静茹的《逐步来比较快》挂在嘴边。
慢,并非慵
犹如电影放映——胶片匀速迁徙改变,一帧一帧画面垂垂播放,故事情节在发生发展,烧水,温杯,醒茶,冲泡,分茶,闻喷鼻香,细品慢啜,气定神闲,从容优雅。
茶与艺,“艺”起秀
他们还奥妙地将日式茶肆与庭园“嫁接”在这幢工业建筑里。
作为主体空间的延伸,走廊式的庭园虽很迷你,却绝不突兀,令初来者面前一亮。黑白相间的砾石,沿墙而植的花树,并以青石、青苔、细草点缀,小巧而精细,富有禅意。一抬眼,即是草色花影,很治愈。
角落处的庭园,为两个茶肆的“共享景不雅观”。于半开放的日式茶肆而言,为背景。与主体空间内的茶肆而言,为窗景。二者既相互独立,又有所联系,诚为妙笔。
庭园上方的房顶,移除部分的木构,用玻璃代替,让天光倾泻而下。除采光外,晴时,可赏月;雨时,可听雨。中国式的浪漫与优雅,都在这一碗茶里了。
细心的主人,还在庭园中辟出卡座。这是为年轻人量身定制的,让喝茶像喝咖啡一样,更大略,更轻松。
他们对自己精心打造的茶空间定位不但是饮茶,还是一处艺文空间。
空间里有个柜子,满满当当地码着各种各样的“杯具”。夫妻俩都有重度茶器网络癖,是妥妥的“茶器控”。他们热爱旅行,每到一处,都会包罗各式茶器,留作纪念,如有朋友看上,他们也会年夜方地割爱。
对付器物,与其说是喜好,不如说是一种敬畏。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还扮演着守艺人的角色:他们专为传统手工艺设计开辟了融展示、互换为一体的灵巧空间——既可喝茶、陈设茶品,也可举办小型展览、艺术分享会,成为手艺人、艺术家们的新“秀场”。
机器厂里的茶光阴,无时不刻都在制造文艺。
来源:茶道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