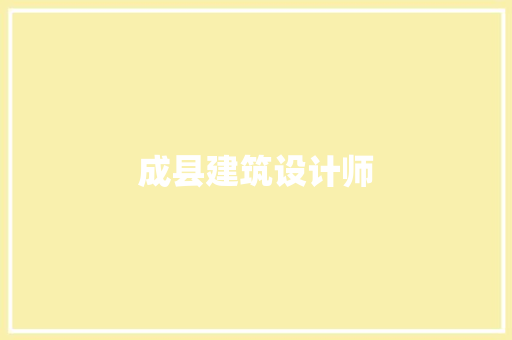文|王丹妮
编辑|胡大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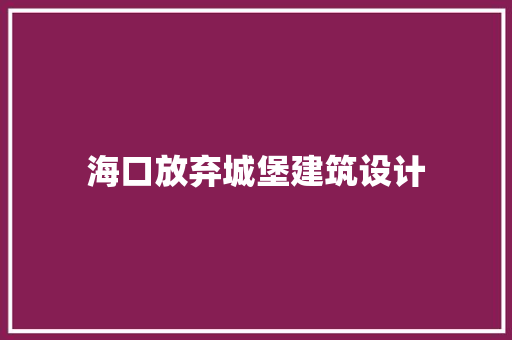
张素英正在建造一座“城堡”。 图片来自网络。
废弃的砖洞里一片漆黑。 张素影把一些衣服塞进蛇皮口袋里,和被褥绑在一起,绑在了背上。 她左手拎着塑料袋,右手拿着喷鼻香烟,朝后山走去。
“那边……更高一点……”她说。
在甘肃省陇南市成县这个村落落里,张素英是一个神秘的外来者。 四五年前,她开车来到这里,在一个废弃的砖窑里定居下来。 她从垃圾场捡起建筑垃圾,与石块、瓦片、水泥稠浊,一点一滴盖起一座六七米高的屋子,歪七扭八,像一座“城堡”。
张素影不爱说话。 村落里没有人知道她是谁,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她为什么建造这所屋子。 直到2017年5月,从事绘画和记录片拍摄的当代艺术家孟小伟才有时创造了这座建筑和这个女人,并开始了长达一年多的视频拍摄。
孟小伟对张素英只有一些基本的理解:她60岁出头,从鄂渝边疆流落到甘肃,丈夫已经去世,在家乡有一个女儿。
2018年尾月,张素英被送往当地接济站,未落成的“城堡”被铲车夷为平地。 在救助站待了十几天后,张素英又回到了砖窑,末了再次离开,失落踪了。
从接济站回来的那天,有村落民看到张素英站在废墟前哭了一个多小时。 一位村落民蹲在一堆石头阁下吸烟。 他看着她,道:“没什么。”
孟晓伟将一年拍摄的素材剪辑成记录片《张素英的《城堡》》来记录这一过程。 他借这个影像作品提出疑问:为什么会涌现张素英这样的人? 为什么没有社会福利制度为她供应保障? 我们对无家可归者的态度是什么?
以下是孟晓伟的口述:
孟小伟手绘的“城堡”构造图。 照片由受访者供应。
造屋子
我在甘肃省陇南市成县有一个事情室。 我白天画画,晚上喜好开车到处走走。
2017年5月的一天晚上,7点旁边,当我快到滨河路尽头时,远远地看到一个很高的烟囱,以为是冶炼厂。 到了那里才创造,这是一座废弃的砖窑,阁下矗立着一座六七米高、歪歪斜斜的三层小楼,就像一座城堡。
我很惊喜,哦,这里怎么会有这样的建筑呢? 它蜿蜒而波折。 它与当代建筑的钢筋混凝土构造完备不同。 另一个特点是它利用的材料是建筑垃圾,比如碎瓦、空心砖和旧门板。
楼的底层有一扇50到60厘米宽的小门,人要弯腰才能进去。我凑到门边看了一眼。 里面漆黑一片,隐约能看到一张赤色的折叠沙发。 我绕着大楼走了两圈,等了十分钟,没看到人,就回去了。
第二天白天去的时候,看到一个女人呆呆地站在门口的火炉边,阁下躺着一只哈巴狗。 她转头看着我,面无表情。 我见她不想说话,点点头,微笑着离开了。 虽然我还没有决定是用图片还是视频的形式来记录,但我对这座建筑和这个人很感兴趣,打算长期不雅观察,逐渐理解。
接下来的一段韶光,我会开车去看看,每次勾留十分钟到一个小时,用手机拍一些照片和视频。 她没有抗拒被拍照,但她也不理我。 她偶尔说的几句话都暗昧不清,由于她的牙齿全掉了。 再加上她的外国口音,我很难听清楚她说的话。 我花了几个月的韶光帮她修屋子,陪她吸烟,讯问附近的村落民,然后我逐步拼凑出她的人生故事:
这名女子名叫张素英,今年60岁出头,自称来自位于湖北省和重庆市分边界上的新乐乡。 她有一个女儿。 当她女儿五岁的时候,她就离开了家。 有一次她丈夫出车祸,她回来了,从此就一贯在外流落。 大约四五年前,她开车来到成县,开始利用废弃建筑材料修缮房屋。 她操持在2018年3月之前盖好屋子,“修睦后就住进去”。
张素英吸烟。 照片由受访者供应。
我去看张素英的韶光不规律,但每次见到她,她要么在楼上打水泥,要么在搬石头。 和水泥、去瓦砾堆里捡材料、在屋子上堆石头……张素英日复一日地重复着这些步骤,无论下雨还是下雪,过年和节假日也一直歇。
两年前,有村落民来看望张素英的女儿,带她到县城用饭,希望能带她回老家。 但张素影却并不高兴。 女孩呆了四五天,就离开了。 她留在这里连续盖屋子。
我多次跟张素影说:“别再建了,够了。”
“是的。” 她点点头,什么也没说。 几天后我去看了一下,创造屋子又增高了20厘米。
“浩气”
张素英的家间隔附近的一个村落落不远。 听几个村落里的妇女说,没事的时候就会去家里看看。 当他们看到张素英在三楼楼顶拐角处搅拌水泥时,他们从下面喊道:“天啊,你又爬这么高了,你看……天啊,连小伙子都顶不住了。”大石头……”张素影仿佛听不到,连续用手当尺,比划着把石头找平。 她用碎石把大石头压平,再用砖把碎石捣实,把缝隙里倒泥土,用手把泥抹平,让石头粘在一起。
不修屋子的时候,张素英就去地里帮村落民干活,不说一句话,也不要钱。 她干完活就走。 几位村落民浮夸了素英的“吃苦能力”和“能力”。 一位村落妇说:“我们三个人都比不上她。”
我一开始也给过张素英钱。 我从口袋里拿出它。 有时给10元,有时给5元。 第一次,我拿出50块钱塞到她手里,“买根烟,或者洗头洗衣服之类的。” 她一开始是武断不要的,但再问了一遍之后,她还是接了过来,放进了自己的口袋里。 。 后来听村落民说,她把钱捐给了附近村落落的无家可归者。
张素英吸烟,随身携带打火机和一包代价四五块钱的喷鼻香烟。 熟习后,她常常递烟给我。 吸完一支后,她就会塞给我另一支。 张素英也很爱干净。 事情前,她必须戴上橡胶手套和围裙。 阳光好的时候,张素英就端一盆水放在门口的炉子上,把头发洗干净,干后仔细梳理,有时还扎成两条辫子。
张素英住的砖窑里堆放着很多旧衣服。 她穿不了那么多,但她以为好看,就选了。 我建议把衣服像展览一样挂起来,但她不同意。 “堆起来就发霉了,咱们把它们挂起来晾干吧!
” 她以为道理很对,就拿起一根绳子,把衣服挂了起来。 她在色彩缤纷的衣服中走来走去,说了很多话,见告我这个好看,那个也好看。
张素影捡到的旧衣服。 照片由受访者供应。
我觉得她有一种“崇高的精神”,对生活有一定的品味和追求。 普通无家可归的人建造一所可以遮风挡雨的屋子。 张素英已经盖了四五年了,还在加砖加灰,彷佛有钱人家要盖屋子一样。 与层层分隔的普通建筑不同,“城堡”内部的构造蜿蜒弯曲,凹凸不平,转角处被整洁绑着的树枝隔开,有点少数民族的觉得。
我以为张素影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没有更多的须要,而且很富有。 她谢绝了我和村落民给的钱,非要给她,面无表情地收下,从不说感激,也不讲究世俗意义上的礼貌。 她不爱说话,看上去对统统都漠不关心,但碰着不恰当的言语,她就会反击,态度很好。
有一次,和我一起来的一个女孩和张素英开玩笑说:“女人不能吸烟。”
“可我是个女人啊!
” 她嘴里叼着烟,声音更大,语气也更武断。
张素英很少回答有关家乡的问题。 有一次我问了良久,她终于透露了一些零散的信息。
“你结婚后和你老公关系不好,然后就跑了是吧?”
张素影轻声“嗯”了一声。
“他不爱你了吗?”
“爱!
” 她立即对我喊道。
“哦……那是由于你不爱他,对吧?”
张素影的声音规复了往常的低沉,看也不看我一眼,说道:“我不爱他。”
我和几位艺术家商量发起一个募捐活动,送张素英回来,帮助她在家乡盖屋子。 我多次把这个操持见告张素英,她既不同意也不谢绝。 她低下头,用鞋子来回摩擦泥土。
张素英的屋子被叉车推平了。 照片由受访者供应。
“屋子被拆了”
2018年尾月,我去海南过年。 我让一个小兄弟定期帮我看望张素英,并用手机拍一些照片。 第一天去没看到人,以为她出去拉建筑材料,没把稳。 接下来三天,张素影就消逝得无影无踪。 屋子变成了一堆瓦砾。 有人说是政府派人来拆的。 两个铁锅还在瓦砾堆阁下,里面装满了雪。
小弟弟跑去讯问村落支书,得知张素英被送进了福利院。 当他去那里时,他找不到录取记录。 打听了一两天后,他得知她被暂时安置在救助站。 “送她去福利院是要费钱的。” 接济站事情职员表示,没人乐意付钱,他们也不接管。
当她看到张素英时,她正躺在救助站的铁架床上。 弟弟对她说:“把你的屋子拆掉吧!
”
“我没拔出来……我出来的时候也没拔出来……”张素影坐起身来,微皱着眉头,茫然地看着他。
大约十天后,小弟弟拿着食品去救助站看望张素英,但没有看到任何人。 门口的保安说,他看到她在扔垃圾时跳过栅栏逃跑。
小弟预测张素影可能又回到了原来的砖窑。 他跑到那里,但没有看到她。 两天后他回去,创造她回来了。 救助站与砖窑之间有一条5公里的公路。 村落民估计她这两天一贯在找路。 “走路时,她坐在车里,认不出她来了。”
刚回来的那天,村落民们就看到张素英站在废墟前哭了一个多小时。 她的衣服被火烧掉了,地上留下了玄色的痕迹。 收抹布的人也捡起了水壶。 一位村落民蹲在一堆石头阁下吸烟。 他看着她,道:“没什么。” ”
待了四五天,张素影就打算离开。 小弟弟走进岩穴,瞥见她用绳子把蛇皮包和被子绑在一起,扛在肩上。 她主动跟弟弟打呼唤,“我走了。”
“你要去哪里?”
“去更高的地方吧。” 说完,张素影出了岩穴,顺着路往前走。
正月初十,我回到陇南,想再次探望,张素英却又回来了。 她仍旧住在窑洞里,赤色的沙发换成了网状电脑椅,门口还搭了一个火炉。 我问她还连续修屋子吗? 她反问:“我还怎么修炼?”
屋子没了,张素影的生活空虚了。 她每天坐在废墟前发呆。 砖窑的烟囱高高耸立,身后是连绵起伏的群山。 后来我去找她,却不见她的踪影。 村落民们说,她走了,把剩下的柴米油盐都给了他们。
这一次,张素影再也没有回来。
张素英和她的新电脑椅。 照片由受访者供应。
神秘
直到今年,我还常常开车绕着砖窑转,看看能不能再碰着她。 张素影成了我心中的一个谜。 我很遗憾没有讯问有关她的更多个人信息,也没有留下她的手机号码。
作为当代艺术家,我更多关注以张素英为代表的“流浪汉”群体及其背后的社会问题,很少打听她的个人隐私和生活细节。 拍完张素英被送到救助站后,我以为主题突出了,就决定拍一部记录片。 可能和周浩这样的导演拍的电影不一样(记录片导演,有媒体评价周浩电影的主要特点之一便是可看性强,故事冲突明显)。 我不是在讲故事,而是用图像来提出问题。 ,传达思想并引起不雅观众思考:为什么会涌现张素影这样的人? 为什么没有社会福利制度为她供应保障? 我们对无家可归者的态度是什么? 我只是提出问题,不雅观众须要自己思考答案。
在视频的末了,我利用了独白式的字幕:
人类生命的深刻内在实质是灵魂的自由。 我认为她的灵魂与她自己是分开的。 正如加缪所说,“我的灵魂与我的间隔是那么迢遥,但我的存在却是那么真实”。 无非便是她的贫穷,而她生命中的每一天,始终伴随着她,她阴沉、悲哀、不安,乃至错愕、小心翼翼,乃至无法抗拒随韶光降的去世亡,但她却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一个被别人视为荒诞的悲哀又阳光的“笑话”。
这是我心底的一声嗟叹,我写得很大略,也不担心会不会太主不雅观。 严格来说,它可能不算是一部记录片,而更像是一部独立的影像作品,是我表达想法的载体。 为了突出主题,我在影片的构造上做了一些设计,但在全体拍摄和沟通的过程中,我是客不雅观的。
这部记录片放映了几次后,我收到的反馈褒贬不一。 有不雅观众以为我们吃饱了没事干,就去给无家可归的人拍照片。 前两天,一位退休县领导向我讲述了这部影片,“张素英走了,城堡也拆了,受益的只有你,由于你拍了记录片。” 这种说法我听过很多次了。 但我心里清楚,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花费张素影。
除了被这座陌生的“城堡”和张素影背后的社会问题所吸引之外,我以为这次拍摄对我来说也是一种生理上的调度。 我常常以为我和张素影很像。 她不在乎别人的意见,只这天复一日地盖屋子; 我在西北的一个小县城,做一些没人懂的当代艺术,画一堆不赢利的画。 “这是为了什么?” 我不知道,但我一贯坚持。
我想过和陕西的几位艺术家一起发起一个“探求张素英”项目,但我没有呼吁。 如果再见面,我会给她看《张素英的《城堡》》,不知道她会有什么反应。 现在,我每隔一段韶光就回去一次,总以为奇迹会发生,张素影就在这里。
免责声明:文章内容如涉及作品内容、版权图片或其它问题,请在30日内与本号作者联系,如反响情形属实我们将第一韶光删除任务文章。文章只供应参考并不构成任何投资及运用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