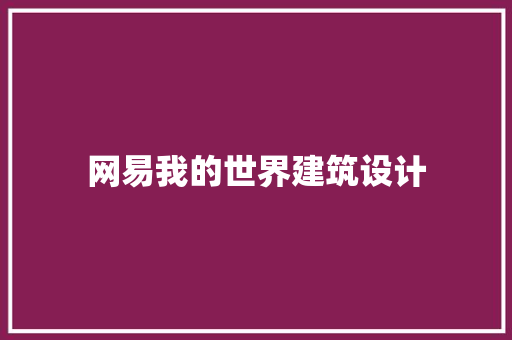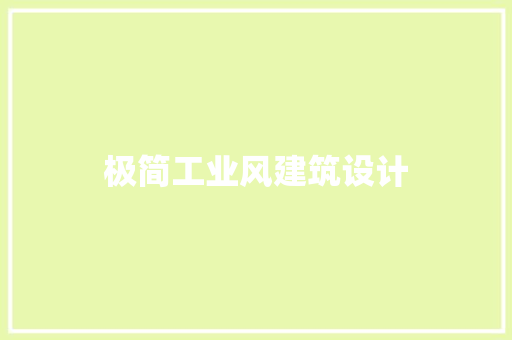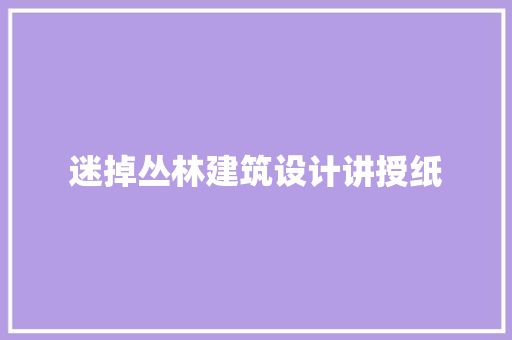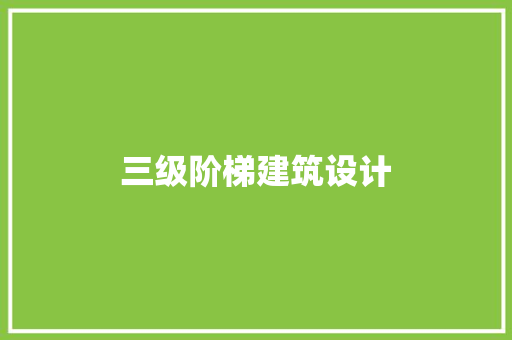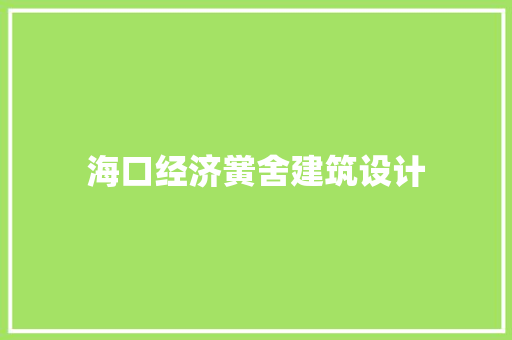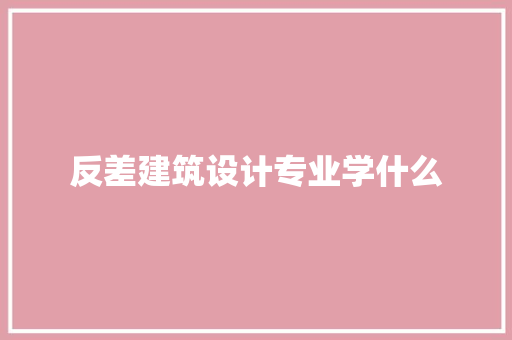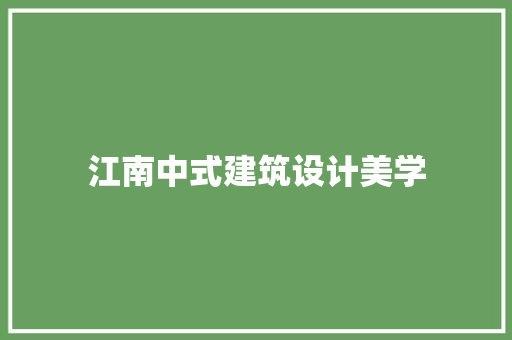难忘当年“筒子楼”
运城市教诲局 张俊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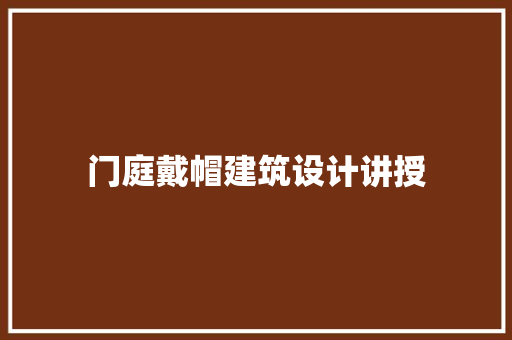
2014年,路胜利局长到市教诲局履新后,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地对局机关办公楼和大院进行了环境整治,美化、亮化、文化、硬化和绿化全面到位,使机关面貌焕然一新。个中最大的举措,是将机关后院两栋破旧不堪、已闲置多年的原职工宿舍楼全部拆除,之后将后院硬化,变成了停车场,缓解了局机关停车难的局势。我在这两栋楼里先后共住过十几年。那两栋楼没有拆除前,好几年险些没人住了,我偶尔过来过去对它们的存在也未以为有什么觉得。但那天局党组会上一决定立时要拆除这两栋楼了,我溘然对它们觉得好象有点眷恋了。会刚结束,我就跑到后院,楼前楼后、楼上楼下转悠了好永劫光,并用手机在各个角度照了好多相。这一转悠不要紧,却勾起了我对当年居此楼时所经历的酸甜苦辣的回顾,以及对当年居住在此楼内那些人们的怀念,特殊是人们当年生活的艰辛、窘迫和楼内所发生的一些趣事逸闻,至今历历在目,影象犹新。
机关后院的这两栋楼,均建于70年代初。东西走向的三层楼为双面楼叫北楼,靠东环路南北走向的二层楼为单面楼叫东楼。这两栋楼因所有房间呈长方形,又无洗手间、厨房和阳台,故也叫“筒子楼”。两栋楼均为“预制板、二四墙构造”的大略单纯楼,没有“防震柱”,也没“圈儿梁”,按现在的建筑标准这两栋楼都应为不合格的建筑,但在当时,城里很多机关、学校、医院的建筑大多都还为大略单纯瓦房顶、土坯墙的大背景下,这两栋楼算是好的建筑了。听说当时,运城地区从晋南地区(驻地临汾)分出单设专署(后改为行署)后,专署教诲局的办公室、人事科、计财科在专署大院办公,统称为“教诲革命组”的其它业务科室却无地方办公。专署决定在康杰中学(老校区)东北角靠近东环路的闲置地划出一块,盖了这两栋楼,并在东环路开了个大门,作为运城专署“教革组”的办公院。说是办公楼,实在办公住宿不分家,每个房间都有床,白天办公,晚上单身职工住宿。后来直到改革开放后的八十年代初,行署在“教革组”办公地的北面(也属康杰中学的闲置地),给教诲局盖起了一栋三层戴帽、门庭朝河东街的办公大楼,之后,教诲局才算有了独立办公场所,将行署大院的几个科室和“教革组”的所有人马,除仪器站、印刷厂仍在老东街外,全部搬到此楼办公。那两栋楼不办公后,就正式成了职工们的宿舍楼了。此院与北边新办公楼院之间开了个门,连为一体,成为局机关后院。
1984年秋日,我由稷山城关中学调到地区教诲局办公室上班后,局里就将双面楼三层阴面的一间房分给我作宿舍,大约15平米。我在稷山事情时,学校给两个西席一间办公室兼宿舍,而且还是很简陋的平房。之前从未住过楼房的我,现在有了这么一间三层楼上的宿舍,真是大喜过望,何况每个宿舍均配有一个三屉桌子,一张栏杆床,一把椅子,以及一个铸铁炉子配铁皮烟筒。在那个年代,单身宿舍能有这样的配备算是很不错的了!
那两栋楼上,除了一两个局级领导和八九对双职工夫妻能分到两间或一间半的宿舍外,别的单职工不管结婚与否均一人一间。有的单职工的老婆在屯子没事可干,带上孩子基本常年住在运城,一家三口或四口挤在一间房里的家庭大约有十来户;一家三代六、七口人挤两间屋、爷孙或奶孙或姐弟住高下铺的家庭大约也有四五户。
我刚调来运城事情时还是单身汉,后来结婚后的好几年我爱人仍在稷山事情。故每年一到尾月二十五旁边,我就提前请假回稷山老家过年,直到正月初六才返回。我对门住着教诲科张喜群老师和她老公运师郭校长一家,他们一家三代七口人挤在两间不到30平米的套房里,里间是他们夫妇的寝室,并兼作书房、库房和缝纫机房,外间南边窗户两边分别放着两个高下床,一个是两个儿子高下铺住;一个是下铺住着张老师年迈的父亲,上铺住着上初中的二女儿。而且外间不仅一年四季要放置案板、水缸和坛坛罐罐等生活用品及杂物,一到冬天还要再加放个火炉,一是用来取暖和,二是用来做饭、烧水。因而两间屋里可以说险些没有人站立的地方。每年尾月末,他家买下年货和蒸下白馍、炸下烧豆腐、丸子等就没地方放,加上他大女儿从外地回家过年家里根本住不下,因而很是发愁。我头一两年回家过年前,张老师总是提前不好意思地求我回家前能否把我房间钥匙给她留下,好暂时让她家两个儿子春节前后过来住上十来天,给大女儿回来腾个地方,并能临时放些年货。我非常理解张老师一家的困窘,后来几年我回家前,不等她开口就把钥匙送到她手里。此时,他们百口总是对我很感激的样子,而且每当我正月初六返回后,郭校长总要过来请我到他家饮酒,还说很多感谢的话。每每此时,我的心里总涌出些许莫名或无奈的酸楚。
那时,机关后院西边靠康杰中学的地方建有一排东西朝向的红砖瓦房,南边几间为车库,北边四间为机关食堂,个中餐厅约有30平米,有四张高高的方桌子和三四十个凳子;食堂前的小院里还有四个水泥预制的小方桌和多少石凳,景象暖和时,大多数人乐意在室外就餐。食堂有两名大师傅,还有一个买菜管灶的事务长;饭菜很大略,每顿只有一个菜、一碗汤和一个大馒头,每天的炊事费大约五角钱。那时,在机关上班的干部职工统共也就五六十名,个中绝大多数住在大院后边。除了几户双职工或带家属的职工以自家做饭为主、偶尔到食堂买上几个馍或菜外,别的约有四十来户每顿都吃食堂。每到三顿开饭韶光,食堂里总是欢声笑语,是机关职工大聚会的时候,是机关每天最热闹的时候,也是那些爱开玩笑、爱抬闲杠、能言善谝者等生动分子们大显技艺的时候,他们说的笑话和趣事,发布的新闻和小道,或者“抬闲杠”时互不相让、妙语横生的情景,每每搏得大家一片笑声,乃至有季候人“歕饭”。不过,也有偶尔不和谐的时候,有时两个爱“抬杠”的“杠头”,辩论起来面红耳赤,若话不投机每每就“变了脸”,闹得不欢而散;有时乃至还要动起手来,这时大家就不能再看笑话了,就七嘴八舌地相劝,实在弗成就叫一方硬行拉走了事!
那时,这两栋楼没有通暖气,冬天取暖和就靠生炉子。机关每年给每个职工免费分一吨“钢炭”(阳城无烟煤),几辆大卡车利用晚上拉来几十吨钢炭后,一古脑堆在办公楼后边的篮球场上,然后由后勤职员将钢炭按职工人数目测分成多少大小一样的堆,一堆大约一吨。分好后,大家抓纸蛋确定自家的炭堆。之后,人们陆陆续续将自家的钢炭转到楼上靠自家门边的楼道上;住一层的则将钢炭转到自家的窗台下。以是,本来就只有一米五六宽的楼道上,两边全是各家用砖垒起来的炭池,中间过道也就只有一尺来宽,刚能让人走过去。人走过阴暗的楼道时总是要小心翼翼,一欠妥心就有被炭池拌倒的可能。因钢炭普遍块儿大,往炉子里填时又要砸成鸡蛋大小的块儿,故楼道里常常有人砸炭,震得满楼道和楼上楼下各屋里的人都能感到,很是烦人!
而且各家砸炭的韶光都很随意,不分早晚,此伏彼起。有时凌晨正睡得好梦连连或者星期天早上还想多睡会
生炉子和管炉子都是个麻烦活,也是个技能活。我不太会生炉子,每次总是反反复复活不着。同时,我也不太长于管炉子,每每昨晚费了很大劲刚生着,第二天早上就灭了,又得重生!
而且每次生炉子总弄得满屋子都是浓烟,光靠烟筒和窗户不能及时排光,因而总要打开门、揭开门帘往楼道上排一些烟。此时,楼道上就烟雾滚滚,不仅呛得楼道上走过来的人睁不开眼、喘不上气,而且其他住户只要一开门,浓烟就迅速侵入!
弄得我每次生炉子总以为不好意思。好在各家各户都有生炉子弄得楼道浓烟弥漫的时候,大家也就都不好意思埋怨谁了!
冬天一过,不带家属、吃食堂饭的单职工们,便不再生炉子,纷纭将炉子和烟筒拆下来放到楼道自家门口;而双职工或带家属的单职工,也都将生着的炉子抬到自家门口,做饭、烧水都在上面,因而楼道上显得更加拥挤。而且每天中午或晚上一进入楼道,什么味道都能闻到,不想闻也得闻,有些味道还呛得人直打喷嚏。
春天、秋日倒也没什么,但一到盛夏,本来运城盆地便是个大蒸笼,加上筒子楼楼顶的预制板上也没啥隔热层,“二四”的砖墙又很薄,因而火辣辣的太阳一晒就透,屋里温度从早到晚都在30℃以上,而且加上每层楼道里还墩着七八个火炉,使已经十分闷热的楼房里更是火上浇油,人一上到二层就立即感到热浪迎面,纵然只穿个短袖衫,也能令你一分钟就浑身淌汗!
特殊是进入暑期那一两个月,房间里中午和晚上就像一个大烤箱,有时温度能达40℃,一进屋就让人酷热难耐,纵然立时脱光衣服也汗如雨下,浑身燥热。不管午觉和晚觉,热得人根本睡不着,躺在床上,手里拿个扇子,一直地扇上十来分钟刚迷迷糊糊睡了不到五分钟,又被热醒,浑身是汗。此时,赶紧又得抓起扇子就扇……。这样折腾十来回都睡不了一个囫囵觉。那时,落地电风扇可是奢侈品,像“骆驼牌”等一样平常品牌的都得一百元出头,像“蝙蝠”等名牌,大都在一百五以上。而那时我的人为也就48元多,除了衣食住行等开支,每月能攒上五六元就不错了,因而要想买个电风扇那可是件可望不可及的事情!
因而,盛夏的那一两个月, 好多人都是午饭后在前院办公楼一楼大厅地板上铺个凉席勉强睡个午觉;晚上只要不是刮风下雨天,就卷着铺盖爬上三楼楼顶,在那满天繁星与皎洁玉轮的陪伴和凉风的吹拂下,度过了一个个酷热、漫长的夏夜。记的有几户百口男女老少,每晚定时上楼顶过夜。楼顶上的夏夜中,每天都有乘凉人们发出的胡谝闲聊时的欢声笑语,时常还有悠扬婉转的笛声和二胡声穿过夜空袅袅而去。现在想来,那时的夏夜倒也充满了乐趣和温馨。当代人的夏夜,大家都蜗居在自家有空调的风凉的单元楼里,那种人们在酷热的夏夜虽充满无奈、却能彻夜相聚和闲聊的机会与情景已一去不复返了!
那个三层的筒子楼里,原来每层都有一间阴面靠东边的房间为洗手间,里边隔为男女厕所,男厕占了三分之二还多,有三个蹲位和二米长的小便槽,女厕则只有一个蹲位。但均因年久失落修,上水管道不是生锈堵塞,便是分裂破坏,因而我住到此楼时,男女厕所早就不知何时停用,里面堆满了各家各户不用但又舍不得丢弃的大纸箱、破桌子和烂凳子等等杂物。只有女厕里原来洗墩布的池子,与下水道还通着,因而成了各家倒污水的唯一地方。但由于池子下水口较小,加上每每有人乱往里倒剩饭、菜叶等杂物,因而常常堵塞。故,就有人用羊毫不才池塘上边的墙上大大地写上几个字:“严禁往池里倒菜叶、剩饭等杂物”。但有些人却置此标语于不顾,明明瞥见池子堵塞了,却还要往里再倒带有杂物的污水,使污水流得池子下面和楼道上满地都是。此时有任务心的人就找个铁丝费好大劲才将下水管弄通,但每每刚弄通不到半天就又堵塞了,真是烦人!
有些爱管事的人此时忍不住就要在楼道里大声骂人:哪个缺德鬼光往下池塘子里倒剩饭?你眼睛瞎了?看不到池子老堵?这样骂上几次有时也顶点事,但每每撑不了几天,骂人声就又会响起!
个中爱骂人者紧张有一中年女同道,此人皮肤较黑,爱穿黑衣服,性情泼辣,爱管闲事,且骂起人来声音洪亮,口无遮拦。由于她常常清晨天不亮就在楼道上不管不顾地大声骂人,因而免不了时常将拼音报社的一个年轻编辑从梦中惊醒。这个年轻人就对这个中年妇女很不感冒了,有一天他就用羊毫在四开大的白纸上写了一首打油诗,贴到楼道墙壁上的显眼处。打油诗为:三楼有个黑乌鸦,每天早上叫喳喳,声嘶力竭引人烦,楼上大家讨厌她!
大家看了又可笑又可气,但更多的是无奈!
因这两栋筒子楼上的自来水管多年不通水了,因而住楼上用水是最麻烦最令人头疼的事情。后院大梧桐树下有一个自来水龙头,是大院几十户人家唯一打水的地方,因而每天随时有人在此用桶接水,或直接拿上盆在此洗衣服、洗菜。清晨或晚上用水高峰时还要排队打水。住一楼的往家提一桶水还省点事,住二层、三层的往家每提一桶水都要费点劲才行!
尤其是孩子们和老年人,提一桶水上到楼上,一起上免不了碰碰磕磕,不仅将楼梯上和楼道里洒得到处是水,而且一桶水到家也就只剩下半桶了,还常常将裤子和鞋洒湿,很是烦人!
因筒子楼里的公共厕所都无法利用,因而上厕所必须到楼下北边的旱厕。住二楼和三楼上的人,尤其是老年人想上个厕所非常不易,若是碰着内急时,每每有人来不及下到一楼,就在裤裆内干出尴尬的事!
故,那时家家户户都有便盆。那些未便利下楼的老者或不愿意下楼的小者,险些晚上白天都便在便盆。以是楼道上常常能看到端着便盆往下池塘子去的人。
记的熟年夏天还闹出个笑话,有个中年男科长,是个单职工,住在三层的一间房中,晚上为图凉爽脱得精光,一个人在屋里边看书边喝茶,不到十点就将尿盆小便满了。大约十点半旁边,他听见楼道内悄悄静的,就光着身子打开门,端着尿盆蹑手蹑脚地快步走向下水口。谁知刚出门几步,一股大风从开启的窗户上忽然吹过,“咣当”一声将房门反锁住了,等他反应过来才创造没带钥匙,便顿时傻了眼。他忙钻到水房内,连续喊叫着几个男人的名字。有女人听见喊,就跑出来问啥事,科长忙说不要女人出来,要男人出来。那天我恰好还没睡,就跑到水房问咋回事,看到科长光着身子蹲在地上,一问才明白了咋回事。此时楼道上站了不少人,在大伙的嘻笑和帮忙下,我从他门上没关住的天窗上翻下去,才打开了反锁着的门,并给他取了裤子和上衣,返回让他穿上后,他才红着脸走出水房。呵呵!
那时楼里这样或类似的“笑料”常常能有发生。
1991年秋日,我爱人带着四岁的女儿从稷山调来运城事情。第二年春天,东边单面楼二层一个一间半的套间宿舍有人搬出,经我申请和争取,机关研究后将此屋分给了我。机关资格比较老点的双职工才有可能争取到此屋。此套间可以客卧分开,外边一间大约15平米,东西都有窗户;里边半间靠街有个窗户,大约有7、8平米。此屋因永劫光没有粉刷,墙壁烟熏火燎得险些成了玄色,灯管上、窗框上、玻璃上的灰尘和油腻足有一毫米厚,而且水泥地板上到处是坑,木窗框因风吹雨淋也褴褛变形,不是闭不住,便是闭住了拉不开。我和爱人整整打扫了一天卫生,之后又灰头灰脑地到街上买了半桶涂料,用了一晚年夜将此屋粉刷一新。此时,看着窗明灯亮、墙壁白净的新居,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记得搬家那天,几位同事和朋友过来帮忙,有一位百口四口人还挤在一间屋的同事感慨地说:何时我家也能住进这样的套间里!
还有一位年长的同事说,俊耀刚三十就住进了一间半的套间,不大略呀!
那天我请这几位同事到康中边上的“君乐饭店”搓了一顿,虽然花了一个多月的人为,但心情那个高兴劲是无法形容的。新居里放置了一张1.5米宽的木床、一张三屉桌以及一个钢丝床,这已经差不多够满的了,可还得再放置一个取暖和用的铁炉子。这样下来,里间能落脚的地方也就不敷一平米了,通往外间的小门也只能开一半,勉强刚能让人挤出去。外间东半为客厅,西半为厨房。我们把结婚后买的一个金丝绒面长沙发摆在靠东边窗户下,将搬家前不久借钱刚买的一台19英寸的电视机摆在靠南墙中间的一张单桌子上,又上街花了几十元钱买了一个茶色玻璃茶几,放在沙发前,这就有点像客厅的样子了!
然后在西面门边窗户下垒个砖台,将液化汽灶置于其上,窗台上可摆放油盐酱醋的瓶子等厨房用品,靠灶台南边再用砖垒了一个台子,上边放上个菜板,这样就象个厨房的样子了!
虽然做饭炒菜时满屋油烟,但晚上一家人或与客人一起坐在客厅看电视谈天时,倒也让人其乐融融、倍感温馨。过了一年多,我们又先后攒钱买了一个组合柜和一台抽油烟机。那时组合柜比较时尚,既有衣柜、被柜、书柜功能,还有几个抽屉可放杂物,另有平台可放置电视。组合柜明光彩朗,使客厅增光不少;抽油烟机安到西边窗户上后,炒菜做饭时屋里油烟顿时少了许多!
住进东二楼的小套间后,用水比原来住北三楼还要麻烦许多。由于东楼受地理位置限定,没有单独楼梯,只是在靠北边的地方与北楼二层之间建了个天桥连起来,故高下东二楼必须过天桥,必须从北楼的楼梯高下,并穿越一层和二层的西半楼道。而我住的套间又在东二楼的最南边,离天桥较远,因而高下楼要绕一大圈,十分未便利。每次从下面提一桶水上楼,要圆圆转一大圈,每每提到家里,一桶水洒得就只剩下多数桶了,而且常常洒湿裤子和鞋,令人烦恼不已。特殊是我们咬牙攒钱花了好几百元买了一台全自动洗衣机后,用水量大增,每次洗衣,先要花半个来小时,提上三、四桶水才能让洗衣筒倒满水迁徙改变起来。而且由于房间没有下水道,洗衣机无法自动排水,每次洗衣只能将洗衣机放在几块砖头上,然后将排水管置于一大铁盆内盛污水。而铁盆又每每盛不下一洗衣机排出的污水,免不了常常流得满地都是,让人惊悸失措地赶紧拿小盆从大盆里舀出污水倒进污水桶,又提上污水筒倒往位于楼道北真个唯一一个下水口。因而用洗衣机洗一次衣服非常不易,且根本不能发挥全自动洗衣机的浸染,还不如手洗大略省事。以是,除非洗被罩、床单等大件,洗衣机轻易不用。后来,见有人用绳子绑了水桶从一层往二层吊水,我也从老家拿来粗绳学着吊水,果真比之条件水上来要方便省事省力多了。每次吊水,先将粗绳一头绑在门口的铁栏杆上,另一头绑上水桶放在楼底,然后人绕行一圈下去解开水桶,从水龙头上打满水后,再将水桶提到绳子前绑好,人再绕行一圈上到楼上,用绳子把水提上来倒到水缸里。这样不仅省力,而且效率也要高许多。但这种无奈的吊水之举,不仅须要有技巧和履历,也须要有力气。我刚开始没履历或欠妥心也常常将水桶碰到栏杆上,一桶水吊上来往往只剩半桶,且溅得楼下面满地都是,令别人讨厌。老婆干这活就弗成,因而那几年每天吊水便是我不得不干的硬活。
由于东二楼那半间寝室临东环路,我们住过去之前已改为河东市场一两年了。每天早上六点钟河东市场里就熙熙攘攘、人声鼎沸了,加上东边幼师和南边康中做早操的大喇叭声,险些每天都甭想睡个喷鼻香甜安稳的“黎明觉”,使我这个爱睡
1996年底,地区教诲局在东郊集资建了机关家属院,此院四十户,大多都是二层小楼独门小院,二层楼内共四寝室两客厅,还有独立的洗手间和厨房,且楼内通自来水和下水道,冬有暖气,夏有空调。从此,我再没生过炉子,也再没有提过水、吊过水和倒过污水!
彻底告别了住筒子楼的艰辛、麻烦与窘迫,生活质量与住筒子楼比较可谓寰宇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