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媒体对“丑陋建筑”的宣布非常之多,使其一度成为热点事宜。很多建筑类网站针对丑陋建筑的评比活动也推动了这一热点的发展,导致大众将丑陋建筑的涌现当作当代建筑的乱象,以至于波及建筑界的从业者。笔者认为,对付当代的“丑陋建筑”或“丑陋艺术”,该当精确地看待和理解,并给予其精确的评价。
在日常生活中,美与丑实在是相对的。人们可以把美与丑置于一个坐标轴的两端,从丑(负轴向)到美(正轴向)形成一个整体。如此,在美和丑中间存在一个非美非丑的普通状态或者中庸状态,这便是当代城市中大部分建筑物所处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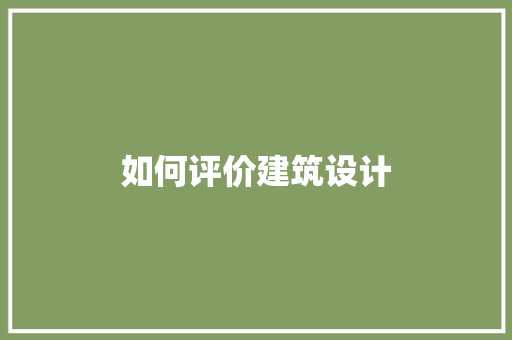
美国 弗兰克·盖里 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
大部分建筑之以是显得平庸、丑陋,笔者认为大概有两方面的缘故原由。第一,建筑物没有明晰的层次感、违背形式美规律或者形式过于具象和表面化。这类建筑因此被评为庸俗且丑陋的建筑。第二,建筑物的意义不被大众所认同或者被大众误读而导致差评。由此,可以将当代海内的“丑陋建筑”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种,建筑设计师或者甲方授予建筑物分外的意义,但这种分外意义并没有普遍性,不能被大多数人所认同,从而被大众评价为丑陋建筑。当建筑设计师或者甲方过于迁就建筑形式的象征、隐喻意义或分外目的时,就一定会涌现捐躯功能或者忽略功能的情形,从而造成建筑功能的紊乱。在这种情形下,虽然在建筑师或者甲方的逻辑里,这类建筑物的形式和意义是自成体系的,但是当其意义被大众抽离之后,就只剩下了没故意义的形式,给人丑陋又不实用的觉得。德国美学家西奥多·里普斯(Theodore Lipps)说:“凡是我们投进了对生命无代价或否定的东西,投进了冲突、毛病或匮乏的东西,这便是丑。”这一不雅观点就能够与上述状况契合。
法国 柯布西耶 朗喷鼻香教堂
第二种,建筑短缺意义而被大众根据其形式进行不恰当的遐想,授予一些建筑设计者或甲方未曾料到的“意义”,而且这种意义每每是负面的或不成立的。这便是大众对建筑物的误读。如果大众对建筑物造型的遐想是积极的,对其评价自然也是好的,如被称为“鸟巢”的中国国家运动场和被称为“小蛮腰”的广州塔等。反之,大众若对建筑物的意义产生悲观的遐想,则会将其评价为丑陋的。
瑞士 雅克·赫尔佐格等 中国国家运动场
中国 汪大绥 中国苏州东方之门
笔者认为这些建筑本身在设计上并没有太多的问题,其问题就在于过于象形而随意马虎导致大众作出误读和误判。辽宁沈阳的周遭大厦便是一个范例的例子。建筑设计师虽然利用了古泉币的造型,但想要表达的是天地合一的传统宇宙不雅观,同时也具有规范市场经济行为的寓意,然而其过于具象的形状很难不令大众遐想到建筑设计者对财富、金钱或成本的崇拜,从而招来各类差评。
与周遭大厦不同的是,中国公民银行总行大楼虽也是具有财富、成本象征的金元宝或聚宝盆的造型,但并未招来差评。其缘故原由在于此建筑遵照了齐白石所说的艺术“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原则,并未执着于形似,而是捉住了神似,从而使建筑的造型符合审美生理学的规律。对此,笔者要作进一步的引申:具象仿照建筑的形式背后的意义须要由建筑师或者甲方主动奉告并得到不雅观者普遍的审美及不雅观念认同,并非由鉴赏者自行判断得到。因此,在对上述类型建筑的整体审美过程中,鉴赏者每每觉得自己是被胁迫的,乃至是被愚弄的,以是很随意马虎就会对相应的建筑作品作出差评。
荷兰 雷姆·库哈斯 葡萄牙波尔图音乐厅
第三种,一些建筑设计师不顾建筑材质与人文环境,照搬西方的建筑风格而创造出丑陋建筑。这些建筑设计者所借鉴或照搬的西方建筑物每每是精品、佳构。借鉴工具本身并没有很大的问题,而关键的问题就在于照搬的西方建筑与中国的人文环境难以契合。近几十年来,海内各界“照搬”过来的最著名建筑物便是美国的白宫。据宣布,遍布中国各地的仿“白宫”建筑的数量已高达200余座。此外,“山寨版”西方小镇的地产项目也遍布全国各地。海内这些照搬西方建筑样式的建筑在社会上的评价并不好,个华夏因有二:一是西方外来样式无法与当地的人文环境领悟起来,二是施工工艺导致粗制滥造。个中紧张的问题便是用混凝土材料模拟石构造的细部而留下的“后遗症”。
荷兰 雷姆·库哈斯 中国中心电视台总部大楼
“丑”并不总是负面与悲观的,在我们理解和关注不到的层面上,其很多时候也是有积极意义的。纵不雅观历史,我们会创造人类对“丑”的理性认识经历了由恐怖、利用到鉴赏的漫上进程,个中折射出的是人类主体性的觉醒和认知能力的拓展。
进入当代,丑将美取而代之,成为艺术家创作的一大焦点,而很多后当代主义的艺术作品与建筑开始利用丑的形式表达创作者和设计者的思想、不雅观念。
法国 保罗·安德鲁 中国国家大剧院
艺术史的发展规律表明,“丑”的艺术的涌现是人类理性拓展的一定结果,艺术层面上的“丑陋建筑”亦是如此。笔者认为,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丑”是对“美”的补充,由于追求美好是人类的本性。因此,我们对“丑陋建筑”的认识不能只勾留在表面,而是要深入其内里,才能发掘更多有益于人类探索和创造美的成分。
本文节选自《中国艺术》2022年第6期
《理智与情绪——对当代“丑陋建筑”征象之研究》
《中国艺术》2022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