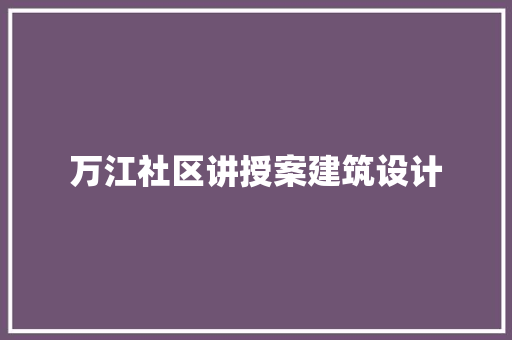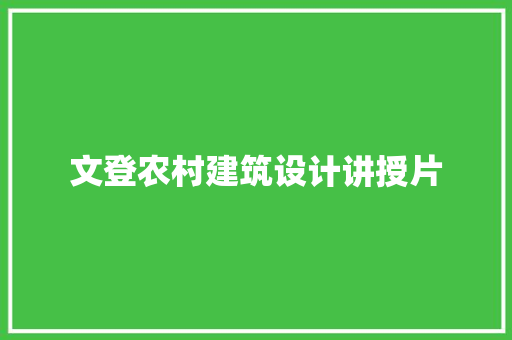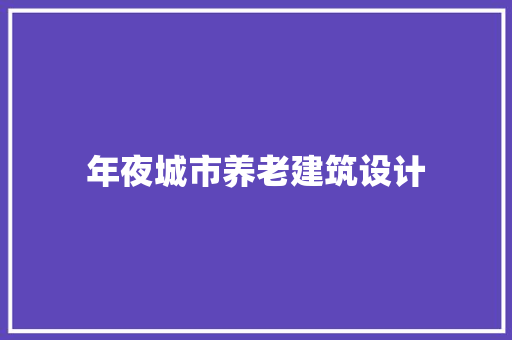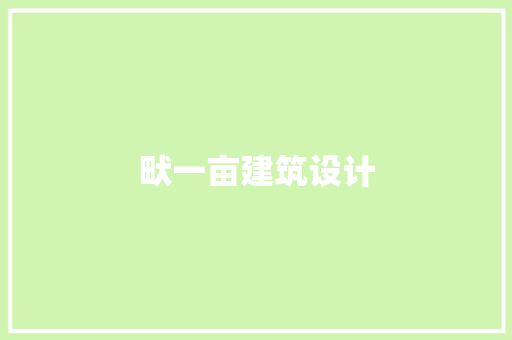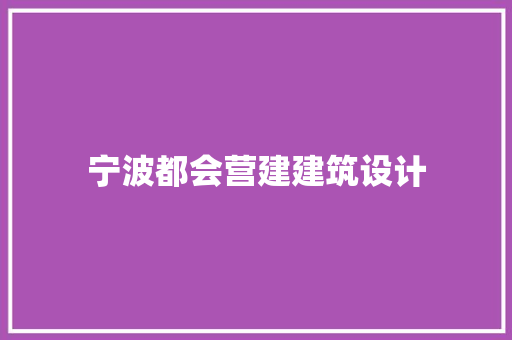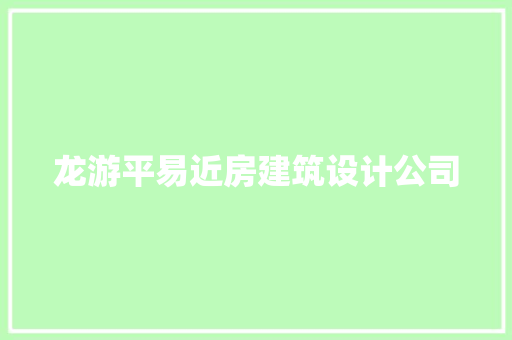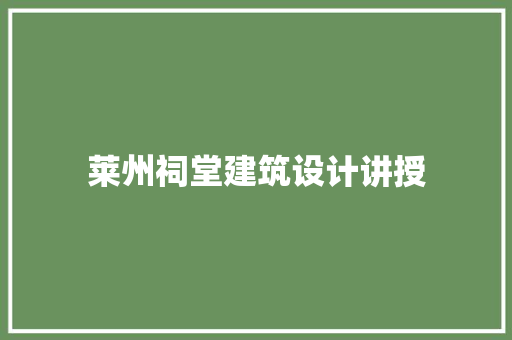大地褶皱里的班前村落。
石砌碉房与自然融为一体,并用丰富的信息为我们展现了千百年来藏民族的生存遗迹。

这些藏式碉房,墙体转角都砌筑得十分俊秀,一律线条笔直,棱角分明。
在班前村落旭日的山坡上,依山筑建的石砌碉房错落有致,与环抱的山水融为一体。
去班前村落时,正值夏末,这是草原在一年中最丰饶的时候。
班前村落地处我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玛县灯塔乡,间隔省城西宁700余公里。沿途穿越甘南草原,旖旎的景致令民气动神摇。如今,通畅的高速公路将如此迢遥的路程缩短为10个小时多点,这是一代人曾经无法想象的速率。记得20多年前,我第一次前往班玛县采访,乘一辆老式北京吉普,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一直颠簸,花费两天韶光才灰头土脸抵达班玛县城。中途宿玛多县,整夜头痛欲裂,无法入眠,却不知这是海拔反应。那次的目的地是玛柯河林场,置身个中,完备被原生态的自然风貌吸引住,并不知晓藏式碉房聚拢的村落就近在面前,终极和班前村落擦肩而过。
前往果洛班玛稽核藏式碉房,这个想法由来已久。作为藏民族古老独特的文化遗存,它与其地域的历史文化息息相关,密不可分。曾经是中国西南地区主要贸易通道“茶马古道”上的重镇班玛,藏语意为“莲花”,一百多年前也是商贾云集,贸易兴盛,因而遍布班玛各地的碉房便融入了多民族文化的建筑元素。这极具特色的民族建筑,也使班前村落声名远扬,2014年被住建部及国家文物局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落。如今,班前村落还是著名的赤色景点,当年红军长征途经青海时,曾经驻扎班前村落,村落前那片绿意葱茏的草地上,留下过朱德、李先念、贺龙、任弼时的足迹。走进班前村落,你便会和这条赤色路线不期而遇。
班玛县城和班前村落相距50余公里。汽车驶出县城,很快进入了玛柯河林场域内。玛柯河是大渡河主要的源流,玛柯河林场是长江源头海拔最高的天然原始森林,但见山峦苍翠,水流丰沛,散落在山谷间的藏式碉房陆续进入视野。听说班玛碉房最早可追溯到800年前,多数至少也有300年纪月。查阅有关资料,在《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就有“皆依山居止,累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为邛笼。”如此推算,涌如今青藏高原最早的碉房建筑大约在东汉期间。而考古创造的石砌建筑技能的年代更早,从西藏昌都的卡若遗址判断,大约在距今4000年的新石器时期就已产生。
作为天下建筑奇不雅观的藏式碉楼,在青藏高原分布十分广泛,但最密集的地区是川西一带,紧张以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内的丹巴县为核心。丹巴以“千碉之国”享誉天下,只管我还没有去过,仅从图片上不雅观赏,那直插云霄的气势就足以令人震荡。
碉楼最密集和类型最完好的丹巴,明清期间曾达到三千余座。想象站在高处远眺,那密密麻麻的高碉恍若一支昂扬的军队,那该是多么壮不雅观的场面。实在,藏式碉楼很早就被先容到了国外,比如美国植物学家约瑟夫·洛克,上世纪20年代在四川木里稽核后,写下《黄教喇嘛的地皮》一文,个中描述藏式碉楼的笔墨及图片就揭橥在1924年的《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上。
走近这些碉楼,其高度足以让你仰望,敬畏之情陡然而生。因此近些年里,有专家就按照碉楼的形态将其分为多少类型,从最常见的四角碉到十分罕见的十三角碉。据传历史上还曾涌现过十六角碉,但早已在岁月的烟尘中子虚乌有,险些没有人见过。现存的十三角碉也难得一见,可以想象它的壮不雅观和建造难度。
在青海的江源大地,我的目光所及实在有限,视野里难得涌现像丹巴那样的高碉,基本都是外不雅观古拙的四角石砌碉房。在班前村落一壁旭日的山坡上,依山筑建的石砌碉房错落有致,与环抱的山水融为一体。
班前村落以石砌碉房为主,也有少许的夯土碉房和石砌夯土稠浊的碉房。拥有300余年历史的碉房,经由如此漫长岁月风霜雨雪的磨砺,依然完全地保留下最初的样子容貌。近在面前的这栋,没有人能说得清这里究竟住过多少代人。碉房的构造为三层,紧张墙体为石砌,黄泥涂抹墙面。虽然多处和碎秸秆稠浊的泥巴都已脱落,袒露出粗砾的石片,但仍可以看出当初涂抹的泥巴相称厚,差不多达到8厘米,我想这样在冬季能起到御寒保温的浸染。三层空间布局有序,疏密自然。一层基本不开窗,可能是为了安全,光芒完备来自低矮且唯一的房门,紧张用来置放杂物和圈养畜生。那天我走进这座历史长远的老宅,站在空荡幽暗的底层,想象着数百年前,这个家族的先祖,在没有月光的夜晚,手持什么样的照冥器具,来照亮自己的脚步,是那种古老的酥油灯吗?
采光最佳的三层是家族设置佛堂的地方,这栋老宅由于年代太久,面积局促的佛堂已看不出当年庄严鲜艳的色彩,佛堂前面,还设有一个煨桑炉,可见数百年前,藏传佛教崇奉已在当地民气中至高无上。班前村落的老宅还有一个独特之处——在房屋外围用柳条编织的竹篱墙,又隔出约一米宽的走廊,这样,竹篱墙既能挡风,也可以利用空间放置畜生吃的草料。
很多年里,我对藏地这些百年耸立不倒的碉房充满好奇,仿佛是一个博识莫则、不得其解的谜。为了探寻这个颇有传奇色彩的石砌技能,班前村落的村落长尕玛求特地给我先容了省级藏式碉楼营造技艺传承人卓杰老人。如今快80岁的卓杰老人听说有人上门求教,满脸都是笑颜。他7岁时跟随长辈学艺,20多岁开始正式参与碉房建造。虽然我们的言语不通,互换要靠朋友翻译,但透过老人的讲述,一栋碉房建造过程的大致轮廓,逐渐在我面前清晰地呈现出来。
对藏民族而言,建造一栋生活起居的碉房是生命中的大事,因而神圣的仪式感在悠远的岁月中代代延续了下来。
首先,碉房选址尤为主要。藏地大多地处高寒地带,一年中的大半日子风大阴冷,早中晚的温差彷佛是循环了几个时令。同时,河流穿越的山谷多陡坡,很难有开阔平地,为了节约十分有限的耕地资源,碉房只有向上发展。另一个缘故原由是,青藏高原在远古曾是大海,如果屋子建在低洼处,室内就会湿润。以是建造碉房一样平常会选择背风旭日,或面路面水的高处,大门要朝向苍茫的群山或绿色的野外。位置选定后,房东人就会请当地寺院的喇嘛来卜算一个奠基吉日。破土动工的那天,他们要在宅基地前摆一个祭台,放上供品,煨桑,以感谢神的赐予,并祈祷日后人畜茂盛,吉祥安然。
卓杰老人先容,班前村落一带碉房的地基并不深,乃至没有达到一米。这让我不免迷惑:如此浅的地基,如何支撑起高大壮实的碉房?对此,卓杰老人的阐明是,玛柯河流域一带的山体,险些都是坚硬的石山,当时又没有前辈的挖掘工具,于是,祖辈们便想出一个聪明的办法:将岩石层表皮的泥土杂草打消干净后,在坚硬的石头上按房屋面历年夜小凿出80厘米深的沟槽。但宽度至少要达到一米,由于只有厚实的墙体,才能抵挡高原隆冬的寒冷。这样,弘大坚固的岩石山体,就成为碉房依托的天然地基。只管很多碉房都是依山而筑,但地基必须是在平整的地面上,地基的沟槽完成后,要用工具将其夯实,再用大块的长形石头铺筑,就算是完成了地基部分。接下来的石墙砌筑则是碉房的关键。这个传承了千年光阴的高超技艺,在赐予碉房朴拙持重形象的同时,也带给人们一种不可思议的神秘和惊异。
让我们来看这面石墙,这些大小、长短不一的石片,完备依赖天然形状。但必须经由严格挑选,质地坚硬,不易风化,无裂纹,无杂质。然而,要想把这些极不规则的石片从墙基起始,让它们垂直于地面,相互间严丝合缝地自然咬合,错落叠压,结结实实地融为一体,并非随意马虎。砌墙工匠以丰富的履历找到了一种找平和加木筋的方法。找平便是当石墙每砌到一定高度,工匠就会停下来,用一碗水或线锤来检测墙体的水平有没有偏差,这是担保墙体质量的关键环节。然后,要给石墙加上一层长条木板,我创造在一些短缺木材的地方,他们就用长条的厚石片来代替。但我不知道木头“筋”和石头“筋”有无差异。为了测试垒砌的石墙是否坚固,是否经得住高原风霜雨雪的严厉磨练,匠人们常常采纳分层构筑法。也便是碉房每盖好一层,就会被搁置起来,经由四季循环的细细不雅观察,确定没有任何施工毛病后再连续下一层的筑建。因此藏地的一栋碉房每每须要数年韶光才能落成。
砌筑过程中,石片之间要形成“品”字形构造,空隙必须用碎石填实,每砌完一层涂抹粘土夹杂草秸粘合石块,不能留一点空隙。这些技艺博识的工匠,在与石头的朝夕触摸中,逐渐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千姿百态的石头,只需看一眼,就能把它们各归其位。选择一壁比较光滑整洁的,叫面石,可以用来砌筑墙面。选择有一定长度,扁平的片石,可以用来砌筑里墙,叫里石。还有太多的不规则的小石子,可以用来填塞面石和里石的空隙,叫内石。最难的是它的收分、转角技能,完备凭借工匠丰富的履历和操作时的手感,层层叠叠,自下而上。没有图纸,更没有设计师,石墙筑至高处,乃至看不到脚手架,只见工匠站在内墙,反手砌之,游刃有余。他的手里仅仅晃动着填石缝的泥抹子和夯石的铁锤,但你分明觉得到图纸、尺子、墨线就深埋在贰心里。统统都管窥蠡测,不差毫厘。仿佛石头早已化为他身体的一部分,凭借一双慧眼和巧手,将其变成了令人惊叹的艺术品。
这些地处三江源地区的藏式碉房,从外不雅观来看,外墙呈梯形,很有美感。但对很多在城市的水泥森林里生活久了又不熟习藏式建筑的不雅观者来说,一定不明白为何砌成梯形。这是藏式碉房最具特色的收分技能。仔细不雅观察,创造厚实的墙体外层从墙根向上按一定比例逐步收敛,而内墙却始终保持垂直。
为了搞明白这个主要的收分技能,我查阅了有关藏式建筑的专业书本,给出的答案是:“首先可以较大程度减轻主体建筑部分的自重,自重减轻了,那么碉楼地基的荷载就可以减小,同时还可以节约部分建材的花费。第二,可以降落碉楼的重心,重心降落,自然就在一定程度长进步了建筑物自身的稳定性。第三,使外墙产生一个由下而上的斜向支撑力,而碉楼内部由于有各楼层的横向支撑,这样既对碉楼墙体自身起到一个支撑浸染,同时还可以避免墙体向外倾斜的可能。”
更为神奇的是,下重上轻的构造可以起到抗震的浸染。三江源地区属于地震多发地带,为了让自己家族千辛万苦盖起的房屋耸立不倒,聪慧的藏族先祖在生活中创造出了多种抗震方法。这些看似乱石片随意组合成的石墙,实在它们之间交错的缝隙,以及弥合缝隙的黄泥,就好比建筑师在抗震构造设计上,为了缓冲地震的拉伸浸染留出足够的伸缩缝,都均匀地消解和分散了相互挤压的力量,使坚硬的石墙有了弹性,同时,梯形的构造上轻下重以及内置的横梁,还有在石砌墙体内部安置墙筋等,均起到了天然减震的浸染。
这些藏式碉房,墙体转角都砌筑得十分俊秀,一律线条笔直,棱角分明。实在,石墙转角砌筑技能是全体碉房筑建难度最大的环节,必须由技能极其娴熟的工匠来承担此项重任。角墙砌筑的效果直接影响到碉房外不雅观和内部构造质量。以是石料要精挑细选,一样平常以整洁长形的石料为优。同时角的横切面必须成直角,收分系数必须同等,转角的角度要特殊精确,不能有任何偏差。
碉房的二层有窗,但老式碉房窗户很小,这和起先战事频仍,部落间常有摩擦有关。尺寸小的窗户防御性更强,同时也能抵御风寒。还有,藏族民间有这样一个说法,窗户小,光芒暗,会聚拢财富。一样平常在阳面和侧面各开小窗,多是外小里大。起先藏地用窗纸替代玻璃,怕风吹坏,窗格都很密实。一些大户人家,顶层还专门设置有瞭望孔和射击孔。门也如此,整栋碉房只有一个出入的大门,小且矮,个头高者进门需弓腰才会避免碰头。
为了保护家族不受侵害,人们的确谋划出诸多有效的办法,最精妙的要算是那个连接起各楼层的独木梯,由一根完全的圆木做成,一半砍平,另一半砍出能放下前脚掌的槽子,被安顿在每一层的通道口。灵巧轻巧,只要将它抽走,来犯者就无法登堂上楼。我这才创造,它竟然孤独无援,没有扶手。房东人微笑着鼓励我,我这才当心翼翼攀缘而上,等脚踏上平地,终于如释重负地松口气,觉得实在也没那么大的难度,而后对独木梯来了兴致,上蹿下跳练了好几次,竟也能高下自若了。还有一种较宽的板梯,多为大户人家所用。不雅观赏藏地碉房,最令我着迷的便是这独木梯了。它保留着树木本色,天然朴实,气定神闲,像一首温情的小诗,时时刻刻绽放在我对藏地的思念中。
碉房屋顶皆平,这种被《唐书》中记载的“屋皆平头”,也是藏式碉房的光鲜特色。高原少雨,被炽烈的阳光覆盖的平坦屋顶,成为主人用来晾晒粮食、衣物,安歇、瞭望的最佳场所。在西藏的拉萨、日喀则等地,可以看到碉房顶层四角还立有方形墩子,上面摆放着白色石子,插有五色经幡。它们在给外墙增加坚韧度的同时,也被房东人当作敬拜神灵的祭台。这是江源地区和卫藏碉房的不同之处。在藏地生活过的人都知道,藏民族崇拜白石,认为白石是神,他们把白石供奉在房屋的最高处,还把白石摆出宗教图案砌进石墙中,看上去新奇能干。
经堂是碉房的核心部分,是家族进行宗教活动的地方。大都建在顶层,以示主人对神灵的敬畏。在藏地,纵然经济再窘迫的家庭,经堂也支配得尤为华美。经堂正面全体墙壁,安装木制的佛龛,供奉佛像和佛经,下面摆放祭桌,上有净水碗等。两边墙壁上,挂有多幅唐卡。个别大户人家在经堂的天花板、门、窗、柱上都装饰富丽的彩绘,阁下还设有小寝室,专供寺院的活佛或僧侣安歇。
二层是家庭生活起居的紧张场所,因而选取的建材也讲求些,早期那些碉房的二楼,一样平常都设有一间面积最大的正房,兼顾客厅、厨房、餐厅、储藏室、待客安歇等多种功能。烧茶煮饭的牛粪火,恰好为室内带来温暖。寒风凛冽的冬夜,一家人围着熊熊燃烧的火炉,吃肉饮茶,谈天谈笑,那是一天费力后最温馨、最惬意的时候。
富有浓郁宗教色彩的内部装饰,是藏式碉房最独特的标志。在这间空间相对较大的居室里,梁与柱所霸占的位置非常贵显。因而对它们的装饰尤为看重。民居的房梁一样平常选择彩绘,常日是祥云图案。房间中柱的顶端常常绘以花瓣,下面束上吉祥物和哈达,以表达主人对代表先祖的柱子充满敬仰。
除此之外,草泥涂抹的墙面,选择吉祥八宝和宗教题材的壁画加以装饰,红、黄、白、黑的颜色,每一种都暗含着不同的宗教意蕴。它们细腻的构图和艳丽的光荣,与建筑外不雅观的朴实粗犷,形成光鲜比拟。
从远古卡若遗址显示出的碉房雏形,到光阴逐步雕刻出它朴拙的造型,石砌碉房始终贴近大地,与自然融为一体,并用丰富的信息为我们展现了千百年来藏民族的生存遗迹。三江源域内丰富的林木和石料为石砌碉房这一独特的建筑形式造就了天然条件,而地貌与景象又成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定的选择。藏民族对石的崇拜,对石的理解,以及对力学事理的心领神会,使得这种就地取材的建筑艺术拥有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和科学研究代价。可以说,碉房的石砌技能,是凝聚了藏民族聪慧结晶,浑然天成的艺术精品,更是天下建筑艺术宝库中的珍品。石材质地坚硬敦实,散射出阳刚力度之美,好似藏民族坚韧豪放的性情。同时,碉房的用材取自大地,终极又回归大地,没有任何污染,这种原生态,节能环保的精神品质,正是我们当下时期所要担当的任务。
此刻,我正站在班前村落一栋碉房的晒台上,一位80多岁失落聪的老奶奶仍旧留在这老屋里。她悄然无声,用温和的目光与我对视。我双手合十,对惊扰了老人家的安静表示歉意。从这里放眼望去,远处鳞次栉比的碉房在盛夏浓郁的阳光和青翠的山野里,浓缩成一幅别有情韵的油画。那些碉房外墙密集的石片,听凭光阴的嬗变流转,始终心无旁骛地守护着自己的本色。
记得有位建筑学者说过:无法与大地割裂开的,才是建筑。我相信,他一定也曾站在这晒台上,眺望过那群被山野簇拥的石砌碉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