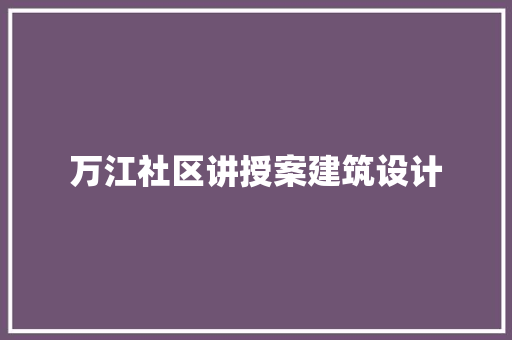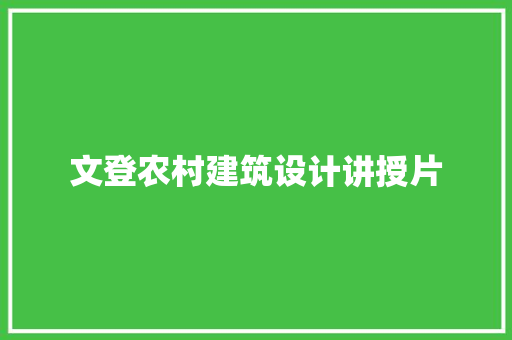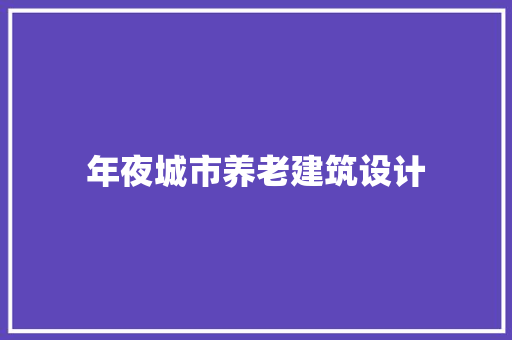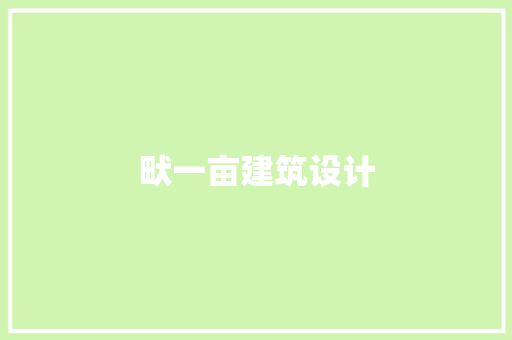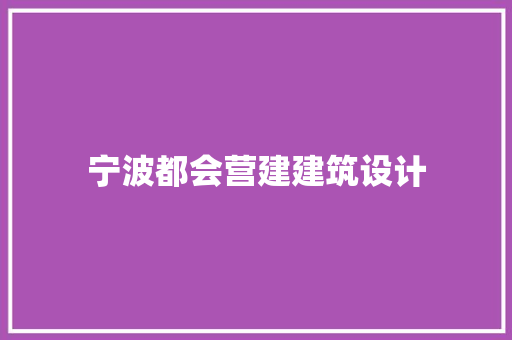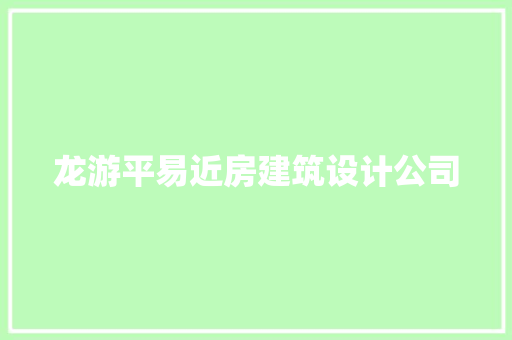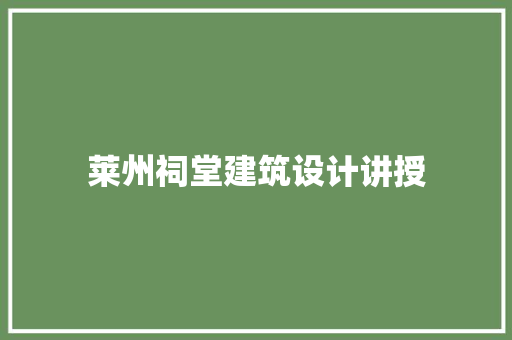往东行驶两三里,一个岬角在村落后突出于海湾之中,直面着海浪一浪一浪扑腾而来。海岬上长着一座大圳山,海拔三十余米,将一条六公里的海岸线从三面环抱包围起来。
碧海蓝天,遗世独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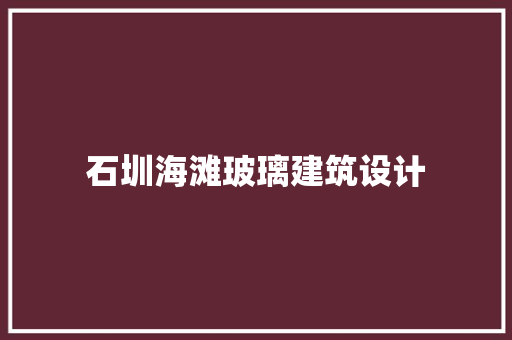
村落里人说,“这是我们自己的后花园”。在人烟稀少的海边,时常有村落民翻过一座小山丘,踏着湿漉漉的沙滩,择一处礁石,等一场潮涨。
山坡上,橘红的夕阳一点点落下。即将入秋的傍晚,海风肆虐,衬衫在风里层层叠叠。与我们一起来的石圳宣委陈文捷说,若没有村落民带路,很少人能知道这里。
“这个地方不能来,来了你就不想走。”
逆风向海
金井的海边,以围头最为著名,临近几个村落各有特色。塘东有沙洲,福全有古城墙,在以前,很少人知道,还可以去往金井石圳,赴一场海角天涯的浪漫。
海快到村落外。途经被风撑起的绿荫和花,举头看到风车在哪,石圳的海就在哪。长长的海岸线上,一到夏天,村落民聚拢在西边的石圳海滩上。
而东边的大圳山,游客稀少,每年却赶来许许多多地理爱好者。只因经由漫长的地质运动,在这里堆叠着奇特的海岸变质岩,它们来自著名的平潭—南澳变质带,是全国少有的奇不雅观。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这片无人的海疆展现得淋漓尽致。山脉与石头将这里隔绝起来,车行过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方才开到大圳山脚下。
迎着海风刮来的小型沙尘暴惊扰了入海的脚步。可是这儿的沙,细得犹如敦煌月牙湾上的。捧一把在手里,它只管细细碎碎从指缝溜走。
讨海的人一来到海边,哪儿有螺,海蛤、虾蟹,指得明明白白。村落庄里的渔民,总在天未亮就驾着渔船出发,他们算着潮涨潮落的韶光,退潮的时候三三两两带着工具,挖海鲜来。
地理爱好者在变质岩上感叹,以海为生的村落民在岩洞里追着海螺。
还未终年夜的螃蟹在入水的沙滩上留下圆形苗条的洞穴,大的小的,一个一个。洞穴边上螺旋出一粒粒裹成圆圈的沙粒,洞穴越大,螃蟹越大。
白色的海蛤在呼吸,将沙滩上渗出了两个两个相邻的小口子。手指往沙子里一挖,全体下午能有一脸盆的海蛤,捧回家煮一把汤,汤头鲜甜鲜甜,生出了野味。
落日逐渐掉到了风车的风页上,天边一片橘红。附近秋日的海边风大,海浪张大了嘴,一浪赶着一浪。陈文捷领我们走进一条车开不进的小路,山脉将这里遮挡,成了避风处。
她指着大圳山的另一壁,怪石嶙峋,问我们,“你看这个像什么”。每个人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她往前带头,走到一处海崖上。这里的石头千奇百状。
有的像出海的乌龟,有的像鲸鱼扑浪,还有山上的如巨蟒探头。它们站立在偏僻的山海间,等人来猜。陈文捷说,如果不是好几个伴,一人切切不敢独自前来。正是藏在了丛林深处,这一起才显得宝藏了起来。
大山大海。想起有位朋友说,她曾站在黑夜的海上,以为生活里的不快意就像这脚下的浪,一脚一脚踩下去,有一天,它总会消逝。
人到了海边,彷佛生活总能被治愈。
秘密花园
每年夏季,石圳迎来休渔期。渔民们或干脆休整,或往城镇谋生。村落民会在禁渔前买上一整筐品种不一的鱼,冻在冰箱里,吃上一整季。
我们往86年历史的古屋子拾级而上,穿着白背心的老人正在砧板上处理一条竹荚鱼。87岁的李冠群往我们凑了过来,看清了来人。
这是一座建于民国二十一年的两层番仔楼,前后各一栋,名为“种橘山庄”。李冠群在这里出生,终年夜,一贯住到了如今,岁数与古屋不相上下。
石圳村落是远近著名的侨村落,村落里人口三千多,在外的就有一万多人,分散在菲律宾、印尼、新加坡各地。1933年,李冠群在菲律宾打理家族买卖的伯父将钱寄来,兴建了这样两座一样的番仔楼。
中西合璧,除了就地取材的石头,其他材料千里迢迢从外洋运来,到了石圳港,再由工人一车一车往村落里运。终极在那个时期,人们说泉州南门外,再没有比种橘山庄更精美华贵的建筑了。
这个美好的名字,牵扯出这个村落庄曾有的果林。曾经这里种满橘子树,树上一摞一摞垂着果子,李冠群说,在以前的老宅门口也有棵橘子树,种橘山庄便取了这么个浪漫的名字,也寓意着如喷鼻香甜的果实,家族多子多孙,吉祥快意。
他和老伴住在后落的二楼,极富年代感的木楼梯二楼出入口关着一扇小门,保护着两位老人。如今几百人的大家族,子子孙孙有的住到了镇上,有的则依然在南洋。
夫妇俩宁静地生活于此,柴米油盐,说谈笑笑。老人洗净了手上的鱼腥,随我们在屋子里绕了绕。天花板上久远的雕花灯座依稀可见,他指给我们看屋顶外立面,一根颓落的钢筋。透过天井,楼下前座的种橘山庄有师傅正修缮着后门。
建筑在韶光里风化,人声总在这里流淌。前落的正厅,闲聊家常的邻居散了又来。葡萄架攀附在屋顶,地瓜藤在地里成长。
门前的古榕伸着古老的垂枝,年年纪岁。
历史里,石圳村落还出身过与陈嘉庚齐名的著名爱国侨领李清泉。在那个相继下南洋的期间,村落人陆陆续续发财后,纷纭往村落里寄钱,相继建了一落落富贵的洋楼。
1932年的“陇西衍派”如今已不再住人,铁门内一片复古的泰西风情。来人拾级而上,看着庭前依然成长着的花花绿绿,凌乱地在风中扭捏,抱负此前这里将是如何美的一座花园。
光秃秃的铁树是从何时不再着花。脚下镌着图案的鹅卵石多久不再有人走过。村落里人说,“石圳有多少座桥,就有多少侨的故事”。
百年来,侨胞归来,侨胞远走。这座滨海小城白浪依旧拍打着海岸,年复一年,在安静的村落落里发生发火声响。或许不用几个夏天,游人会相约往大风车的方向走来。属于石圳的后花园正在逐步打开。
那时,这座村落庄,终将不再只有离开的痕迹了。
END
文/六月 图/吕波
走,到金黄的秋日撒个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