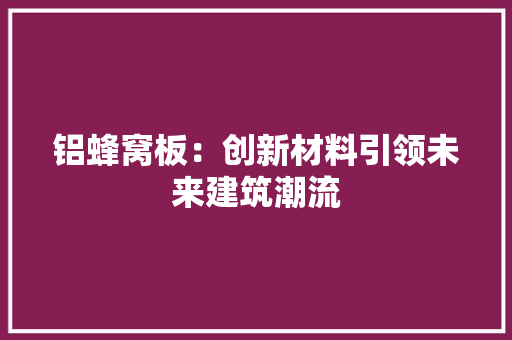本文已得到授权
作者:陈思岐 巴斯大学 建筑系 Year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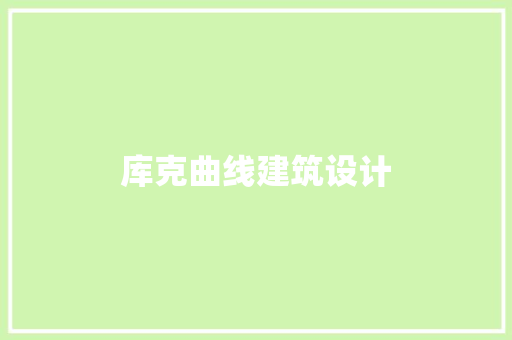
James 烟台大学 建筑系 Year 4
Part 1
Peter cook 与 Archigram
1
弁言
会移动的城市,单元规格化的住宅,能随着个人需求变换的楼房,可以相互连接相互组合的建筑,这些想法或许已经不再新颖,如今我们也可以在各种建筑竞赛中看到相似的观点,但这仍是现今的人们须要推敲的难题,也有可能成为城市的未来方向。然而,早在50年前,一群刚从AA毕业的年轻人就提出了问题,并给出了他们的答案,这便是 Peter Cook与以他为核心的Archigram(建筑电讯派小组)。
笔者今年有幸在他的事情室事情过一段韶光,通过在Crab Studio的事情实践结合与老爷子相处的日子,加深了我对彼得库克的作品与思想更立体的思考。于是我撰文,写下了这一篇《Peter cook 与 Archigram》。本文将分成两个部分,首先简单地先容早期建筑电讯小组的构想与中期格拉茨美术馆的设计,其次先容后期Crab Studio的一些作品,希望本文能让同学们有所启示,更理解这位建筑大师与他的故事。
阿基格拉姆学派 (Archigram亦译“建筑电讯小组”或“阿基格拉姆集团”)1960年以彼得·库克(Peter Cook)为核心,由伦敦两大建筑专业学生集团为主体成立的建筑小组,他们把利用建筑的人算作是“软件”、把建筑设备算作是“硬件”,是建筑的紧张部分。“硬件”可依据“软件”的意图充分为之做事。至于建筑本身,他们强调终极将被建筑设备所代替,因此被算作是“非建筑”(Non-Architecture)或“建筑之外”(Beyond Architecture)。Archigram反对传统、反对专制、反对任何形式的束缚,提倡自由,对技能抱着乐不雅观的态度。评论界有说他和“建筑范例”小组的对天下建筑界的影响可以等同于披头士乐队对摇滚乐的影响。
2Peter Cook的生平
Archigram早期的核心成员们
彼得.库克(Sir Peter Cook),1936年出生在英国南部的海边小镇(Southend-on-Sea)。在1958从Bournemouth艺术大学毕业后,他来到了AA 进建筑筑学。1961年彼得库克在AA领导成立了建筑电讯派小组(Archigram)一举成名,著名作品包括Plugin City(插入城市),Instant City(立即性城市),Walking City(行走城市)。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代主义大师已入晚年,人们处在当代主义潮流之后的迷茫。而这群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对城市的重新解读急速在建筑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向结束不前的理论输入大量新鲜的血液。在Archigram中,建筑从当代主义的方盒子中跳跃出来,成为了流动有生命的有机体,其对空间的理解直接影响了如扎哈.哈迪德+雷姆.庫哈斯+理查德.罗杰斯等一整代的建筑师,巴黎蓬皮杜中央的设计(因在原方案可移动的楼板)也被公认为是对Archigram的一次致敬。彼得库克在2000年设计的格拉茨美术馆(Kunsthaus Graz)更是二十一世纪初旗帜性建筑(2003年Stirling Prize提名),因其大胆独特的造型被当地人称为“友善的外星人”。
1990年从AA离开,库克来到了UCL的巴特莱学院(Bartlett)长期就任院长,并在2007年因其对建筑和教诲的贡献被英国女王封爵。同年,他和建筑师Gavin Robotham在伦敦成立了Crab Studio,年近80的他仍旧奋斗在建筑设计实践的第一线,并在近年主持设计了邦德大学Abedian建筑学院和维也纳金融学院等有名作品。Archigram以其叛逆而天马行空的乌托邦思维精神,对英国传授教化更是影响深刻,巴特莱特的建筑传授教化,便是这种思潮的延续。
3
Archigram的奇思妙想与发展
彼得.库克出生在海边的小镇,在他16岁的时候又去了一个海边的城市上大学,他说近海的生活对他的影响很大。首先,一个靠海的城市常日旅游业非常发达,也导致城镇人口的变革随着时令而发生改变-常日在夏天游客量更加而在冬天荒无人烟。这让儿时的他以为十分有趣,也开始留神起城市的可变革性于人口的流动性。
小镇海边 Southend on Sea(图左)
海边小镇Bournemouth(图右)
上图的两个建筑装置分别在彼得出生的小镇和他读大学的城市,对少年的他影响很深。游客们费钱进入一个小房间里,然后巨型的机器装置将房间升至山上或制高点,就像缆车一样帮助人们升降。彼得说,这是十分有趣的,由于他们的形态与功能和周围的楼房截然不同,已经从传统意义上的建筑分开转而成为了一种机器装置。这也令他从小就在思考,建筑的未来是否可以和机器与运动存在联系。
一转眼来到了二十世纪60年代,经由二战后创伤的二十年修复,天下在飞速发展着,科技也走进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拐点。一韶光,登月,太空飞船,打算机,摩天算夜楼,学生涯动,摇滚,朋克艺术充斥在耳边。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年代,所有人都在展望未来等待着技能爆炸,彷佛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更没有什么是人们不敢想的。
建筑电讯小组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涌现,他是一个具有强烈未来主义风格并反对威信的象征。在他们的构想中,建筑是可流动可变换的存在,从根本上否定了资产阶级资产固定的代价不雅观。并推崇科技,企图用最尖真个技能逃脱限定,来办理城市与建筑之间的问题,打造了一个一个抱负中的乌托邦。通过杂志《建筑电讯》,他们把想法公之于众,并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脚印。
Plugin City(插入城市),彼得库克,1964
Plugin City无疑是建筑电讯小组最为出名的作品。首先彼得对几千年以来建筑的固定性提出了质疑,在他的构想中,传统意义上的建筑消逝了,城市变成了森林,而树干树枝便是拔地而起成45度的巨型钢架构造,所有的居住、办公、商业空间等单元化成为了树叶,而他们都具备可移动性,能够在巨型构造之内插入(Plug in)或拔出(Plug out),像是一个超大型的乐高积木。所有的部件都在工厂统一加工,建筑标准化,也将大大降落生产的本钱。
Plugin City的蓝图是对人们所理解的建筑从根本上的推翻。建筑可以由于人的需求所移动,当一个人须要到外地办公,我们可以把自己的屋子直接拖走,当商铺在某地无法连续经营,我们可以轻松地另谋他出,当一个区域遭到自然磨难的侵袭,我们可以寻觅一个更安全的归宿。从此,远方也可以是家。
在彼得的设计中,城市与国家的观点都被弱化了,贫富之间的阶级也因此肃清,天下走向大同。而城市再也不须要被精心方案了,由于统统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改变,应人们的需求而改变。城市活了起来,可以自我调节建筑的密度,可以随时改变社区的成份构造。所谓,不治而治,统统都会为了知足人的需求而做事,而所有的改变都是发生在不经意之间。城市,将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
提到建筑电讯小组,就不得不提日本的新陈代谢派(Metabolism)。不足为奇,1960年旁边在地球的另一端,以黑川纪章为首的一批建筑师提出了相似的不雅观念。新陈代谢流派强调事物的成长与变革,认为建筑不应该是静止的,而应像新陈代谢一样是一个不断变革的动态过程。
中银舱体大楼(Nakagin Capsule Tower),黑川纪章,1972
在黑川纪章的设计中,居住单元成为了一各个统一标准的小方盒子(2.3m x 3.8m x 2.1m),像堆积的积木一样插在了建筑的核心上(Core),而核心部分包括电梯楼梯和机器设备知足建筑的做事需求。所有的部件都在工厂预制现场直接安装,所有的尺度参数也都是成规格的。 由于低廉的造价和大幅减小的居住面积,胶囊宾馆的观点在战后的日今年夜面积盛行。因其统一规格的单元随意插入建筑主干的特性,建筑电讯小组作为背后的助推手功不可没。
Instant city(立即性城市),彼得库克,1968
Instant city是彼得其余一个比较出名的作品。城市建立在平台吊颈挂着巨型的热气球,同时气球可以作为投影装置成为信息互换平台。城市就像是一艘航空母舰一架太空飞船,永久向着梦提高。
Walking city(行走城市),罗恩赫隆(Ron Harron),1964
建筑电讯的浩瀚作品中,其余一个让人津津乐道的就要数罗恩赫隆的Walking City了。和Instant City相似,Walking City也是可以移动的。人类生活在巨大的金属仿生态形体中(昆虫),城市可通过在形体下部的“腿”移动行走。若建立在人口密集的区域,建筑和建筑之间可以通过管道状的步辇儿带链接,组装成为一个超级城市。在Walking City中,人们摆脱了交通工具,个人所须要的统统都可以在巨型建筑体中自我知足,而于此同时建筑本身也成为了一个移动的交通工具,可随时转移到资源或制造力须要的地方。
Walking City与宫崎骏《哈尔的移动城堡》做比拟
数学中的费马大定律,这个定律实在没有什么实际用途,但却引发欧洲数学家将近300多年的思考,过程中也触发了很多其他领域的发展。在当时Archigram探索的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建筑抱负。在作品“行走城市”(Walking City)中,他们试图展望未来,将那个时期的新技能和材料发挥到极致后的建筑会具备哪些可能性。虽然他们的设想不可能真正实现,但思维始终没有分开严谨的逻辑和理性。
粗野主义:Pirelli大楼 马赛尔·布鲁尔(左图)
高技派:伦敦市政厅 诺曼·福斯特(右图)
人们很快创造这些想法内在实在很科学,而且有很多值得考试测验的地方。也正是捉住了这些地方,一代实践家如罗杰斯和福斯特才逐渐摸索出一套全新的建筑语系,即“高技派”(High-Tech),成为一代宗师。高技派建筑彻底颠覆了之前盛行的“野兽派”,将原来笨重粗糙的混凝土墙换成了轻盈透明的玻璃幕墙,并且诚恳自傲的将建筑真实布局展现给公众,彻底撇开贴面材料的遮挡。建筑的骨骼露出来了,墙体加倍透明,空间的通透感空前大增,并且焕然清新。大量的标准部件可以在工厂生产完成后直接进场安装,本钱得以节省,工期得以加速。而这个中,从袒露构建之美,到工厂部件加工,统统都是Archigram多年前就提出过的观点。
Archigram在20世纪70年代旁边终结,这也顺应了逐步平复下来的时期。虽然,他们没有将纸上的蓝图化为实际,也注定无法在百年内实现,但毫无疑问他们是成功的。建筑电讯的假想乃至有点玩世不恭,但他们的理念放在如今也是前卫令人寻思的。数十年来有无数的设计师被其影响,也有很多团体仍在研究城市的出路。比如由CJ Lim领导的巴特莱学院Unit10,这个单元象征着巴特莱乃至环球最前辈的教诲理念。每年,都有十几名成绩最精良的学生进入这个单元,提出城市涌现的问题并给出自己的办理方案,勾勒出一个一个抱负中的乌托邦天下。
Bartlett Unit10 学生作品
建筑电讯的理念,让人遐想到了20世纪中期柯布西耶做出的一系列城市方案。在某些层面上,二者拥有十分相似的英雄主义精神。他们都具有以上帝的姿态来改变城市从而拯救人类的精神。无论这样的构想是否能实现,也无论他们是否能成为未来城市发展的方向,但他们的理念代表着一种空想化的终极。而这种乌托邦式的架构,从某种层面也代表着人类的归宿。无论建筑电讯小组究竟有多大的现实意义,我始终相信,思考未来,才有更美好的现在。
4友善的外星人:格拉茨美术馆
格拉茨美术馆,彼得库克与科林福尼尔,2003
随着格拉茨美术馆于2003年培植完成,沉寂了几十年建筑电讯再一起走进了人们的视野,一韶光人们纷纭惊呼“Archigram is Back”。而这一次,不再局限于纸上谈兵,彼得库克把他的梦幻带进了现实。美术馆坐落在一群1842年的老建筑之上,流畅的曲线和怪异的造型与古典建筑造成了强烈的反差,成为了奥地利小镇格拉茨最亮丽的风景线。
全体建筑有由四个紧张部分组成。核心区域是类似于心脏形状的容器,他被称作建筑的“胃”(Belly),承载了大部分的展览空间。最顶部类似于心脏血管的触角被称作建筑的“管口”(Nozzles),可以将自然光柔和地引入顶层展厅。位于“胃”的下部分与地面打仗,为全体形体供应支撑的部分被称为“栓角”(Pin)。与此同时,建筑的最上方还有一个悬挑的柱状物体,作为一个酒吧和不雅观景台,被称为“针管”(Needdle)。
艺术馆的首层是由方正的玻璃幕墙围和出的空间(“栓角”),包括接待大厅多功能厅展示厅等等,为游客供应了常规的建筑空间。而在主入口处设有移动式斜坡道可以将人逐步地吸入建筑的“胃”中,这种动态是一种从常规空间进入混沌的反差,营造出独特的不雅观展体验。进入展厅部分,室内没有多余的装饰,参不雅观者如置身于巨大的蓝色泡泡中,感想熏染空间的韵律与纯粹。柔和的光芒从“管口”打入,也使室内的光影效果随着太阳的运动而不断变革。末了,游客来到最顶部的“针管”,在全透明的不雅观景台上,与“胃”部靠近全都封闭的空间产生巨大的发差,视野变的豁然开朗,这种戏剧性地安排使得参不雅观者的游览更佳的具有意见意义性。不难创造,彼得所营造的空间和建筑电讯有许多相似的理念。他们都在追求一种夸年夜并戏剧的建筑表达手腕,追求发差,长于玩弄空间的流动性与不愿定性。
格拉茨美术馆的外表皮由半透明有机玻璃构成,表层之下安装了BIX发光装置可以让全体建筑的外表皮成为一个低像素的显示屏。这不禁让人想起Instant City中的信息互换展示观点(Communicative Display),让建筑本身成为一个信息互换的平台,也是建筑电讯小组追求高科技影响城市生活所致力的目标。夜幕降临时,建筑“超表皮”在中心电脑程序地掌握下改变图像的序列,使建筑充满更多的可能性从而达到建筑电讯对变革的追求。
Part 2
Crab Studio的征途
1
为了梦想的坚持
2007年,当彼得.库克在71岁高龄的时候他没有选择退休而是与建筑师盖温.罗伯特姆(Gavin Robotham)在伦敦成立了Crab Studio。彼得的设计从此走向了更实用化的路线,但仍旧追求流畅的空间和大胆的构思。几年来建成了不少佳作,也在很多国际设计竞赛中博得头筹。个中,落成不久的邦德大学Abedian建筑学院是笔者最喜好的作品之一。
邦德大学Abedian建筑学院,2013
坐落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邦德大学地处酷热的区域,以是Crab Studio最先开始考虑的是屋顶大面积地挑出从而最大程度地减少阳光地摄入。建筑在东西北三个朝向上开窗更为谨慎,并用精心设计的遮阳盖来挡住大部分直射的阳光。在阳光不会直射的南面(澳大利亚地处南半球),建筑更佳轻盈,大面积的开窗担保采光,而室外的垂直立柱和悬挑出的屋顶也将避免夏季阳关间接照射的可能性。
全体建筑最出彩的地方在于室内中轴线上的长廊。Crab Studio相信,一个好的大学设计该当是开放的,鼓励学生相互互换的,应有更多的社交空间(Social Space)。因此,他们用一条中轴线把建筑的旁边两侧相连,而在中间的公共空间里,一系列的走廊楼梯平台与桥相互连接,制造出极其丰富地空间层次,而混凝土的墙是扭曲的,让人感想熏染到流的空间带来的震荡。每逢Crit(单元结束时导师的评测),学生们都会走出教室把作品贴在中轴线的混凝土墙上,公共空间同时也是教室的一种延伸,鼓励学术互换展示学术成果的存在。
末了分享一些Crab Studio近年来的其他作品:
维也纳金融学院,2013
Bournemouth艺术大学画室,Crab Studio,预期2015年11月落成
澳大利亚.黄金海滩文化中央
台湾.能量塔(a Tower of Living Energy)
2夜晚的灯光
彼得库克已经是
韶光会摧毁一个建筑师的肉体,但永久不会击垮他的灵魂。一个年入古稀的老人对建筑的忠实,是他一辈子的坚持。我相信,物质不再主要了,金钱不再主要了,而对空想与信念的追求才是唯一。这种信念不老,这份坚持不朽,这种精神会一代一代的传承。高迪去世前衣着寒酸却仍在构思圣家族大教堂的辉煌,赖特尚未来得及走进他的古根汉姆博物馆就撒手人间,太多太多的建筑师在趴在图纸上与世长辞。与其说,建筑是一个事情到去世的职业,不如说,建筑是一个追梦到末了一刻的光荣。
彼得库克未完成的手稿,2015
勿忘初心,这种对空想的追求,
不正应是每一个建筑师都守卫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