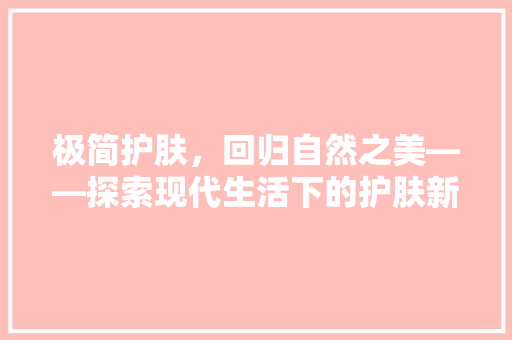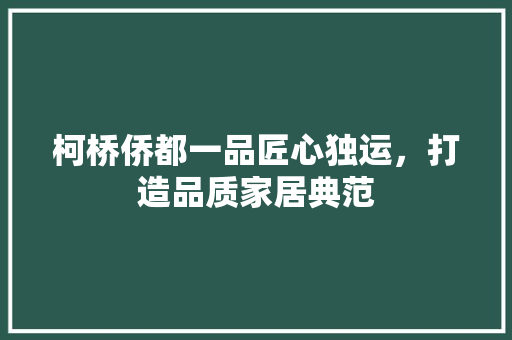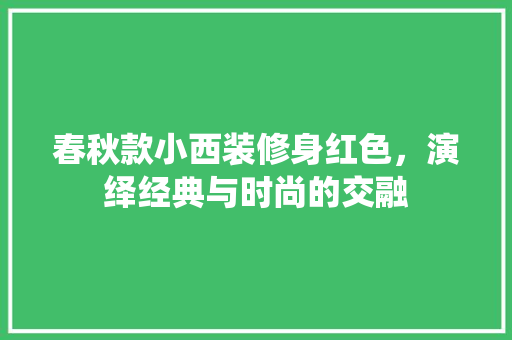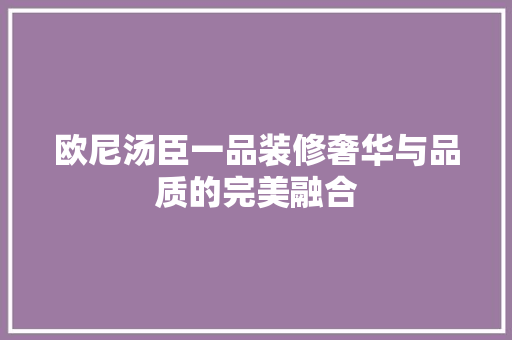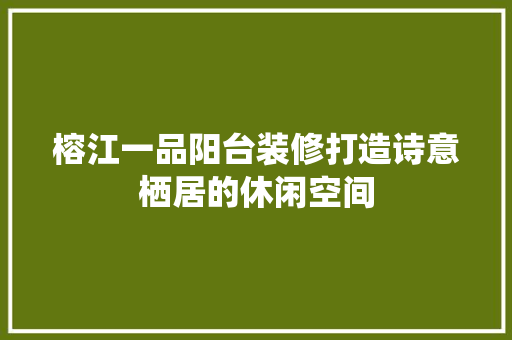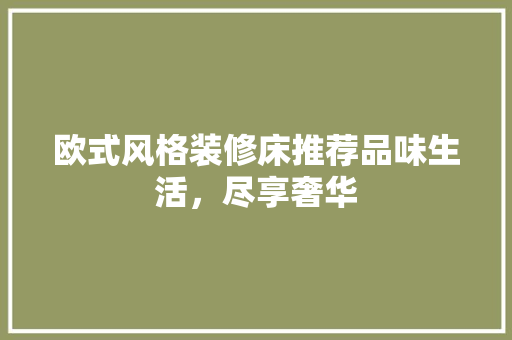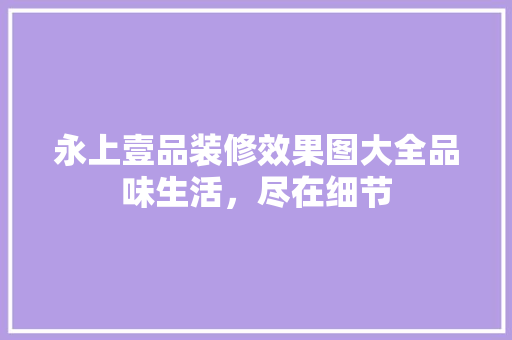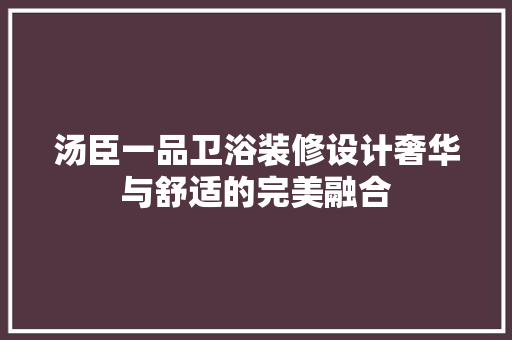李青松供图
之前,我从未见过上万只鹰聚群的壮不雅观场面。

那座山谷里的鹰多为苍鹰,黑褐色,白羽尖,胸部密布灰褐与黑白相间横纹。翱翔时,双翅宽阔,翼展发达。细不雅观之,翅下灰白色,并间杂黑褐色横带。好威武的鹰啊!
那座山谷,在大西北天山脚下。起先,这座山谷没有名字,当地人提及它时就叫“那块地”。我去后认为欠妥,这么有故事的山谷怎么可以没有名字呢?该当有个名字呀,便曰之:老鹰谷。
当地村落民都很赞许这个名字。于是,“老鹰谷”取代了“那块地”,就被叫开了。
老鹰谷走向自西向东,两边是起伏的峭壁绝壁,裸岩狰狞。山谷是陡然沉下来的,沉到最底处,便是一条河了,蜿蜒弯曲,河水悄悄地流着,滋润津润着两岸的万物。胡杨,一副忍辱负重样子,倔强地成长着。数不清的鹰栖在树枝上,远看犹如树上挂满了黑褐色布条。红柳,虽然个体纤细柔弱,但组成群落却密密实实,以绝对多的数量,霸占着山谷里最惹眼的位置。它们在河水反衬下,泛着幽幽的暗赤色的光。红柳丛中,跳跃着生命。野兔、野鸡、沙斑鸡、田鼠、刺猬、旱獭、草蛇出没其间。鹰,在高处盘旋,时而静止不动,时而滑翔翻转,一圈,一圈,又一圈,探求抓捕机遇。
老鹰谷的鹰可不好惹。性情暴烈,彪悍。
鹰的嘴和爪子如铁一样平常,强劲有力,抓取猎物时,犹如疾风扫落叶般凶猛。鹰的身躯矫健而厚实,肌肉紧实,羽毛坚硬。它的姿态是轩昂而英挺的。在浩茫的天宇间,动作疾骤,快如闪电。在所有鸟类中,鹰是飞得最高的。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照亮老鹰谷的时候,也照亮了这片斧削般的绝壁。黑褐色的羽毛微微动了动,鹰便睁开了眼睛。
“丢——溜——溜——!”
“丢——溜——溜——!”
长长的唳啸,唤醒了沉睡的山谷——新的一天开始了。
鹰巢筑在峭壁绝壁上,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牧羊人陈老爹知道,村落民也知道。但是,没有人把这当回事。
鹰巢像是一个平底筐,用横七竖八的枯枝树条,就那么毫无规则毫无逻辑搭建而成。——不是凹下去的,而是凌乱无章胡乱堆起来的。“平底筐”每每建在两块岩石之间(那里干燥安静,少有滋扰),简陋,粗鄙。看起来彷佛并无多少道理,也没有什么美感。但是,错了,如果我们都那么认为,解释我们是多么的屈曲。实在,“平底筐”正好透着鹰的大聪慧:稳固、牢固、避风、避险、耐用。
从生存学的角度来看,大概,“平底筐”的实用代价远大于美学代价。不过,“平底筐”的缝隙里也间或夹杂着一些羽毛,是为了装饰?还是为了舒畅?大概只有鹰自己知道吧。
老鹰谷的鹰,虽说不是作歹多真个坏东西,但有时它们也会惹是生非,令人讨厌。
这天,陈老爹赶巴扎回来,手里拿着一个锅盖大的馕,边走边吃,不觉间就进了老鹰谷。一不留神,陈老爹手里的馕却丢了。他转头探求,路上没有,阁下灌木丛没有。馕哪里去了呢?难道长了翅膀吗?对了,馕真的长了翅膀。陈老爹举头向上看,原来,空中一只老鹰叼着他的馕,正忽闪忽闪抖动翅膀嘲笑他呢。陈老爹很是生气,捡起一块石头抛向空中,老鹰一惊,嘴巴一松,馕从空中滴溜溜落下来。陈老爹奋力去接,可没接住,馕落在了一个沙坑里。腾地一下,沙坑里蹿出一个黄色的影子,慌慌然逃进红柳丛中。是野兔吧?也可能不是。
陈老爹拾起馕,用嘴吹吹了沙,接着,狠狠咬了一口,往下咽,却噎住了,噎得直翻白眼。他挺了挺脖子,骂了一句:“狗日的老鹰!”
“丢——溜——溜——!”空中的鹰,排出几粒屎,陈老爹躲闪不及,屎落在脖颈上。臭!
鹰是在故意羞辱陈老爹。这还没完呢。
越日,陈老爹家鸡窝里的鸡蛋被什么贼偷吃了,光剩下空蛋壳壳。越日的越日,正不才蛋的芦花老母鸡又不见了。陈老爹忍着,没言语,照样在老鹰谷牧羊。可是,于崖壁的底端,陈老爹却创造了一堆芦花鸡的羽毛。一片散乱。
陈老爹怒火满腔了。陈老爹打算给老鹰点颜色看看。某日,在老鹰谷里牧羊的陈老爹一眼瞥见了崖壁上的老鹰巢,便举起牧羊的杆子要把它毁了,却听到“溜溜溜!”一声唤。细不雅观之,崖壁上趴着一只老鹰,挣扎着动了几下,就又安静了。
原来,那只鹰的翅膀断了。
鹰的眼神里没了戾气,却满是恐怖、无奈和哀伤。
陈老爹心软了。
陈老爹爬上崖壁,把衣服脱下来罩住了受伤鹰的头,抱回家。找出接骨木叶子,捣成糊糊,涂在鹰翅伤口处,再用绷带小心翼翼地缠上。多日之后,在陈老爹细心照料下,老鹰翅膀上的伤口,逐渐愈合了。然而,在陈老爹看来,那只鹰还相称虚弱,元气和体力规复尚需时日。陈老爹三天两日,从镇上屠宰场弄回一只鸡架子喂鹰。后来,鸡架子涨价了,陈老爹的开销有些急急,就去田里下夹子夹老鼠给老鹰吃。伤筋动骨一百天,老鹰的伤终于养好,元气和体力也规复了,翅膀一抖动呼呼生风。陈老爹知道,老鹰又可以把云和风踩在脚下,重返蓝天了。
选了个晴朗的日子,陈老爹便把它放飞了。陈老爹徜徉于老鹰谷,心里空落落的,痛惜若失落。
——这是多年以前的事情了。
由于鹰,老鹰谷里的草木,从没有遭受过鼠害虫害。老鹰谷麦田里的麦穗粒粒饱满,年年丰收。
头一场春雨过后,老鹰谷沉浸在超乎想象的宁静里。头顶晴空水洗过一样平常,瓦蓝瓦蓝。那些胡杨,那些红柳,又长出新叶,欣欣向荣。风仿佛是甜的,微微拂动着树梢。
然而,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嘭!陈老爹在追赶一只走散的羊羔羔时不慎坠崖。从此,老鹰谷里不见了陈老爹的身影。
老鹰谷,时时传来一声声悲惨的唳啸。陈老爹并没有摔去世,而是摔断了脊椎,再也不能健步如飞地行走,再也不能挥舞着杆子牧羊了。在陈老爹养伤的日子里,家人凌晨开门时创造,门口总是有人隔三差五地丢下一只野兔。
会是谁呢?
举头望天,一只鹰在陈老爹家屋子的上空,盘旋着。一圈,一圈,又一圈。久久不肯拜别。
后来,每年四月间,老鹰谷就会涌现上万只鹰聚群征象。
老鹰谷充满鼓噪。鹰鹰鹰鹰鹰。空中是鹰,胡杨枝头是鹰,红柳丛中是鹰,地上是鹰,河边是鹰,麦田里是鹰。鹰鹰鹰鹰鹰。如此多的鹰聚在一起,涌如今这里,到底是什么缘故原由呢?连鸟类专家也无法阐明。
我出差来老鹰谷看退耕还林,适值看到聚群的鹰。——唉,不禁吃惊地瞪大了眼睛。
生态须要空间的分布,也须要韶光的积累。修复了自然,也就治愈了自然。我模糊觉得到,随着生态系统的逐渐规复和稳定,老鹰谷里,所有的美好,都会准期而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