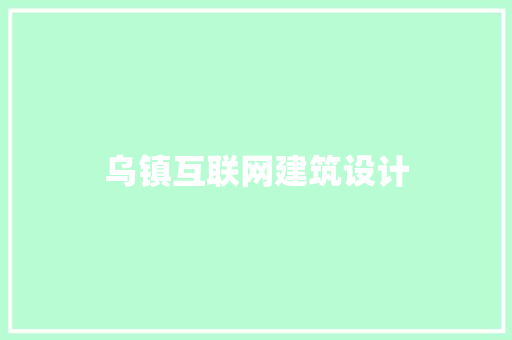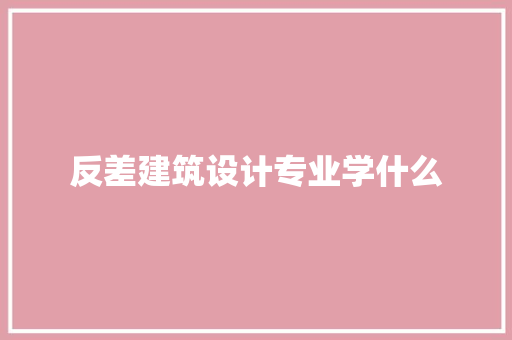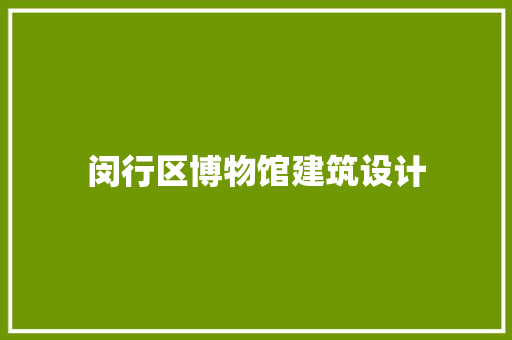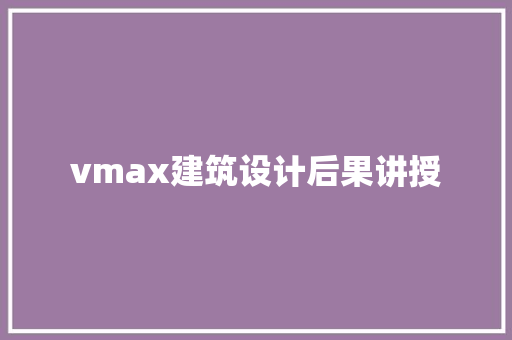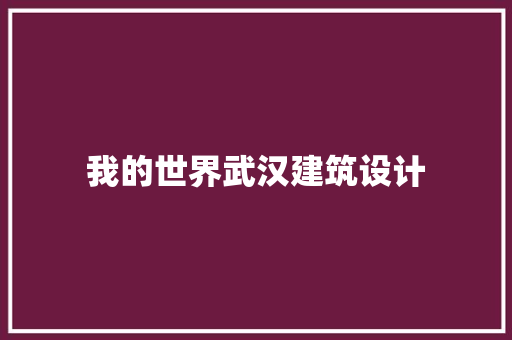一座工业建筑
位于黄浦江东岸的老白渡码头煤仓建于1984年。与大多数其它煤仓一样,它是煤炭从运输船上岸、储存、装载以及分配的节点。经由沿江的高架运煤廊道,煤炭被暂时存入八个储煤仓中,而在须要之时,通过相连的八个巨大的煤料斗落下,由卡车运输到须要的场所。这一合营生产的操作过程,强调经济与高效,而这也反响在了煤仓的原有构造上。很难说这座普通的煤仓建筑内在地有着某种艺术代价,但生产性工业建筑每每因其服从于功能性需求,采取最为经济、通用的框架构造,而具有一种朴素之美。在法国建筑师柯布西耶的《走向新建筑》中,他曾将被视为西方建筑源头的帕提农神庙与普通的谷仓和工业建筑的照片并置,从而暗示出普通工业建筑不逊于经典建筑的美学代价。中国建筑师张永和也曾在《向工业建筑学习》一文中亦从工业建筑推导出了“基本建筑”的主要观点。对付他来说,工业建筑受益于对经济与高效的追求,而频年夜多数民用建筑更为靠近建筑的实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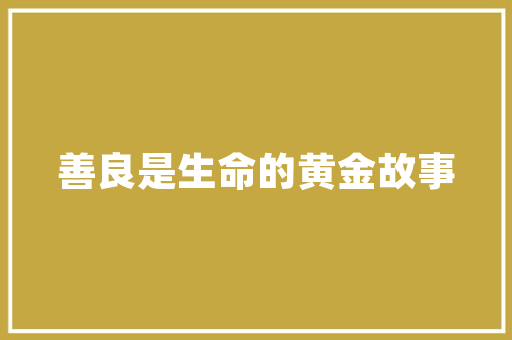
2009年,合营世博会的召开,老白渡码头所在的上海港煤炭装卸公司和上海第二十七棉纺厂进行了迁居。北至张杨路、南至塘桥新路的总面积近8.9万平方米的地块被方案为新的“老白渡滨江绿地”,而老白渡码头煤仓则被改造为了一座滨江不雅观景建筑。这次改造拆除了所有的添补围合墙体,仅仅保留了钢筋混凝土的框架构造。完备打开的构造,使得原来被外墙包裹的八个煤料斗如在X光视线之下,将它们自身呈现在了"大众年夜众的面前。在方案设计解释中,建筑师写道,“把建筑中巨大的储煤斗展现出来,供游客参不雅观。”位于北侧的斜向运煤通道被改建成为了一座钢构造天桥,直接通向煤仓顶部,使得人们得以“登高揽胜”,一饱浦江两岸的景致。位于黄浦江起势转弯之前的关键位置,老白渡码头及其滨江确实有着独一无二的城市景不雅观。对岸,是十六铺码头以及外滩历史建筑群;向南,可以远眺徐浦大桥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向北,则是陆家嘴鳞次栉比的高层建筑。可以说,在不同的方向上,它展示着上海城市历史的不同阶段。
2012年,这片绿地和不雅观景平台正式向"大众免费开放。然而由于缺少具有吸引力的功能以及滨江配套举动步伐的尚不成熟,老白渡滨江绿地在改造后“一贯鲜有人问津,参不雅观市民寥寥无几”。于是,这一片区在策划定位上被转向为一个“集艺术文化、时尚休闲为一体的翡翠滨江艺术区”。在新的操持中,翡翠画廊(Halcyon Gallery)将落户这里,作为不雅观景平台利用的煤仓操持将被拆除,并在原地新建一座画廊。所幸的是,在煤仓的人字形屋顶以及三角钢屋架被拆除后,它的命运又发生了改变。2015年,老白渡码头煤仓终极被确认保留,并操持将被改造为一座美术馆。在此之前,它首先被用作了2015上海城市公共空间艺术季“上海精良工业建筑改造案例展”展场,展出了包括老白渡码头煤仓改造在内的八个近年来的上海工业建筑改造案例。
在短短三十几年间,老白渡码头煤仓经历了多舛的变革:从做事于明确、直接的功能到功能的消逝,从完全的建筑构造到局部拆除、乃至险些被完备拆除。对付其的态度和策略的改变,既反响出城市发展所带来的构造性改变,亦折射出人们对付工业建筑的认知变迁。如果说它曾经虔诚地做事于工厂和生产,那么在本日,它的美学代价也逐步开始被认可。
一座美术馆
在经历数次变动之后,老白渡码头煤仓的原非构造墙体和屋顶均被拆除,一个高5层、长向7个开间、纵向2个开间的钢筋混凝土柱网和8个被柱网构造支起的煤料斗被完备地暴露出来,顶层则仅剩下两排残损的柱子,指向天空。几次短暂的改造也在煤仓的构造中留下了痕迹:运输煤炭的传送带被改建为了一座直达煤仓顶层的钢构造人行天桥。这便是大舍建筑的主持建筑师柳亦春在接手改造之时所面临的状态。当时,他这样记录道:“现状的煤仓便是因废弃而只剩下一副骨架,当我数次进入这个废墟,就像进入一种自然,没有了遮蔽的构造骨架的表面粉刷迅速风化,内里的混凝土透了出来。”
在2015年的展场改造中,大略的嵌入和叠加便使得老白渡码头煤仓知足了展览空间的需求。然而,当一座工业建筑须要成为一座美术馆之时,展览空间和面积的需求一下子使得改造难度陡然增加,特殊是考虑到煤料斗的构造和园地的分外性之后。常日的扩建每每会直接在原有构造的外围加建,将原有构造包裹个中,并进行必要的加固处理。然而,煤仓位于滨江高桩码头上,地理条件的繁芜注定了项目改造须要尽可能的避免根本施工,从而减小改造对现有码头及船只通畅的影响。所幸的是,煤仓原有构造依然有着较好的构造性能,那么是否可以发挥它的“余热”,来承托新增的楼板面积呢?在经由与构造师张准的多次谈论后,建筑与构造团队决定以一种“戴笠帽”的办法来知足新的空间需求。设计将为屋顶旧有的两排柱子“戴”上一个四边外挑的钢构造桁架,而楼下各层新增楼板则通过垂直钢拉杆层层下挂。这一奥妙的做法既避免了新增根本作业,又依托了原有构造的存在。新的构造,既成长于老构造之上,又在材料和构造形式上与之保持了分离的姿态。
进入到美术馆内部,原来的混凝土框架构造和煤料斗仍旧霸占着主导。它们既是空间的构造,也构成了展呈的界面。只有当不雅观众来到五层展厅,暴露的灰色钢桁架结才透露出了新构造的端倪。灰色的方形钢构造构件既是旧有的破损的混凝土柱子的收头,也承托起了新增的钢桁架。其上的钢桁架和墙体之间的交卸却暗示着桁架并未在此结束,而是向着两端连续延伸。来到五层的室外平台,答案才开始揭晓:那些不才层看似如立面构件一样平常的、斜向交叉的纤细的白色杆件原来也是新构造的一部分。如果说旧构造的自明性是不言而喻的,那么在改造后,构造是如何被建造的便成为了建筑师与构造师共同安排的一个反向的谜面:混凝土框架构造自大地颓然伫立,反抗着重力,而新构造则自上挂下,被混凝土框架所支承。谜面的解答则隐蔽在构造的细节之中。
改造后的艺仓美术馆与一侧的高架运煤廊道构成了一段连续的水岸景不雅观体验。从浦江对岸远不雅观,美术馆的滨江立面和长廊均以光洁的铝板勾勒出一段段横向的线条,形成了沿江界面的整体性与连续性。至北向南,旧有的混凝土排架被局部增设二层步道,步道之下的一系列通透的玻璃盒子则可被用作咖啡厅、商店或小展厅等;一些新构造从排架之上“长出”,支撑起几段冒出于郁郁葱葱的树木之上的三层不雅观景台;在一段“之”字型曲桥后,艺仓美术馆的水平错动的体量构成了滨江景不雅观步道的终点。然而与其说是一座美术馆,它却更像是景不雅观步道的延续与盘旋而上,美术馆则被步道与景不雅观平台包裹在内。即便不雅观众从浦东市区靠近艺仓美术馆,也可被一条坡道缓缓地引向面江一侧,进而到达美术馆位于二层平台转角处的入口。一段通往上层平台的台阶则使得进入美术馆这一行为在此时变得并非唯一。事实上,即便在美术馆闭馆布展之时,开放的步道和平台仍约请着不雅观众在此容身,眺望江景。
一座公园
正如煤仓曾经与长长的高架运煤廊道构成了一个生产性的整体,高架运煤廊道亦是改造的一个重点。如果说艺仓美术馆彷佛是一个拜访的目的地,那么改造后的高架运煤廊道,凭借其高低错落的平台以及点缀个中的咖啡、餐饮,则成为了一座滨江公园的有机组成部分。
当艺仓美术馆的立面将煤仓原来的构造包裹个中时,以不雅观景、休憩为主的功能使得高架运煤廊道依然能够保持原来的可见状态。不雅观察现有的高架运煤廊道,可以创造,竖向构架和横梁之间呈现出了清晰的搭接关系:它们并非被直接浇筑在一起,而通过两个金属构件被连接在一起。新的步道平台的构造也与旧排架呈现出类似的关系:在混凝土横梁上,一段横向的钢构造梁首先被固定,在其之上才连续铺设纵向的钢构造梁和压型钢板。被暗藏在平台和混凝土横梁之间的横向钢构造梁起到了如旧构造之间的连接构件般的类似浸染:从竖向构架到混凝土横梁再到平台步道,它们被轻轻地搭接在一起,而在视觉上保持着若即若离的效果。步道和铝板栏板之间的缝隙则更进一步地延续了这一逻辑。
在高架运煤廊道的高下,一系列不雅观景平台和玻璃盒子被支配。在一些局部,两片钢柱夹住混凝土排架,向上承托起一段三层不雅观景平台。只管不雅观景平台的重量仅由钢柱承担,但它和排架之间的相夹关系以及它的片状形状则使得其犹如自排架“长”出一样平常。事实上,这一固定办法也有助于加固旧有的构造。可被作为咖啡厅或是小展厅的玻璃盒子则以一种更为奥妙的办法与排架产生着联系。一片轻薄锋利的工字钢梁被按照3米的板跨置于原间隔为6米混凝土排架之间。然而与每每落于柱上的梁不同,这片钢梁则在两端由V字形拉锁固定和支撑,在事理上形成了一个张弦梁系统。玻璃盒子的顶面在四个角点被两道钢索悬挂于钢梁下表面。由此,玻璃盒子的内部构造得到的极大的自由:形成围合的玻璃仅需由细巧的框架承担自身的重量即可。从工字钢梁到V形拉锁,从钢构造顶面到玻璃立面,新构造和旧构造的关系在此被清晰、直接地呈现。
当生产的功能褪去后,改造后的美术馆和高架运煤廊道共同形成了一个开放的城市滨水公园,而原有的煤仓与运煤通道的旧构造则构成了这一城市公共空间的骨架。依托于它们,新的构造和功能被加入,并授予了旧构造以新的意义,使得它再次发挥“余热”。新与旧,在此共同依存,而相互彰显。
作者:莫万莉(青年建筑学者、策展人)
编辑:周敏娴
拍照:田方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