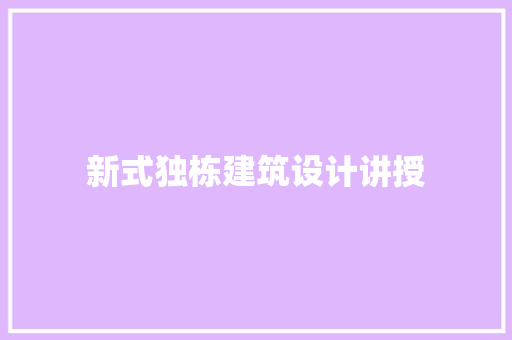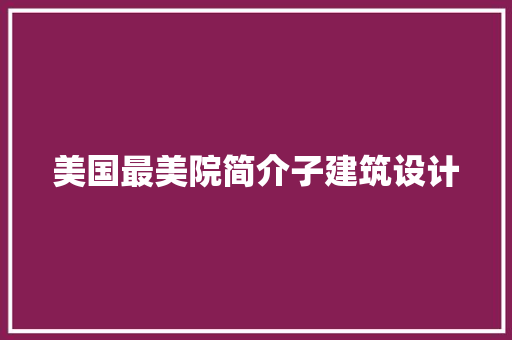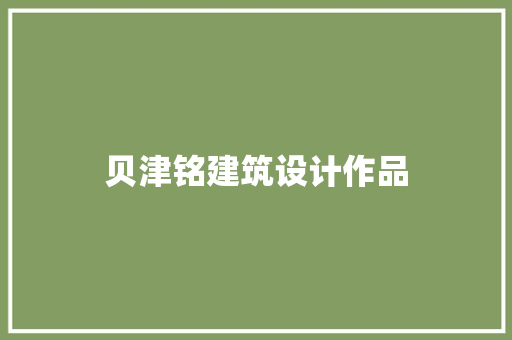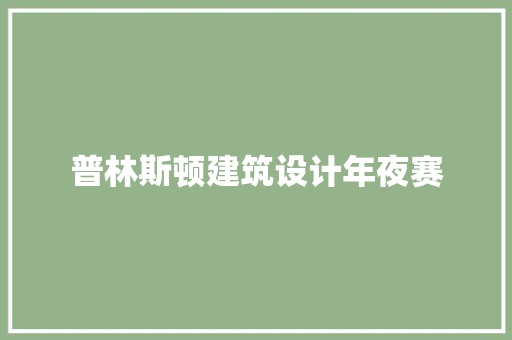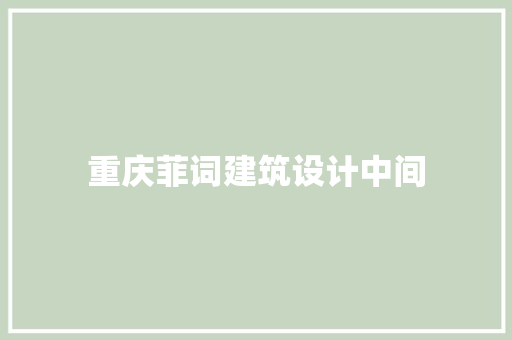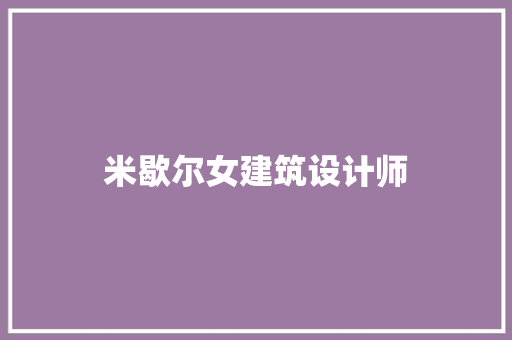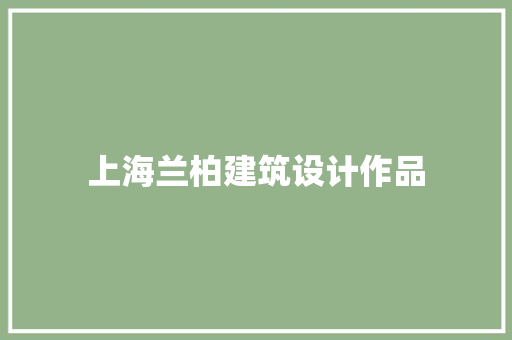从当时的角度看待问题,会将生理史算作国与国争、种与种战。但从今日的角度视之,则宜把这些问题生理化。在20世纪美国史里,我们仍不妨把欧洲裔的美国人权充这段历史的“主体”,把非裔美国人和亚裔美国人当作“他者”。如此做,即创造黑人这个“他者”和作为另一个“他者”的黄种人身影的涌现是十分有趣的比拟。以白人男性的生理作为一个中间支撑点的话,玄色人种与黄色人种恰好形成它的两端,在这两极之间呈现出张力:前者的雄浑性成为白人男性妒羡的工具,而后者的阴柔则引起他们对阳刚隳沉的恐怖,两者皆引起生理焦虑。

这个焦虑又因妇女运动的兴起而加剧:至19世纪末,美国传统性别角色已产生动摇,渐导致20世纪新性别不雅观之出身。偏偏在这个时候,一种在男性之间叫作“神经衰弱”的“世纪末病”成为时尚,引起更广泛的“文明没落”的焦虑。在文化生理层次上,向外洋做帝国主义扩展是证明自身的人种还未“退化”的一个测验,另一种考试测验则是营建“西部原野”的神话。至19世纪末,尤其在美西被横贯铁路贯穿后,美国的“西部”已被驯服,它在本色上逝去之时,却摇身一变成为一个传奇,且被奉为美国文化有别于欧洲的紧张特色。
\r\r 1.“黄祸论”成为时期话语\r\r美国在19世纪中期抵达加州后,已成为太平洋国家。1893年,美国进一步并吞夏威夷,成为亚太地区的国家。待并吞了菲律宾后,美国在东亚也有了地盘。这个形势,客不雅观地落实了20世纪是黄白两族大对决时期的前景。在1904年,赫斯特旗下的作家杰克·伦敦(Jack London,1876—1916)在旧金山的一份赫斯特报纸上为文鼓吹“黄祸论”。[1]他作为宣布日俄战役的战地,从中国东北凤凰城[2]发稿,谓人口浩瀚又勤奋的中国人如受具有统治才能的日本人领导,对白种人的后果堪虞。[3]当时,对欧美造成威胁的紧张这天本,中国人还不足格跻身当代文明之列。然而,在国际形势的刺激下,仍旧有中国作家在发霸权梦。[4]
\r\r老罗斯福总统本人并不是一个黄祸论者。在八国联军侵华期间,日本作战部队给予他良好印象,令他产生惜英雄、重英雄之感,并思在东北亚联日以制俄,因此他把日本升格至“文明”之列:“日本人在玩我们的游戏,由于他们在玩文明人类的游戏……”[5]事实上,日俄战役爆发之始,老罗斯福总统还暗中袒日。但日本降服了俄国之后,又产生坐大的担忧,因此他在1905年出面调解日俄战役,并因此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在制定条约进行期间,加州即因日本移民问题引发暴动,老罗斯福反对无效,反而逐渐顺应民情,认为种族主义潮流不可抵挡。
\r\r在1907年,美国的排日运动在日本引起强烈的种族仇恨。[6]老罗斯福却在该时敕令把美国海军的全部战斗舰调到太平洋,并从那里出发做环球一周的航行,这是有史以来首次有弘大的舰队做这类壮举的。该队船舰一律漆成白色,号称“大白色舰队”(the Great White Fleet)。在“种战”氛围弥漫的国际环境里,此举易被理解成白种人强权的耀武扬威。的确,老罗斯福一贯用海军作为他“巨棒外交”(big stick diplomacy)的工具。这次环球航行的外表虽是敦睦活动,但由于美方认为东亚海疆是不友善的,因此,在进入该海疆时,“大白色舰队”便进入鉴戒状态。[7]这也难怪,美国政府敦睦的外表底下藏着持续串正当的隐忧:1904年,日本在俄国的西伯利亚铁路即将完成之际偷袭了旅顺港,在美国的巴拿马运河竣工前夕,日本是否会维持原状,偷袭菲律宾、夏威夷,乃至加州呢?[8]此外,老罗斯福固然在日本移民问题上和该国达成“君子协定”(Gentlemen’s Agreement)[9],但日本在加州移民造成民愤,而美国在中国东北也有筑铁路的兴趣,若侵入日本的势力范围,势必造成两国关系的紧张。[10]因此,太平洋彼岸便变成美国的一个前哨。
\r\r在那个时期,主见向外扩展的帝国主义者多依据“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以及基于此原则的“种战”说。西方着眼于太平洋地区者,亦在预测环球范围的黄白大决斗。1895年,由于甲午一役显示东亚国家似模似样地打当代化战役,已有追上西方之势,德皇威廉二世为了示警而制一图,用日耳曼神话里的女武神(Valkyries)象征欧洲各国,与背负佛陀的一条中国龙作战,以守卫基督教的西方,他把此图复制后赠送西欧各政府。[11]1900年之义和团事宜无疑更强化西方人“黄祸论”生理。在19、20世纪之交,亚太地区如欧洲一样平常战云密布,日本和中首都有人主见20世纪将是黄白两大种族对决的时期。[12]既云“种战”,自身的种族是否“适者”的问题即被放上了议程表。
\r\r[1] Richard Hofstadter,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1860-1915(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45),p.163.赫斯特报系的《洛杉矶邮报》(Los Angeles Examiner)在1904年秋日亦登载一篇社论,曰《有黄祸否?》(“Is there a Yellow Peril?”),个中评论辩论日本人最近的进展以及他们与中国人缔盟之可能性——详见Ian Mugridge,The View from Xanadu:William Randolph Hearst and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Montrel and Kingston: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95),p.55。不知是否同一文章的转载。
\r\r[2] 即今辽宁省凤城满族自治县。——编者注
\r\r[3] Jack London,“The Yellow Peril”,in Revolution and Other Essays,http://sunsite.berkeley.edu/London/Writings/Revolution/yellow.html.
\r\r[4] 详见孙隆基:《科幻与现实》,载《南方周末》(2005年1月13日)以及孙隆基:《1908:黄祸论的一年——中、德、英三国文本的比较》,载《成大历史学报》第45号,2013年12月,第47—85页。
\r\r[5] Raymond A.Esthus,Theodore Roosevelt and Japa n(Seattle&London;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6),p.43.
\r\r[6] Bill Ong Hing,Making and Remaking Asian America through Immigration Policy,1850-1990(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p.28-29.
\r\r[7] Robert A.Hart,The Great White Fleet:Our Nation’s Attempt at Global Diplomacy in the Twilight of Its Innocence,1907-1909(Bost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65),pp.215-219.
\r\r[8] Frederick W.Marks III,Velvet on Iron:The Diplomacy of Theodore Roosevelt(Lincoln&Londo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82),p.55.
\r\r[9] 签订于1907年2月24日,老罗斯福哀求国会与加州停滞对日本人的歧视,而日本政府则答应限定往美国移民,详见William R.Nestor,Power across the Pacific:A Diplomatic History of American Relations with Japan(Houndmills,Basingstoke,Hampshire and 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1996),pp.82-83。
\r\r[10] Mikiso Hane,Modern Japan:A Historical Survey(Boulder and London:Westview Press,1986),p.201.美国有建筑一条和“南满铁路”平行的铁路之操持,因投资者哈里曼(E.H.Harriman,1848—1909)去世而未果,详见K.K.Kawakami,Japan Speaks on the Sino-Japanese Crisis(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32),pp.16-17。
\r\r[11] 详见孙隆基:《1908:黄祸论的一年——中、德、英三国文本的比较》。
\r\r[12] 详见孙隆基:《清季民族主义与黄帝崇拜之发明》,载《历史研究》2000年3号,第74页,已收入《历史学家的经线》。另详见Lung-kee Sun,The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from Nationhood to Individuality(Armonk,NY:M.E.Sharpe,2002),p.13。
\r\r 2.原野的空想和神经衰弱气质\r\r老罗斯福也是颇有造诣的历史学家,除了著述美国海军的战史之外,也曾于1889至1896间著有《西部开拓史》(The Winning ofthe West),此书认为美国的民族认同该放在西部。这个不雅观点启示了特纳“边陲学派”的美国史学。他们两人都悲叹至19世纪90年代美国的大陆边陲扩展已经抵达尽头,老罗斯福尤其担忧当代美国人已经变成“过度文明的人”,损失了雄浑性。[1]
\r\r在西部边陲行将消逝之时,也是美国人把西部原野神话化之始。“美国商业娱乐史上最大规模、最得人望,也是最成功的奇迹之一是野牛比尔的西部原野(Buffalo Bill’s Wild West)演出”,它从1883年持续到1916年,经久不衰。[2]这些演出是后来美国电影中“官兵大战红蕃”的原本。野牛比尔·科狄(Buffalo Bill Cody,1846—1917)这个明星本身是西部的传奇人物。1876年卡斯特(George A.Custer,1839—1876)将军在西部的小大角(Little Big Horn)一役全军尽殁后,科狄曾以斥候的身份参与对印第安人的报复性征讨,卡斯特将军随处颂扬的故事后来也成为科狄演出节目中的压轴戏。科狄之以是大红特红,是由于他表示了“男子汉之美”,也是“一个真实的美国边陲勇士倔强而天下无双质量之最佳模范”。[3]当时的舆论界对“野牛比尔的西部原野”演出竭力捧场,认为它重演征蛮战役有利于在过度文明的当代人身上规复先人开拓边陲时的武德;有人乃至视其与老罗斯福的《困难辛劳的生活》异曲同工,两者都唤醒了当代人身上“潜藏的蛮子”,那个在伟大的战斗民族的血液里“一点滴不能被革除的蛮子本能”。[4]在老罗斯福用“Rough Riders”来命名他组织的义勇骑兵队之前,它已经是科狄成立的一个天下性组织的名称,它是肩负文明国家对野蛮民族作战的神圣义务的未来骑兵队的模范。老罗斯福开始时没有在礼数上承认他命名的来源,只有在科狄指出参军者包括他的一些牛仔和印第安演员,老罗斯福才勉强表态。[5]但在美西战役后,科狄不念旧恶,仍把令老罗斯福一战成名的圣胡安高地之役变成他演出节目的压轴戏,取代了卡斯特将军的小大角之役,让老罗斯福名列民族英雄殿堂。至1901年这出压轴戏才让位给美军参加八国联军讨伐中国义和团的“天津之役”。[6]“红番”被义和团取代,万变不离其宗的是“文明”与“不开化”斗争的比喻,经久而弥新。
\r\r因此,老罗斯福在还未当总统前,已成为西部神话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他之当选,得力于他“西部英雄”这个假面之处不少。在老罗斯福直接鼓励和建议下,他哈佛大学的学弟欧文·韦斯特(Owen Wister,1860—1938)开始创作西部文艺小说,后其在1902年揭橥的《弗吉尼亚人》(The Virginian)是当代西部小说的老祖宗。如果没有韦斯特,很难想象会有日后大量的“西部牛仔”小说、电影、电视。[7]西部小说的源头虽然可上溯至19世纪上叶,但韦斯特征象的里程碑意义在西部边陲关闭后把“西部牛仔”予以神话化。这个东部哈佛毕业生笔下的主角“身上根本没有牛味”,他奠定一个与放牛职业无关的西部英雄模式。[8]在瓦格纳乐剧里的骑士英雄的启示下,韦斯特把他想要塑造的西部牛仔说成是“撒克逊祖宗的美国后代”。这个未驯服的精良人种目前正处于沉睡状态,有待卸下受染于旧大陆的“娘娘腔习气”(sissif ied manners),他的血液是纯粹的,其规复元气得赖西部的清洁环境,以便摆脱“从他乡侵入的害虫群,他们将我们的城市转变成巴别塔(Babels),将我们的公民变成杂种”。韦斯特歌颂了西部,却说牛仔这个精良人种是天生的,“并非一个新类型,亦非边陲的产物,只是果壳破了往后露出原始内核而已”[9]。精良人种论一样平常是重遗传而轻环境成分。这便是韦斯特写于1885年的《牛仔的进化》(“The Evolution of the Cow-Puncher”)一文的内涵。在1882年美国国会刚通过了《排华移民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故当代西部小说的出身具有世纪之交的“种战”背景。
\r\r韦斯特特殊将《弗吉尼亚人》这部小说奉献给学长老罗斯福。他们俩的出身的确有许多相似之处。韦斯彪炳生于东部大都会费城,父亲是年夜夫,母亲则是名伶之女,百口都喜好艺术。他在哈佛毕业后,赴巴黎攻读音乐,但不久即放弃,回到纽约当一名银行职员。由于康健状况不佳,就短期性地迁往西部,过原野生活,规复康健。后又于1885年进入哈佛的法学院,三年往后毕业。在执状师业一段期间后,才转行当作家,把他在美国西部的暑期履历当作创作的灵感。他在西部原野中探求自由,得到像“野兽一样平常”的觉得,和他摆脱妈妈的掌握有关——在这个意义上,他的妈妈象征东部的城居文明。[10]
\r\r老罗斯福则出生在东部大都会纽约的一个军人之家,爸爸因担当军职而常不在家,他从小就以为身心方面统统都不如父亲,至于母亲,则是一个神经质的女人。不知是否由于遗传,老罗斯福从小就患了哮喘病和视力不良,但年夜夫们创造他的呼吸器官并无欠妥,因此归因于他先天性神经质的气质[11],这种病症当时无以名之,但类似19世纪80年代初期才创设的“神经衰弱”这个观点——而这类病症正是男性变得女性化的征候。老罗斯福自己也承认在少年阶段意志薄弱、缺少纪律、无力气和行动笨拙。
\r\r老罗斯福的这种环境延续到将近14岁。一次他在严重的哮喘病产生发火后,偏偏遇见两个喜好欺凌弱小的同龄少年,“他们创造我是一个先天注定的受害者,遂存心地开始折磨我”。为了永久不再陷入这种“无助状态”,他听取父亲的疏导,开始用铁的纪律来重修自己的身与心。他立即在家中设立一间健身房,开始练举重,又聘请名师教导拳击,同时从事骑马和射击。[12]为了具有男儿的志趣,他从很早就培养自己对自然史和军事学的兴趣,但由于身体羸弱的缘故,仍得通过家庭西席受教诲,直到进入哈佛大学为止。老罗斯福“重修自我”的末了一步便是移往西部作为放牧牛群的牧场主,从一个天真的瘦小子蜕变为一个有钢铁一样平常意志、具有领袖魅力的人物。他除了参加捕盗之外,还制造了一出后来在好莱坞西部电影中被陈腔滥调化的戏码:有一天,他进入酒吧,里面有一个酒鬼两手各拿一支手枪辱骂其他的顾客,并且已经对墙上的钟射了几发子弹。这个酒鬼转向老罗斯福:“下一轮由你宴客了,四眼田鸡!
”老罗斯福被枪指着脸,佯装点头,然后一记右勾拳,一记左勾拳,再一记右勾拳打在对方的下颚,把他击倒。[13]
[1] Roderick Nash,Wilderness and the American Mind,3rd edition(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2),pp.149-150.
\r\r[2] Richard Stotkin,“Buffalo Bill’s‘Wild West’and the Mythologization of the American Empire”,in Amy Kaplan and Donald E.Pease,eds.,Cultures of United States Imperialism(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1993),p.164.
\r\r[3] “Buffalo Bill’s‘Wild West’and the Mythologization of the American Empire”,p.169.
\r\r[4] “Buffalo Bill’s‘Wild West’and the Mythologization of the American Empire”,p.174.
\r\r[5] Ibid.,p.176.
\r\r[6] Ibid.,p.178.
\r\r[7] Ben Merchant Vorphahl,“Roosevelt,Wister,Turner,and Remington”,in 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West,pp.288-289.
\r\r[8] Lou Rodenberger,“The Novel of the Cowboy”,in 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West,p.524.
\r\r[9] Vorphahl,“Roosevelt,Wister,Turner,and Remington”,pp.288-290,293.
\r\r[10] G.Edward White,The Eastern Establishment and the Western Experience:The West of Frederic Remington,Theodore Roosevelt,and Owen Wister(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68),pp.124-125.
\r\r[11] David McCullough,Mornings on Horseback:The Story of an Extraordinary Family,a Vanished Way of Life and the Unique Child Who Became Theodore Roosevelt(New York:A Touchstone Book,1981),pp.91-93.
\r\r[12] The Autobiography of Theodore Roosevelt,condensed from the original edition,supplemented by letters,speeches,and other writings,and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Wayne Andrews(N.Y.:Charles Scribner’s Sons,1958),pp.26-27.
\r\r[13] Nathan Miller,Theodore Roosevelt:A Life(New York: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Inc.,1992),pp.164-165.Michael L.Collins,That Damned Cowboy: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American West,1883-1898(New York:Peter Lang,1991),pp.50-51指出这个事宜发生在1885年5月,于蒙坦纳与德科达边疆的一个小镇。
\r\r 3.野性的呼唤\r\r中国男孩在发展过程中很少有与人斗殴的履历,较难明得老罗斯福的童年遭遇之范例性。近日美国新男性运动的理论家山姆·基恩(Sam Keen)回顾他14岁时发生的“末了一场真的斗殴”(last real f ight):提及来真丢人,他被一个“娘娘腔”(sissy)揍了。“当天晚上,彷佛在一个漫画故事里的场景般,我起誓在未来永久不挨他妈的娘娘腔的揍”,他开始磨炼身体,矢志把“一个98磅的柔弱者转化成一个既精瘦又凶恶的打斗机器……多年以来,一贯到35岁,我都一贯在青年会做健身运动”。[1]由此可见,从19、20世纪之交到20世纪之末,这个美国男性空想是经久不衰。
\r\r老罗斯福的原野空想,使他认为西部才代表真正的美国,也令他大力促进保护美国境内自然环境的运动。他确当局圈定受保护的国家森林地区,比他的三位前任加起来还要多;他在总统任内把国家公园的数目增了一倍,其保护自然环境政策使后代受益匪浅,但其精神和今日的环保很不一样。后者每每和女权、和平运动与非暴力主义连在一起。老罗斯福的一个嗜好则是佃猎。他在1909年卸任总统职后即前往非洲佃猎,为纽约的自然博物馆网络动物标本。今日家喻户晓的“泰迪熊”(Teddy bear)正是由他的名字(Theodore=Teddy)命名而来,其渊源相传是他施恩不杀一头老态龙钟的病熊。
\r\r显然,老罗斯福保护未被人工毁坏的原野意图并非道家式的崇尚自然,而是掩护粗犷的野味,以便抵制都邑化的柔弱和本能退化。这个通过“原野”来让生命力重新呈现的憧憬,也表现在他同代人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The Call of the Wild)中;在这部揭橥于1903年的小说里,一头家犬回物化然后规复为狼,但它是先受过文明的洗礼才去“重温”野性的,因此又比一样平常狼狡猾,反而成了狼群之首。老罗斯福和杰克·伦敦笔下的“自然”并非是自然本身,而是经人工授予了代价的“自然”,它毋宁是一个文化符号。中国人方向把自然想象成“母怀”者,也并非真的让自然摆脱人为的机心,还它一个天真纯朴,仍旧是人追求逍遥安适的意图之投射。美国人欲坚持自然之粗犷,则是极力把自然男性化,而“男性”的准则是主动和宰制。
\r\r因此,老罗斯福的保护“自然环境”不用除人力对自然的积极干涉,例如,利用联邦政府的力量大量灌溉西部的荒地,填平沼泽,以及从事大规模的植林。他说1902年填平沼泽的工程须要战胜的障碍和巴拿马运河工程的一样平常艰巨,他确当局为灌溉工程而筑的水坝也“比先前在世界任何地方筑的都来得高”[2]——倒是有点像当时的“三峡工程”了!
它除了为后人保留资源的理智思维之外,也表现成事在人的思想。
一位研究美国人原野空想的学者说:“美国人对未经人手改造的自然是不生感情的。不断把原野空想化的考试测验终于制造出一门贫瘠的、充满公式化的艺术:‘西部故事’。”[3]西部故事里的“独行侠”(the lone ranger)正是这个原野的神话化。它透露美国文化中男性的雄浑空想:一人一马一枪,驰骋在原野间。这个“原野”并非如母怀一样平常的大自然,而是充斥响尾蛇与带刺的神仙掌,个人并不从它的怀抱里探求抚慰,而是“雄浑地”凌驾于其上。然而,老罗斯福时期已闻环保运动的先声,当时西方文化里呈现“历来由土著与远东文化持有的不雅观点”,即自然界非因人而存在,有其自身目的存焉。[4]老罗斯福具有“大猎物的狩者”(a big game hunter)的一壁“不一定为公众年夜众所喜好”。[5]
\r\r[1] Sam Keen,Fire in The Belly:On Being Man(New York:Bantam Books,1992),pp.35-36.台译《新男人:21世纪男人的定位与角色》,山姆·基恩著,张定绮译(台北:时报出版社,1994年)。
\r\r[2] The Autobiography of Theodore Roosevelt,p.213.
\r\r[3] Leo Marx,The Machine in the Garden:Technology and the Pastoral Ideal in America(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pp.141-142.
\r\r[4] Ralph H.Lutts,The Nature Fakers:Wildlife,Science and Sentiment(Golden,Colorado:Fulcrum Publishing,1990),p.21.
\r\r[5] The Nature Fakers,p.1.
\r\r 4.世纪之交的美国男性焦虑\r\r老罗斯福的时期也见证美国妇女积极争取投票权的运动。老罗斯福在原则上资助,却同时提醒妇女们:“提倡妇女投票权的人们,除非她们是全然地并油滑地损失精确不雅观察事物相连性的能力,该记住未来第一流的妇女形态在实质上该与现在和过去的高档者一样——凭聪慧、勇气和效率来扮演那个在所有社会职责中至为主要的妻母之职。”[1]“有些古老的真理只要地球存在一日就会是真的,不论进步到什么程度都不会改变。这个真理之一是丈夫的紧张职责是养家,他必须养活妻子和儿女,而妇女的紧张职责是作为内助、家庭主妇以及母亲……因此,在超过了某一个点后,两性的演习假若正常就该有别,由于两者的职责正常来说也是不同的。这并不虞味功能上的不平等,但它意味在正常环境下功能的不相似。”[2]
\r\r在19、20世纪之交,把“两性的演习假若正常就该有别”这个命题学理化者,是斯坦利·霍尔(G.Stanley Hall,1844—1924)的男女教诲分途说。他认为男与女在生理上很不同,在发展的关头上,任何一方必须在不受对方的影响下,才能“顺乎自然地”发展得完全。他提倡男性在小男孩阶段必须“重温”(recapitulate)人类进化的初民阶段。他责备当代教诲,尤其是女老师把小男孩都弄得柔弱化了,再下去会造成人种退化的危急(细节详见第三章)。然而,“重温”是否故意制造“返祖征象”呢?非也!
当时的一个盛行学说认为:人从怀胎到出身是在九个月之内重温从单细胞到人类的千百万年进化过程,而文明人的童年阶段则相称于“初民”的进化水平。[3]我们不禁要问:文明人既然已达更优胜的高等阶段,为何还去“重温”低级阶段?
在这里,把霍尔的生理学和特纳的历史学做个比较,有利于发挥它们两者未为古人所道的含义。1893年,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特纳在美国历史学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芝加哥年会上揭橥“边陲说”,实在也是一种“重温说”。和霍尔的一样平常,特纳的理论框架也是直线进化阶段论,并且隐若可见斯宾塞“进化是从同质状态到异质状态”命题的痕迹:
\r\r把我们的把稳力限定于大泰西沿岸的话,就只会看到熟习的征象,亦即是在一个被范围化的区域内的制度进化史,例如代议政府的兴起;大略的殖民地政府之分解为繁芜机构;从没有分工的原始工业社会进步上升到达制造业文明。但除此之外,我们在扩展过程中达到的每一块西部地区都让这个进化过程重演一遍。因此,美国的发展不单只呈现直线的提高,而是在不断提高的边陲线以及在该地区的新开拓上回归原始状态。[4]
\r\r在特纳心目中,美国“边陲”不同于欧洲国家的边陲,后者是划过人口稠密地带、堡垒林立的国防线,前者则是“未开化(savagery)和文明(civilization)的交卸点”。[5]正是这种“边陲”塑造了美国的国民性情,其紧张特色便是运动,它造成“美国精力将不断哀求更广阔的操作园地”。特纳光彩这个性情已经成形,但同时感叹美国大陆扩展空间已关闭:“如今,在美洲被创造后的400年、在宪法底下生活100年的末期,边陲已逝去,随着它的消散,美国历史第一期亦告一段落。”[6]
\r\r当时,“文”与“野”的辩证关系也造成“达尔文主义”内部的紧张。达尔文本人只研究生物学,不涉及人类社会,且从未为人类出息设定一个目的方向。在他的名字笼罩的时期,实在包含各种各样的思潮,在此大略化为两类:其一为社会进化论,其二为人种退化论。前者脱胎于启蒙时期的人类直线进步不雅观,它后来钻进达尔文生物进化说里,将其化为一种目的论的历史哲学。在美国,这种“达尔文主义”且成为展现基督新教文化的救世主义的新路子,其目的同为降服邪恶,把人类臻于至善。[7]至于人种退化论,则是比启蒙时期进步不雅观涌现更早的“人类堕落说”(《圣经》里的失落乐园)、“历史退步不雅观”(上古的黄金时期不再现)、“文明没落论”(罗马帝国的衰亡)等的生物学版。
\r\r这两者同为“达尔文主义”,其意向却全然相反。前者认为“文明”代表进步,它是宇宙进化已造成人类这个理性动物之来临,并战胜了“自然”。后一种“达尔文主义”认为“文明”违反“自然”,它让人工的东西斫丧了天然的本能,导致物种退化和绝灭。第一种“达尔文主义”表现的是启蒙式的乐不雅观,后一种“达尔文主义”则是世纪末颓废的悲歌。当时持此论者控诉工业化的大都会是违反自然的场所,在那里各种污染、毒剂汇聚,恶习、疾病(尤其是梅毒)盛行,此环境中塑造的人种势必退化。[8]当代生活快速和不自然的节奏对人的心身都造成损毁,使神经衰弱成为当代社会的征候,不禁令人疑问高度发展的文明是否等同“颓废”(decadence)。
\r\r霍尔想在文明和自然之间坚持一个平衡,遂提倡从尚未全面进入“文明”的男孩下手,哀求教诲者尤其是女老师不要约束他们的蛮性,在这个阶段上只管即便让他们发挥原始本能。既然他们发展的各阶段会“重温”人类文明的进化史,待至成年阶段自然会超越“初民”阶段,但如能保留一个康健的本能内核,就可让物种朝更高阶段进化。至于女孩,霍尔却不主见她们去“重温”初民阶段。在他眼中,女性代表的正是“文明化”功能,对复活了的男性本能具制衡浸染,但文明只有女性一壁就静止了,没有男性带头冲锋的文明便是守成。而这个把“女性化”等同“守成”的理念与老罗斯福的男性空想何其相似!
后者正是用美国将沦为“西半球的中国”的警告,来呼唤“男子汉气概”。
在上面,我们已提到美国人的原野空想。现在不妨用上述两种对立的“达尔文主义”来参照它。在乐不雅观的启蒙式社会进化论的话语里,“文明”是男性,被战胜和被改造的“自然”则是女性——在个体的层次上,男性人格代表理性已控驭了自然(本能),而不长于节制感情、方向身体化的女性则更为靠近自然状态。但到了“世纪末”退化论的话语里,“文明”则变成女性,而返回自然界、试图恢复原始本能的男性则变成用粗犷的“原野”来象征。这两种自然不雅观都扯不上母亲的怀抱。前一种乐不雅观的启蒙式社会进化话语正表示前述“美国人对未经人手改造的自然是不生感情的”这句话;后一种“世纪末”退化话语则提倡注射一两剂原始兽性来匆匆成文明的再生(regeneration of civilization),这个兽性不是女性化的“自然”,而是生存竞争的阳刚领域。
\r\r担心白种男性呈现退化状态,正是霍尔主见让小男孩“重温”原始性的时期背景。同样的顾虑在那个时期匆匆成了童子军的涌现(细节详见第三章)。在19世纪初,美国母亲教养儿子的角色比重远不如今日,至19世纪末,工业化系统编制涌现,父亲从自耕农或小所有者朝当代工人或上班族演化,由母亲教养儿子变成主流。[9]同时,女子教诲与女子就业的兴起,令小学里开始聘任女老师,女性的“阴”影遂沉沉地笼罩在男童头上。[10]于是,“教诲界展开运动以掌握正在蔓延的小学里女西席压倒男西席的比例,乃至想逆转大学里男女同校的潮流。激烈的体育竞赛、户外露营、打猎以及钓鱼快速地成为被喜好的活动。崇尚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支配了政治作风与社会学理论。强调兽性本能和力量的自然主义影响了美国的小说家”[11]。可以预期,在大众舆论敲响“男性被女性化”的警钟而“规复野性”又成为时尚的环境下,在20世纪初催生了童子军运动,该运动“具有减轻童军教练及其所教练的男童之男性焦虑的功能”。[12]
\r\r[1] “Women’s Rights;And the Duties of Both Men and Women”(The Outlook,February 3,1912),The Works of Theodore Roosevelt,Nation Edition(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26),vol.16,p.217.
\r\r[2] “The Woman and the Home”(Address before the National Congress of Mothers,Washington,D.C.,March 13,1905),The Works of Theodore Roosevelt,Nation Edition,vol.16,p.165.
\r\r[3] Gail Bederman,Manliness&Civilization;A Cultural History of Gender and Race in the United States,1880-1917(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pp.92-101.
\r\r[4]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The Signif 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www.learner.org/channel/workshops/primarysources/corporations/docs/turner.html,p.1.
\r\r[5]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p.2.
\r\r[6] Ibid.,pp.4-5.
\r\r[7] Bederman,Manliness&Civilization,pp.25-27.
\r\r[8] Kelly Hurley,“Hereditary Taint and Cultural Contagion:The Social Etiology of Fin-de-Siècle Degeneration Theory”,NineteenthCentury Contexts,vol.14(1990),no.2,pp.193-214.
\r\r[9] 在内战以前,美国男人有88%是农夫和自雇的小贩子,至1870年,这个比例已降为2/3,到了1910年,再度降为低于1/3,至80年代,只剩下10%。详见Michael S.Kimmel,“The Contemporary‘Crisis’of Masculinit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in Harry Brod,ed.,The Making of Masculinities(Boston:Allen&Unwin,1987),p.138。
\r\r[10] Redding S.Suggs,Motherteacher:The Feminization of American Education(Charlottesville: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1978).
\r\r[11] Ann Douglas,The Feminiz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New York:Anchor Books,1977),p.327.
\r\r[12] Joseph H.Pleck,“The Theory of Male Sex-Role Identity:Its Rise and Fall,1936 to the Present”,in Harry Brod,ed.,The Making of Masculinities,p.23.
\r\r 5.神经衰弱成为“时尚病”\r\r“神经衰弱”已不获今日医学界承认,但从“世纪末”到第一次天下大战期间它是西方的盛行病,往后逐渐为生理学化的话语所取代。“神经衰弱”在中国却经久不衰。根据西方生理学家的不雅观察,由于中国人有把生理问题“身体化”的方向,在大陆和台湾,这个名词都通用到20世纪70年代末,成为原谅统统生理病症的笼统名称。[1]在西方,从侧重用神经系统一类的生理学观点去阐明精神问题过渡到存心理学用语,大致上是在20世纪的头10年,此后“神经衰弱”这一类的名词即衰落,渐被包括弗洛伊德学说在内的生理学话语所取代。[2]在中国,“神经衰弱”观点之以是持续到20世纪下半叶,是由于中国人“生理”的观点不发达,但近年来在台湾西化的中产阶层之间,生理化思维开始盛行,这方面的做事和消费迟早也会传到大陆去。
\r\r“神经衰弱”这个名词的创设者非只一人,但后来的功劳都归于霍尔的好友乔治·米勒·比尔德(George Miller Beard,1839—1883)。[3]他在1869年就创设了该名词,但至生命晚期才完成学说,并把它揭橥在1880年和1881年出版的两部著作中。比尔德善于把科学的新发展、社会学说以及道德呼吁相结合,并用一个名词综括,因此很快就把该名词传播开来,成为大家的口头禅。当时,这种病症的阐明是把新创造的热力学能量守恒定律作为比喻,指人的中枢神经里的能量不敷运用、涌现衰竭,罪魁是“当代文明”。[4]它险些无所不包:焦虑、绝望、恐怖症、失落眠、把稳力不集中、极度疲倦、心跳、偏头痛、消化不良以及性无能。[5]
\r\r神经衰弱和当代文明可说是二位一体,因此神经衰弱引起人们的爱憎双重情绪。一方面,“神经衰弱”成为一种光彩。比尔德本人即强调“神经衰弱由最高度发展的文明造成,因此神经衰弱的蔓延足以证明美国乃有史以来最高级的文明”。纵然在美国,它亦只困扰英裔而不及移民、黑人、亚裔和美洲土著,城居者也比乡下人较易受其侵袭。[6]美国在华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1845—1932)在1894年揭橥了一部谈中国国民性的著作,把“缺少神经”(absence of nerve)当作中国人的优点,但它的意思是中国人无论在如何不堪的环境里皆能生存,实在有十分掉队、几近动物之意。[7]杰克·伦敦比较看得起中国人,他真正歧视的是韩国人,他称韩国为“没有神经的(nerveless)、被摈弃的国度”,由于韩国人“习气于挨任何闯入他们国家的外来者的揍和抢劫,从不抗议或抵抗”。[8]
\r\r“神经衰弱”之作为一种光彩,也反响在它起初是“精英病”这一个征象中。病患者多数是神经较为纤细的清闲阶级、艺术家,以及各种“劳心”的职业分子。长期或短暂传染“神经衰弱”的病人名单念起来恍如文化界的名人录,他们包括:伊迪丝·华顿(Edith Wharton,1862—1937)、艾玛·戈德曼(Emma Goldman,1869—1940)、亨利·詹姆斯、狄奥多·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1871—1945)、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1871—1922)、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1882—1941)、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鲁一士(Josiah Royce,1855—1916)、乔治·桑塔耶拿(George Santayana,1863—1952)、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艾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1858—1917)、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斯坦利·霍尔和杰克·伦敦。[9]
\r\r老罗斯福童年时患神经衰弱,听了年夜夫的话迁到西部边陲,过骑马放牧的生活以做治疗。履行同一种治疗法者包括他的学弟——小说家韦斯特,以及艺术家雷明顿和伊肯斯。[10]韦斯特是西部文艺小说的肇祖,已先容于前。弗雷德里克·雷明顿(Frederic Remington,1861—1909)是东部人,出生于纽约,然而正是他在西部疆界行将消逝时期末了用雕塑和绘画的办法把“西部”捕抓下来,使其不灭的形象成为美国大众想象的遗产。他在1888年替老罗斯福的《牧场生活》(Ranch Life)一书插图。[11]在1898年,雷明顿作为美西战役的战地,为赫斯特的报纸供应战地绘画,在把老罗斯福抬举成民族英雄的圣胡安高地一役中,雷明顿事实上是亲历其境。托马斯·伊肯斯(Thomas Eakins,1844—1916)是画家、拍照师、雕塑家与美术教授。这个费城人亦于1887年访问西部,以规复被东部城居生活所斫丧的元气。伊肯斯以西部牛仔和拳击手为题材的绘画,使历来的艺术评论家都以他的作品为“无羁勒的男性力量”(unbridled masculine power)的表现,但近人指出他自身的男性形象是与时期的持续串协议,一方面迎合当时的男性空想,同时参与对这个空想的塑造和合法化,伊肯斯的艺术实在亦透露同性恋的成分。[12]韦斯特等人各自用不同的媒体塑造了“西部牛仔”的浪漫形象,因此这个神话模范可以说是东部城市的神经衰弱病患者的一个生理倒影。这些人物在西部的“蹲点”或参与西部神话的塑造成为后来名成利就的踏板,尤其是老罗斯福,他切实其实把自己的“神经衰弱”变成一个传奇,“在当时的有名度好比华盛顿的樱桃树和林肯的木屋”。[13]
\r\r德国社会学家也是当代社会学鼻祖之一的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1858—1918)把神经衰弱当作当代文明的中央特色。他在1903年的著名演说《大都会和心灵生活》可能是所有这类论述中最深刻的,值得细引:
\r\r大都会型个体的生理根本便是神经刺激的加强,缘故原由是外在和内在刺激的快速和无间断的转换。人是有分判力的动物。一个瞬间的印象和先前的一个印象有差异,他的心灵就受到刺激。历久性的印象,彼此之间只有少许差异的印象,遵照惯常渠道的印象而又表现惯常之差异的比拟者——这些比起快速密集的印象转换、在一暼瞬间所能节制范围内涌现尖锐断裂,以及印象呈现的不可预期性对意识的消耗都要来得低。这些正是大都会创造的生理条件……大都会对有分判力的人征取的意识能量有异于村落庄生活。在那里,生活节奏和感官心灵印象的呈现都比较慢、比较惯常、比较均匀。正是通过这个关联,我们才能理解大都会生理生活(psychic life)的高度文明性情——它和依赖深切感情关系的小城镇生活对立……[14]
\r\r面临大都会的刺激,当代心灵必须加强自身的保护机制,那便是过度地发展“智力”。这个畸形发展一定对人的情绪浸染征取巨大代价,但这个代价是高等文明必须付出的,尤其是精英分子,这从齐美尔对“愚笨伯”免于神经衰弱的评论中可以看出:
\r\r如果有一种生理征象是百分之百为大都会预留的,那便是“玩累了”(blasè)的态度。这种态度首先来自对神经的缺少折衷的刺激,而它们快速转换并且高度浓缩。大都会的智力高度发展也具同一来源。因此,在智力上不是很生动的愚笨伯常日不会“玩累了”。无边地追求享乐生活固然会使人“玩累了”,由于它把神经震撼达到它们反应功能的最高强度,而且长期如此,甚至它们末了停滞反应。同样道理,纵使比较无害的印象,由于它们转换之迅速和彼此抵牾,把神经粗暴地到处拉扯,甚至它们末了储备的力量都耗光了;如果人留在同一个环境里,他们就不会有韶光补充新精力。因此,遂缺少对新觉得做出反应的适当能源,涌现的是一种无能感……[15]
\r\r至于神经衰弱由精英阶层的“时尚病”(maladieàla mode),到摆脱阶级特色、达到“民主化”,则是后来的事。这种征候的全民化,为社会带来了“神经衰弱的买卖”(neurasthenia business)、“神经衰弱时尚的生产”(neurasthenia fashion production),以及“神经衰弱市场”(neurasthenia market)。[16]这里是指各种药品、治疗、辅导、复健技能,以及与之相应的广告和推销奇迹。到了这一步,西方文化可以说充分展现了“当代性”特色。随着20世纪的进展、社会大众的日趋中产阶级化,人们的“当代病”的场址已从神经系统进展至心理化,而这些征象之有无亦成为判断一个当代文明程度高低之准绳。
\r\r但是,疾病纵使是一种光彩,它究竟是疾病,引发人们的爱憎双重生理。有关神经衰弱的比较史学研究指出:在德、法两国,这种病症尤其和“世纪末思潮”结合,亦即是和劣种遗传和人种退化的学说合流,而且每每被放在民族衰亡的文脉里评论辩论。[17]“世纪末”思潮的特色是把文明和颓废等同,因此文明发展程度越高,它离衰亡的命运越靠近。“文明即是疾病”的命题无疑是和“当代化便是进步”不雅观念打对台的理念,至今日仍存在,特殊是表现在文艺方面。[18]这种题材在“世纪末”思潮里占了上风。
\r\r做神经衰弱的比较史者认为:美国人不像德国人、法国人那般悲观。但他们只着眼于比尔德的立论,没有细心稽核其他病患者的危急论言谈。像老罗斯福的《困难辛劳的生活》这份文献,里面虽然没有片言只字提及神经衰弱,但如果熟习他患病背景,就知道他提倡“困难辛劳的生活”正为了战胜神经衰弱造成的柔弱性情。如前所述,他以中国为反面教材:“我们尽可能不要扮演中国的角色,安于在自己境内过可耻的安逸生活,逐寸地烂掉,而忽略于境外的事情。”他告诫美国如果沉沦腐化为“西半球的中国”的地位,就将不能跻身于“文明国家”之列。在贰心目中,中国大而无当,毫无面对寻衅的能力,遇着些许障碍就打退堂鼓,甘心躲在家里“过可耻的安逸生活”。这个神经系统薄弱的描述,和明恩溥中国人“缺少神经”的说法实在并无冲突,由于后者指中国人在如何不堪的状况下都能生存,乃是一种向环境低头的唾面自干态度。
\r\r[1] Keh-ming Lin,Arthur Kleinman,and Tsung-yi Lin,“Overview of Mental Disorders in Chinese Cultures:Review of Epidemiological and Clinical Studies”,以及Arthur Kleinman and David Mechanic,“Mental Illness and Psychosocial Aspects of Medical Problems in China”,in Arthur Kleinman&Tsung-yi Lin,eds.,Normal and Abnormal Behavior in Chinese Culture(Dordrecht,Holland: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1981),pp.258-259,334-336。
\r\r[2] Marijke Gijswijt-Hofstra,“Introduction:Cultures of Neurasthenia from Beard to the First World War”,in Marijke Gijswijt-Hofstra and Roy Porter,eds.Cultures of Neurasthenia From Beard to the First World War(Amsterdam and New York:Editions Rodopi B.V.,2001),p.21.
\r\r[3] Simon Wessely,“Neurasthenia and Fatigue Syndromes:Clinical Section”,German Berrios&Roy Porter,eds.,A History of Clinical Psychiatry:The Origin and History of Psychiatric Disorders(London&New Brunswick,N.J.:The Athlone Press,1995),p.509.
\r\r[4] Simon Wessely,“Neurasthenia and Fatigue Syndromes:Clinical Section”,p.511.
\r\r[5] Gijswijt-Hofstra,“Introduction:Cultures of Neurasthenia from Beard to the First World War”,p.2.
\r\r[6] Tom Lutz,“Neurasthenia and Fatigue Syndromes:Social Section”,in Berrios&Porter,A History of Clinical Psychiatry,pp.535-536.
\r\r[7] Arthur Smith,Chinese Characteristics(New York:Revell,1894),p.162.
\r\r[8] Jack London,“The Yellow Peril”,p.1.
\r\r[9] Lutz,“Neurasthenia and Fatigue Syndromes:Social Section”,pp.539-541.Lutz在他成书的著作中,光列美国的名人录,名单更长,详见Tom Lutz,American Nervousness,1903:An Anecdotal History(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1),p.19。
\r\r[10] G.Edward White,The Eastern Establishment and the Western Experience.
\r\r[11] Vorphahl,“Roosevelt,Wister,Turner,and Remington”,p.292.
\r\r[12] Jennifer A.Greenhill’s review of Martin A.Berger,Thomas Eakin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Gilded Age Manhood(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in Archives of American Art Journal,vol.40,no.1/2(2000),pp.18-22.Berger的论据是伊肯斯在世纪性的男子汉气概大测试——南北战役一役里躲避了兵役,他与一位男性朋友的一帧背面全裸照片,他在美术教室上首次把男模特儿的遮羞布拿掉并因此导致解聘,以及他的绘画中对拳击手屁股的强调。
\r\r[13] Lutz,“Neurasthenia and Fatigue Syndromes:Social Section”,p.541.老罗斯福向全天下发布的并非自身的残障,而是他终极把它战胜的毅力以及由此缔造的新人格格局。后来他患小儿麻痹症的侄孙小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 Jr.)亦当选为美国总统。较近期的例子是共和党总统竞选人鲍勃·多尔(Bob Dole)在电视上为“伟哥”做广告,公开自己的不举症。
\r\r[14] Georg Simmel,“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in David Frisby and Mike Featherstone,eds.,Simmel on Culture:Selected Writings(London:SAGE Publications,1997),pp.175-157.
\r\r[15] Simmel,“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p.178.
\r\r[16] Gijswijt-Hofstra,“Introduction:Cultures of Neurasthenia from Beard to the First World War”,p.25.
\r\r[17] Gijswijt-Hofstra,“Introduction:Cultures of Neurasthenia from Beard to the First World War”,pp.11,20-21.
\r\r[18] 例如贾平凹1996年的小说《废都》仍发挥都邑代表颓废与疾病、屯子代表康健与生命之母题,并用一头往城市送奶的牛受到城市熏染而去世亡做讽喻,他的议题却是当代的:20世纪90年代“文人下海”的征象。不懂该母题背后“文明没落论”的谱系学的文学研究者,竟然有将贾平凹小说的英文标题翻译成The Abandoned Capital者。
\r\r 6.神经衰弱与阳刚隳沉的梦魇\r\r《困难辛劳的生活》这份文献里声嘶力竭地鼓吹“男子汉气概”,亦透露出阳刚隳沉的危急感。根据当时盛行的见地:“神经衰弱”是男性的一块遮羞布,实在它和女性的“歇斯底里”是同一种病,只不过男人为了不蒙“女性化”之羞,才玩这种失落包名词的游戏。[1]这个说法虽缺少专业性,却反响大众的意见。老罗斯福标榜他降服了神经衰弱,实在便是标榜战胜了自身的“女性化”。在当时,歇斯底里的病人以女性居多,而神经衰弱则以男性为众,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个男女分途征象肯定有社会与文化的成分。纵然患神经衰弱的是男多于女,医师对患同一种病患的两性的治疗法亦背道而驰:他们给男性的处方是常常从事有活力的活动,例如老罗斯福的西部放牧生活,乃至他的《困难辛劳的生活》都可当作一剂药方;医师给女性的处方则是多在家安歇,后者尤其针对过度暴露于当代生活底下的“新女性”。[2]这种分道扬镳的治疗法令我们想起霍尔“男女教诲分途”的方法。
\r\r神经衰弱的男性病患者纵使可免于“女性化”之讥,却不能免除与阳痿、早泄、遗精、性无能乃至同性恋扯上关系的遐想,虽然性方面的神经衰弱症状只是这个无所不包的病症的一个特例。神经衰弱病患者对来自体外和体内的刺激都束手无策,噪声、人群、动作,乃至景象变革都会滋扰到他。来自他内部的滋扰则是焦虑、健忘、把稳力不集中,以及无法掌握的性欲。他既然无力战胜外在环境,因此办理性欲的办法便是过度手淫或者和男伙伴搞鸡奸——这类动作,根据当时的医学学理,都是过分消耗神经系统里的有限能源。这种自我耽溺和过早的性发泄对进行成熟的男女性爱皆不利,待到他必须要完成这项成人任务时,纵然能交差,也会涌现兴趣锐减、早泄,或者房事后的疲倦或沮丧。[3]从西方男性空想的角度看,这些征候代表意志薄弱、自我疆界的损失。在当时,曾盛行过度自渎会导致猖獗的不科学的说法,这个恐怖连中国“五四季期”郁达夫的小说里都有反响。[4]
\r\r[1] Gijswijt-Hofstra,“Introduction:Cultures of Neurasthenia from Beard to the First World War”,pp.11,20-21,24.
\r\r[2] Lutz,“Neurasthenia and Fatigue Syndromes:Social Section”,pp.538-539.
\r\r[3] Christopher E.Forth,“Neurasthenia and Manhood in fin-de-siècle France”,in Marijke Gijswijt-Hofsta&Roy Porter eds.,Cultures of Neurasthenia from Beard to the First World War(Amsterdam&NY;Rodopi,2001),p.337.另详见Angus McLaren,The Trials of Masculinity:Policing Sexual Boundaries,1870-1930(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7),p.142;Bederman,Manliness&Civilization,pp.101-102。
\r\r[4] 当时把手淫和神经衰弱联系,彷佛是一种医学知识:“自慰者之身体状态,不但神经衰弱也,且诱起其他诸无名症,如势力缺少,全身弛缓,怯懦逡巡,影象力减少,性能不调,诸事违意,头痛耳鸣眩昏,视力缩短,言语不清,梦魔漏精,生殖不能,莫不因之而起。”详见日本医学士小酒井光次作,孟明译:《人生科学(二):青年与性欲》,载《青年杂志》第1卷第5册(1916年正月号),第2页。
\r\r 7.白色人种的大欲望\r\r在美国,虽然不像某些女权史学家所说神经衰弱是被比尔德特殊用来“指谓男性的性枯竭”[1],但它的确道出了一种危急感。按照19、20世纪之交的文明不雅观,文明程度最高的白种男性按理该最具男子汉气概,他有康健的本能同时加以理性的调节,不像野蛮人或初民一样平常性滥交。在白种男性的眼里,低等民族也像女性一样平常,少能掌握身体和情绪浸染,在个体理性不如白种男性发达的意义上,低等民族徒有蛮力,表现的只是生物的“雄性”(masculinity),而不是高度文明的“男子汉气概”(manliness),的确,在黑人贫民窟里,男人乃至当龟公,让自己的女人去卖淫。
\r\r待到过分文明化的白种男人患上“神经衰弱症”,上陈说法就难于自作掩饰。神经衰弱的男人,性冲动微弱,在“雄性”方面固然比不上黑人,更说不上有“男子汉气概”,事实上形同女子。白种人的这个种族危急,即详细表现在1910年的一次有名国际的拳击赛上:黑人拳师杰克·约翰逊(Jack Johnson,1878—1946)把白人拳王吉姆·杰弗里斯(Jim J.Jeffries,1875—1953)击败,夺得天下重量级冠军头衔。拳击不但靠蛮力,它还讲究演习和策略,因此这场拳赛成为两个种族的男性空想的较劲。白人选手被击败后,引起各地的黑白种族冲突。白人开始不断物色能击败约翰逊的白人拳手,开始了美国拳击史上所谓的“白色欲望时期”(the White Hope Era)。此外,美国在1912年通过一条联邦法,禁止把具有拳击内容的电影运过州界,目的便是不让黑人把白人击倒在地的画面广为流传。有10个州通过新法,禁止不同种族通婚,也是用来对付约翰逊的。约翰逊在胜利后,不但生活招摇,又喜好与白种女子发生性行为,终于被联邦政府用1910年才通过的《曼恩法》(Mann Act)把他定罪。这项法律本来是用来防止贩卖白奴的,约翰逊只与白人女友超越州界发生性行为,如今触犯刑网,是法律被滥用。约翰逊被判入狱一年,弃保潜逃,流亡英、法、墨西哥等地,至1920年才返国服刑。[2]
\r\r这段史实被霍华德·塞克勒(Howard Sackler,1929—1982)搬上百老汇舞台,并于1967年搬上银幕,名曰《白色人种的大欲望》(The Great White Hope)。故事把历史人物的名字改了,说有一名叫杰克·杰斐逊(Jack Jefferson)的拳师,是第一个得到重量级冠军的美国黑人。《白色人种的大欲望》第一幕第三场是在赌城雷诺(Reno)的拳击赛场外,到结尾处,杰斐逊已经得胜,黑人群众在欢呼鼓舞。在此刻,编剧安排台上的灯光熄灭,然后让一根火柴光划破阴郁,原来是外号“丹船长”(Cap’n Dan)的白人裁判点燃雪茄。论职责,他该坚持赛局公道,但在剧本开头处,正是他游说刚退休的白人间界重量级冠军再度出山,以抵制杰斐逊。在雪茄燃亮后,接着便是道出“白色大愿”的那段独白:
\r\r我真切地感到
\r\r这是旧金山大地震以来
\r\r降临这个国家的最大灾害——我是当真的。
\r\r前者大不了只限于弗里斯科(Frisco)。
\r\r是若何的灾害呢?很难说得准。
\r\r啊,我不认为所有的黑鬼会癫狂,
\r\r考试测验对我们进行吸收、强奸一类的。
\r\r是的,是会有那么一点麻烦,但总能搪塞得了——
\r\r归根到底,他们中只有一个是重量级冠军……
\r\r但我想,这正是症结所在。是他!
我还把他的手高举,
忽然间一个黑鬼是天下冠军!
如今你会说:啊!
这只是汝等运动里的一个头衔——
非也,它不仅如此。认了吧。它远胜于一个人成为
\r\r世上最好的工程师,最聪明的政客,
\r\r或首席歌剧演唱家,或者世上最大的
\r\r制造花生产品的天才。这不构成灾害。
\r\r但天下重量级冠军,就非同小可了,
\r\r令人感到天下彷佛罩上了一层阴影。
\r\r统统都变得更黑——这里并无挖苦之意——
\r\r也有今是昨非之叹,彷佛事物在萎缩,统统
\r\r都像被胡乱堆压,连你也在内,你只想狂喊
\r\r他为何高高在上,
\r\r但你喊不出,由于你知道……阴影重重地压着你,
\r\r而你则觉得到那个笑颜……
\r\r好啊!
我们该做什么!
把尿撒在裤裆里,把泪流到啤酒里?
\r\r不,师长西席,我见告你我们将做什么,
\r\r我们击打草丛物色另一个白色欲望,
\r\r如果他弗成我们再找另一个白色欲望,
\r\r我们会找到他们,高举他们直到个中一个站得住——
\r\r这是哪门子的国家,是埃塞俄比亚不成?[3]
\r\r《白色人种的大欲望》揭橥于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时期,重点在反对种族主义,而且把“约翰逊”改为“杰斐逊”,因此无须琐屑较量于一些“不太方便”的历史事实。[4]令我们感兴趣的是这个“黑祸”的性子:“它远胜于一个人成为世上最好的工程师,最聪明的政客,首席歌剧演唱家,或者世上最大的制造花生产品的天才。这不构成灾害。但天下重量级冠军,就非同小可了……彷佛事物在萎缩,统统都像被胡乱堆压……”显然,其性子迥异于来自勤奋努力的亚裔之竞争。[5]
\r\r在约翰逊对杰弗里斯的那场划时期的拳击赛后两年,即1912年,《人猿泰山》(Tarzan of the Apes)这部小说揭橥,它是美国大众文学领域里“泰山小说”系列之始。这是一个白人在黑人的故乡——非洲——成为丛林之王的故事。这个系列的小说和电影在美国的大众心里制造了一个颇为奇特的效果。美国人一样平常对非洲缺少基本的认识。从前的天下史教科书谈到非洲部分都只描述白人如何开拓这个“阴郁大陆”,乃至连一个原住民的名字都不提。在今日“后殖民主义”时期,关于非洲的叙事都必须包括一些当地人物,但由于美国人对天下知识的普遍贫乏,因此无知不减于前。每次我上天下史课讲到非洲部分时,都会对班上说:“谈到非洲,你们大概只知道一个名字,便是泰山。他与其说是和非洲有关,不如说是白色人种的大欲望更来得恰当!
”
泰山的作者埃德加·赖斯·勃鲁士(Edgar Rice Burroughs,1875—1950)的发展期间也在19、20世纪之交。他成长在芝加哥,是大都会的产物,但和当时的许多精英分子一样平常受过“原野化”洗礼。他受野性呼声号召倒并非由于神经衰弱的缘故,而是由于另一种疾病。在1891年,芝加哥爆发盛行性感冒,去世者数百,勃鲁士的父母害怕15岁的儿子被传染,把他送往两位长兄在爱达荷州的牧牛场。勃鲁士到了边陲后,如鱼得水,不但娴熟牧牛,也学会骑拱背跳跃的野马之技能,乃至结交了盗贼和杀人犯,父母获悉,将他转到东部就学。勃鲁士因桀骜不驯之故,改转入军校,毕业后被派在第七合众国骑兵师,亦即阵亡的卡斯特将军的老部队。他的任务仍旧是扫荡印第安人的残余,但根据他的自身说法,“永久追不上他们”。他因心脏问题而升迁军官无望,于1897年退役,转向文职并成家立室。至1911年,勃鲁士感到坐办公室的职务没有出息,遂开始写作,投稿给低廉小说杂志(pulp f iction magazines)。他的第一部小说是有关火星历险的科幻小说,相称受欢迎,因此紧接着在1912年揭橥《人猿泰山》。[6]
\r\r勃鲁士的“火星历险系列”把西部牛仔抱负搬上了火星,它讲的是一名南军军官在火星上的“红人”之间历险的故事,火星别号赤色星球,因此是把印第安人科幻小说化。他的“泰山系列”则反响白人对黑人的抱负。这从“泰山”一名中看出端倪,这是领养他的那个猿猴族为其起的名字,在它们的措辞里是“白皮肤”的意思。[7]照道理说,皮肤的黑白与否,不该是人兽两个物种之间最显著的差异,倒是判别黑人与白人的紧张标准。泰山的故事在今日已引起黑人的反感,这紧张是好莱坞把故事和人物大略化处理的缘故。勃鲁士的原著实在透露了对黑人的倾慕。[8]幼年的泰山生活在猿猴之间,充满自卑感,他嘴巴太小,鼻子太窄,眼睛颜色太浅,身材太矮小,身体无毛令他觉得到自己像条蛇。但小说很快就透露他有过人的狡猾,这表现在第五章中他单独面对捕食的母狮存活下来而同行的小猿则丧生这一点上。由于他是人类,“他较高的智力令他有更敏捷的心智活动,乃超出猿猴的能力以外者”[9]。这和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里家犬回物化然后反而成为狼群之首异曲同工。
\r\r泰山小说常被理解为白人种族主义的作品——它用欧洲和非洲分别代表“文”与“野”、帝国主义与殖民地。[10]这个大略化的教条式不雅观点忽略了19、20世纪之交的思想背景:文明在智力方面固然占上风,但野性代表生命力,在当时西方“文明没落论”的话语里,“野性”实在是白色人种的一种渴望。在这个意义上,勃鲁士也是当代文明的批驳者。在“火星历险系列”的第二部、揭橥于1912年的《火星众神》(The Gods of Mars)里,有一段话是关于火星上的黑人,他们在肤色上有异于该天下的红人和白人,却是该星球最古老的种族,他们的传承可以直接追溯到“生命之树”。这棵树进化了无数世代,末了涌现还没能分开树干的小植物人,从小植物人的蕾苞里演化出四个分格,第一格是植物人,第二格是十六脚虫,第三格是白猿的开山祖师,第四格是原始的黑人。除了第一格之外,其他的都分开树干掉落地上。黑人最早破格而出,是星球上繁殖的第一人类,血统也最纯洁,其他种族则是十六脚虫、白猿和某些离族的黑人杂交的结果。至于在故事里涌现的白色恶魔(the therns),并不是古代白猿的直裔,而是由他们演化而成,“他们的等级更低”。[11]在这里,我们嗅到了杂种化和人种退化论的气味。黑人的传承与“生命之树”最密切,血统也最纯洁,透露的又是什么讯息?
\r\r此时,美国黑人的“哈林文艺复兴”(The Harlem Renaissance)正在酝酿中,其背景是始自20世纪初期的黑人涌往北美城市的大移民潮(The Great Migration),造成黑人城市人口的集中。这个当代主义征象是美国黑人的文艺才华首次集中表现,并由此建立种族的骄傲。“哈林文艺复兴”的领导人原初的构想仍旧是西化的,其构想是让黑人也发展出欧洲式精英文化,是日然是黑人在白人面前自卑感的表现。但这场黑人文艺复兴倒过分来让白人拜倒在黑人脚下,由于它后来走上肯定自身民间文化的道路:如黑人灵歌、蓝调、繁音拍子,尤其是爵士音乐。后者最主要的一个源头是新奥尔良,它是法裔和西裔集中的地方,又靠近加勒比海的黑人文化,因此老早就在清教徒美海内部打开一个“异教”缺口,这个地域性文化进军至芝加哥和纽约往后,就开始发挥全国乃至环球性的影响。[12]黑人的音乐用的是欧洲古典音乐的乐器,但表现的精神全然不同,它在白人压抑的清教文化里贯注入一层浓郁的“酒神型”成分,亦即原始活力,成为美国开国以来首项原创的艺术形态。说今日的美国音乐紧张是黑人音乐,一点都不夸年夜,而这种音乐则以“美国音乐”之名风靡环球。
\r\r[1] Bederman,Manliness&Civilization,pp.87-88.
\r\r[2] “Johnson,Jack(31 Mar,1878-10 June,1946)”,in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ed.,American National Biography(New York&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83-85.另详见Bederman,Manliness&Civilization,pp.1-4,41-42。
\r\r[3] Howard Sackler,The Great White Hope(New York:A Bantam Book,1968),pp.41-42.“弗里斯科”的典故来自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1922—1969)的《在路上》(On the Road,1957),实在旧金山的人并没有用这样的简称。
\r\r[4] 剧本里杰斐逊对他的白人女友温顺谅解,但历史上的约翰逊则有浩瀚白人女友,他除了视她们为私产之外,还常凌虐她们,导致他第一任妻子自尽。在触犯贩卖白奴法后,他的女伴谢绝做证,而且和他结婚,因此罪名不能成立。后来是其余一名饱受虐待的前女友出来做证,政府重新起诉,才把他定罪。剧本把这些史实都省略,只描写他的爱人爱莉(Ellie)追随他在国外到处流亡。在故事里,杰斐逊被迫亡命国外后,拳赛圈里的白人势力和联邦政府的要员提出一个建议:如果他在一场安排的拳赛中乐意输给白人拳手的话,三年的徒刑可改成一年,而他只需服刑半年就可出监。而剧本末了一幕是哈瓦那的那场拳赛,杰斐逊乐意躺倒,把锦标让给白人。故意输掉乃根据约翰逊自己的说法,但说服力并不强。事实上,哈瓦那那场拳赛发生在1915年,而约翰逊在1920年才回美国服刑,而他肯这样做是由于在墨西哥待不下去。
\r\r[5] 梁启超在1899年如此描述在西方人眼里的黄祸:“今夫日本之民族,视中国仅什一耳……而近年以来,犹以工艺雄于万国,每岁手作之物,售至美国者,且值百千万。西方诸国,糜不之畏之,而况于阗繁朴悫之中国乎。彼美人之苛逐华民也,固彼中巨室所大不欲,而无如其力不敷以胜细民也。彼细民之嫉我也,盖亦由忌我畏我,而无术以制我。故宁冒天下之不韪,而悍然出于此途。我亦必有使人可忌可畏之道,昭昭然也。”见《论中国之将强》,载《饮冰室文集之一》,第14—15页,《饮冰室合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r\r[6] “Edgar Rice Burroughs,Creator of Tarzan:Official Biography”,Edgar Rice Burroughs Inc.,www.tarzan.org,pp.1-3.他在美西战役期间还申请加入老罗斯福的义勇骑兵队(the Rough Riders),但遭谢绝,详见Eric Cheyfitz,The Poetics of Imperialism:Translation and Colonization from The Tempest to Tarzan(New York and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4。
\r\r[7] “Chapter 5—The White Ape”,of Tarzan of the Apes,www.literature.org/authors/burroughs-edgar-rice/tarzan-of-the-apes/chapter-05.html,p.1.
\r\r[8] 白种人把自己想象成非洲的“丛林之王”,是否可以大略地责之为“种族主义”?这个态度无疑是“政治上精确”过了头。这好比把《杀去世比尔》(Kill Bill,2003,2004)里一名白种女子凭日本的剑道击垮了全体日本的黑帮,并在末了的对决中手刃日本黑道女魔头责为“种族主义”一样平常。它表达的实在是西方人对东方武术的欣羡,以及在这门东方技艺中也能压倒原创者之好胜生理。这个对东方的认可比对黑人的欣羡晚了很多,背景也不太相同。《杀去世比尔》里的武打场面是导演塔伦蒂诺(Quentin Tarantino,1963—)对战后的日本和20世纪70年代喷鼻香港武打片的致敬,故事的讯息却是百分之百当代美国女性的“杀夫与杀父”:女人如何摆脱介于父亲和丈夫之间的男性之宰制,遭到他的报复,成为受害者,后来又与他争夺女儿的监护权,末了双方比拼技艺,技高一筹的女方把妖魔化的男方干掉,与小女孩团圆,组成目前美国盛行的单亲家庭。这部电影如果不是在女权主义“总路线”上头“政治上百分之百精确”,是否也会被扣上“种族主义”罪名?
\r\r[9] “Chapter 5—The White Ape”,of Tarzan of the Apes,p.4.
\r\r[10] 患这类“公式化”毛病者一样平常是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的著作,它们不太理会详细历史背景,而方向从一个现成的理论公式入手,如前面引用的Eric Cheyfitz,The Poetics of Imperialism:Translation and Colonization from The Tempest to Tarzan即其一例。
\r\r[11] “Chapter 7—A Fair Goddess”,of The Gods of Mars,www.literature.org/authors/burroughs-edgar-rice/the-gods-of-mars/chapter-07.html,pp.8-9.
\r\r[12] Nathan Irvin Huggins,Harlem Renaissanc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哈林文艺复兴”正式开始的日期是1919年,但新奥尔良的酝酿早已发生。
\r\r 结论\r\r如迎合今日美国的族群政治和性别政治,本文的结论该很大略:它论证白色帝国主义如何歧视有色人种,而种族歧视又与性别歧视盘根错节、息息相关,那便是白种男性对自身“女性化”的忧虑,亦即恐怖男性之性别认同的损失。本章并不否定这类结论,但嫌其过于大略化。在本章稽核的时期——19、20世纪之交的帝国主义时期——“黄祸”和“黑祸”的差异还不显彰,当时的顾虑还是集体式的,乃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乃至人种与人种之间的对垒,但已从一些蛛丝马迹可看出两者之不同。循至20世纪上半期,美国思想越来越方向从个人化角度考虑问题,就将其差异凸显出来了。参考已揭橥的有关较近期美国人对东亚人尤其是中国人的想象[1],即可辨认黑人和东亚人士在美国白民气中形成颇为不同的生理沉淀层。纵然作为对雄浑性之追求的一体两面,黑人是白人这个欲望的妒羡工具,而黄色人种则常常勾起“女性化”和“性无能”的遐想和恐怖。
\r\r[1] Lung-kee Sun,“Without Sex and Violence:The‘UnAmerican’Personality”,New Perspectives:A Comparative Literature Yearbook,vol.2(1996),pp.1-69.以及收入《历史学家的经线——历史生理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和花千树版)的两篇论文:《缺少“性”与“暴力”:非美国式的人格》《飞蛾的沉默:美国大众文化中的“第三性”与东方人》。
\r\r\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