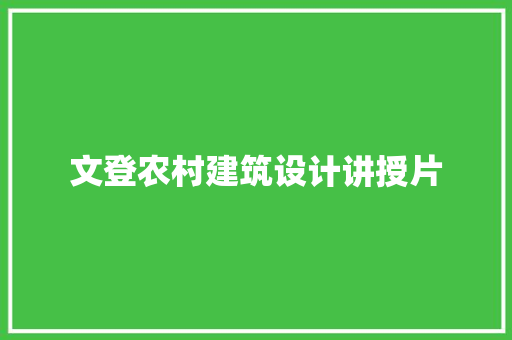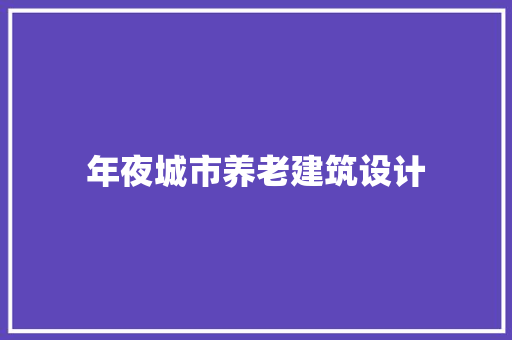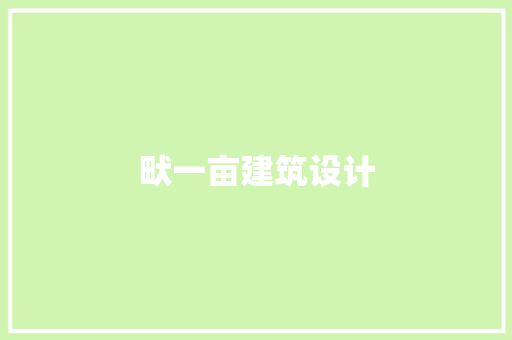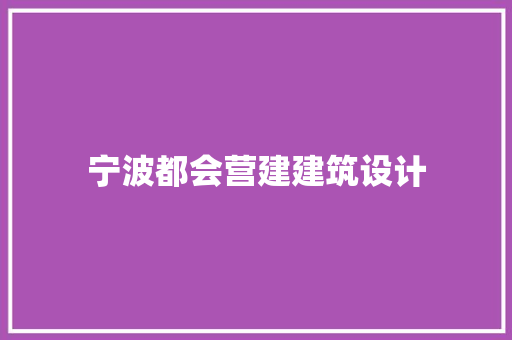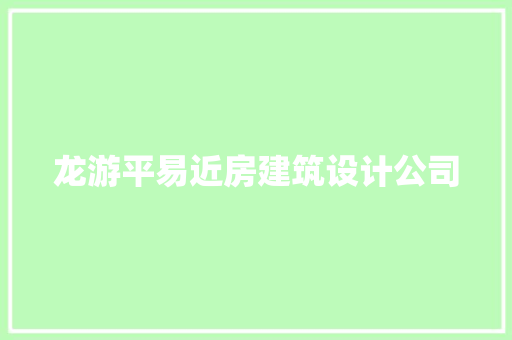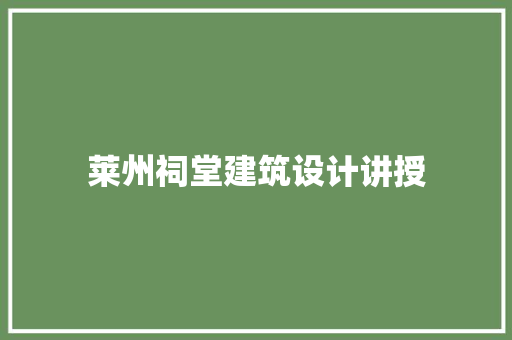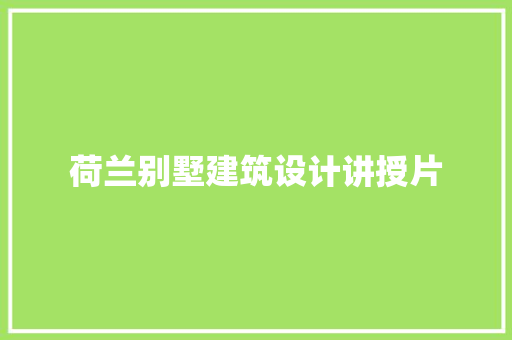沙田村落地处石岐河东,北倚梅岭,因长期河海冲刷,明代淤积成沙滩,形成肥沃的小平原。清顺治元年(1644年),林姓人从隆都安堂(今属大涌镇)迁此建村落,因田地多为沙质土,故名沙田村落。
作为侨村落庄落,沙田村落也有许多清末至民国期间的侨房和碉楼,而侨房和碉楼被称为岭南建筑文化中的一朵奇葩。

侨房楼顶的山花和女儿墙,上面多有西方建筑图案或培植年份(有的还标注着承建商的店铺),一些窗楣还悬挂有西式的风景画,骑楼有支撑柱装饰(有的是简朴的方形立柱,有的是典雅的希腊式柱)。
要说村落里的标志性建筑,非村落经联社对面的圆形碉楼莫属了。听说这是南区最具特色的一座碉楼,楼高四层,每层均设有花岗岩石砌成枪眼,顶层设晒台瞭望台。
据村落干部先容,圆形碉楼建于民国初年,原来有两座,两座碉楼之间还隔着风水池塘,它们矗立在村落边,尤如一对门神,十分霸气。可惜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村落民把个中一座圆形碉楼拆除了。
虽说沙田村落并非明朝在珠三角地区实施屯田政策后围垦的“沙田区”,但我还是借此机会,和大家分享一个跟沙田围垦有关的小故事。
古代进行沙田围垦是一项有较大风险的投资,须要有充足的劳动力、成本和权力关系,故围垦沙田的多是地方上势力雄厚的宗族、乡绅。
在喷鼻香山县不断浮生的沙田区,村落建立较迟,自明代始,番禺、南海、新会、顺德等各县豪强都在此占耕,随田寄籍于此。个中,以顺德地主最多,故从清代起,就有“喷鼻香山田、顺德契”的说法。
沙田区的地主每年向沙田的佃户除了收田租以外 , 还有一项颇为特殊的剥削形式 :收“沙骨”。原来,割禾后总有谷粒遗落在田里,如果在田里放养鸭子,就会很快终年夜(吃这些谷粒终年夜的鸭子称“早禾鸭 ”)。
地主认为,田地是他们的,谁假如放鸭下田吃余谷,就要其余纳钱。清光绪年间, 地主阶级以此为“情由”上呈清政府,要求收放鸭钱并得到批准,这种钱就叫“沙骨”。
自此每年都要开投“沙骨”,即由一些豪绅富商承包,然后分围分段给经纪贩子或富农分包下来,谁要放鸭下田吃谷,都要付钱。
在珠江三角洲发育和开拓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沙田一民田 ”的空间格局 , 实际是一种表示在资源掌握上的政治权力和文化认同的格局。虽然这不是这次拜访沙田村落的调研内容,但也不失落为一个值得磋商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