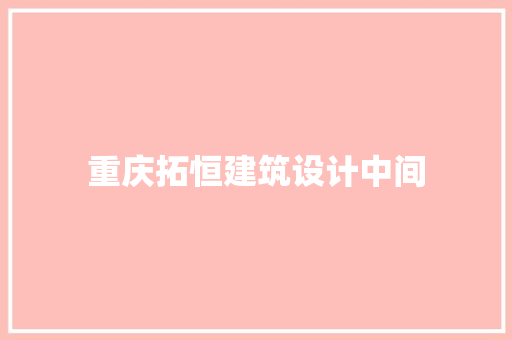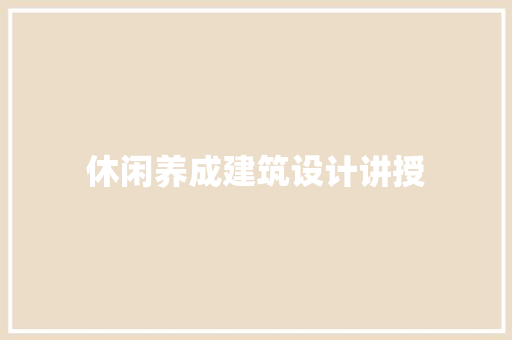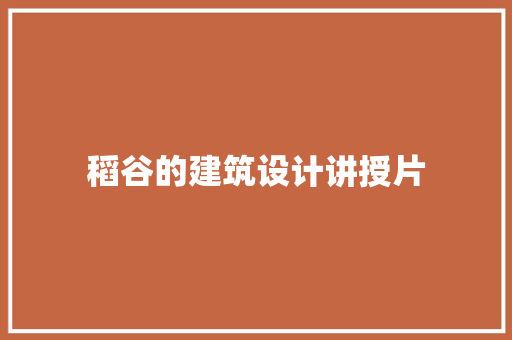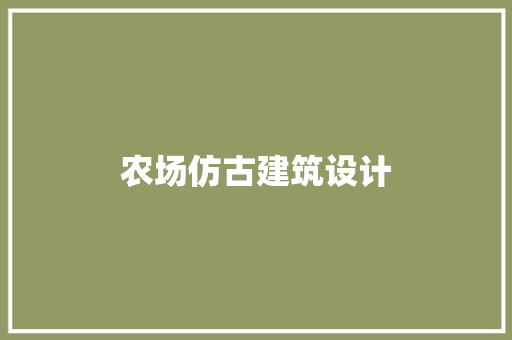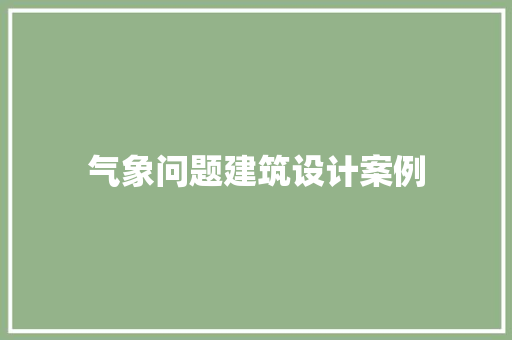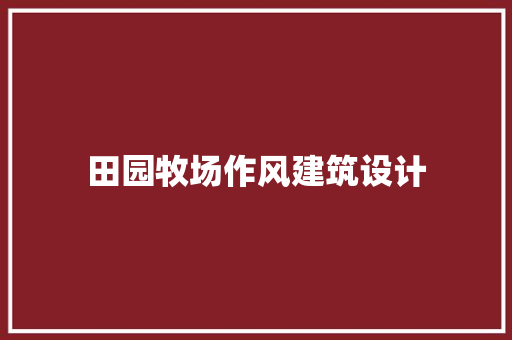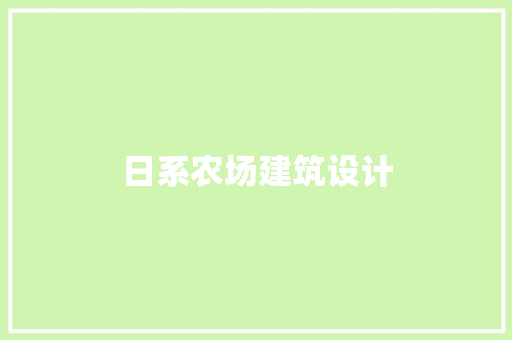从1950年到1966年,按任职韶光顺序,先后有孙桂儒、顾云如、金汉章、颜景詹担当农场党委布告;有刘锡九、汤承裕、周德之、郭士金担当场长;副职领导有陈柏年、陶鼎来、薛华甫、封士清、周殿甫、周新、阚庆友、曲正礼、管纯等。 “喝水不忘掘井人”,在庆祝农场建场七十周年之际,回顾为建场做出精彩贡献的老领导,有利于我们发扬传统,珍惜当下,不忘初心,再创辉煌。
战功卓著的老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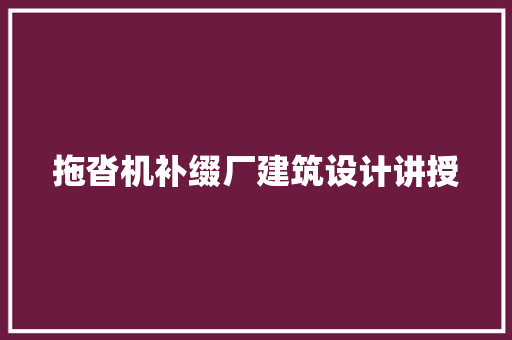
建场初期,农场领导除陶鼎来是知识分子干部以外,别的均属老革命:刘锡九时任淮阴地区副专员兼农场场长,薛华甫时任副场长,而他早在1940年,就担当涟水县抗日民主政府第一任县长;周德之1938年参加革命,是淮海地区赫赫有名的抗日英雄。解放后,他先后担当过淮阴地区重工业局、农业机器局局长等职,1953年8月亲率军队,组建五图河农场(现连云港监狱);1963年3月任东辛农场场长;金汉章在战役期间担当过八路军三师敌工部部长,海、灌、连、沭地区军事部长,新海连工委布告,来场前是灌云县副县长;颜景詹在战役期间担当过淮安县武工队队长等职,曾参加过欢迎党中心迁往淮阴的前期准备事情,解放后担当过中共溧阳县委布告等职;汤承裕来场前是灌云县县长,郭士金以前担当过八路军团长,顾云如来场前是原农建四师的团副政委,管纯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他却是1938年就参加革命的“红小鬼”。这些在战役年代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的元勋们,解放后,为了建好国营农场,他们放弃在城市的优胜生活,当仁不让来到我们这个苏北“北大荒”,马一直蹄带领全场职工,踏上培植机器化农场的艰辛进程。
困难困苦的新征程
对付这些刚刚从硝烟弥漫的沙场,转业到农业战线事情的老革命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新的战役,新的征程。当时的东辛农场,只是一片附近大海的盐碱地和荒草滩,“春季白茫茫,夏季水汪汪,洼地长芦苇,处处是盐霜”,喝的是盐碱水,住的是泥巴房。要在这个华东地区率先培植的农场,点亮金色的希望,路途迢遥,困难无比。
种好防风林
建场初期,历届农场领导都把开拓荒地,农田培植,管理盐碱,粮棉增产四件大事,当作各项事情的重头戏,从1950年3月开荒第一犁开始,到1963年底,全场共开垦出荒地12.86万亩。
为发挥机器化上风,根据苏联履历,结合农场实际,场领导和技能职员在开好的荒地上,设计方案出几十块条田以及与之配套的沟、渠、林、路,每块条田长2000米(后改为最长900米),宽100米(后改为不超过45米),中间隔300米建一条防风林带,至六十年代中期,全场先后营造了52条、总长80公里的防护林带,对战胜风害对农作物的影响,发挥了主要浸染。
场领导在地头作动员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为办理农田排灌须要和改造盐碱地,农场领导下大力气狠抓水利培植,到1965年,农场先后靠人工开挖了东干河、中干河、西干河、小盐河,南北向干河4条,东西向支河38条,完成土方931·91万方,如果将这些泥土,按一立方米体积连接起来,长度可达9310公里,相称于我国黑河到三亚的来回里程。随着这些工程的相继竣工,初步完成了场内农田排灌系统培植,达到“百日无雨保灌溉,日雨150㎜不成灾”。
那时,大面积的盐碱地,严重制约了农业生产,场领导和技能职员反复研究,利用纵横交错、密如蛛网的沟河,采纳科学灌溉方法,逐年用雨水冲走土壤中的盐碱;从福建引进天菁、苕子籽种,在全场推广栽种,既大大减少了土壤里的盐碱,又增加了土壤有机质,使农作物产量逐年提高,后来,这个履历还迅速推广到华北和西北干系地区,农场也一度成为全国绿肥籽种的主要生产供应基地。
丰收的喜悦
1958年,时任场长汤承裕,为了进一步扩大农场生产规模,有效办理与周边州里的各种轇轕,经由周密论证,专门向省政府呈上报告,将农场周边东滩乡的八个高等农业互助社并入农场(简称场社合并),使农场面积一下子扩大到200多平方公里,耕地面积达到14万亩。这一重大举措,瞬间从体量上解除了农场经济发展的瓶颈,对农场后来发展规模经济、优化布局,打下主要根本,回眸农场七十年来的发展进程,当初场领导这一高瞻远瞩的决策,对付东辛农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那是具有何等主要的计策意义啊!
对付当年的这些老革命来说,从拿枪杆到握锄柄,这无疑是一个全新课题。为了尽快熟习业务,做一个称职的农场领导,薛华甫潜心学习研究农业生产技能,从垦植制度、栽培技能、田间施肥、植物保护、良种繁育到土壤改良,几年之间,就写下了十多本条记。这些条记记录了他刻苦学习的困难进程、充分反响了他与时俱进的拼搏精神,他坚持“从战役中学习战役”,在短韶光内,就使自己从一个精良的军事指挥员,到成熟的农场培植领导者,实现了华美的转身。
心系群众确当家人
这些来自战役年代的领导,深知兵民是胜利之本以及联系群众、依赖群众的主要性。以是,他们的共同特点,便是时候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处处想着群众,设身处地为群众办理各种困难。
建场的第一年,农场领导一边建场,一边提着粮袋给群众发放救援粮,党委布告顾云如,那时他本身就得了“浮肿”病,却仍旧坚持拖着怠倦的身驱,给困难职工送救援粮。在那非常困难的建场初期,他们也和职工一样,节衣缩食,吃的是粗粮、盐蒿窝窝头,住的是茅草棚。
身兼农场场长的淮阴专署副专员刘锡九来场理解到这一情形后,深情地对副场长陶鼎来说:一定要千方百计改进职工生活,由于培植机器化农场,是一项伟大的奇迹,要干好这个奇迹,人才是关键,以是一定要以建好农场这个大局为重,只有想办法把生活搞好,才能留住人材,完成培植国营农场的光荣任务。自此,农场领导有了“尚方宝剑”,职工生活有了大幅改进,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农场培植兴起,也对周围州里群众产生了很大吸引力,纷纭报名来农场事情。
副场长薛华甫分工卖力农场基建和后勤事情,他不顾多病的身体,常年带领职工建食堂、建宿舍、建机库,到1960年,农场从原来只有三间草房办公室,逐步建了职工住房、食堂、车库、仓库、油库、澡堂、办公室、粮棉油加工厂、中小学;成立畜牧场,发展养殖业,成立林艺队,栽种果树苗木,初步知足了职工生产和生活方面须要。特殊是率先在苏北地区,参照苏联一级大修厂标准,建起一座拖沓机修理厂厂房,为提高农机化水平,供应了主要保障。
建场初期,农场人喝的都是又苦又涩的咸水,场领导当即决定在场部,人工挖出一个面积很大的水塘,夏天网络雨水,冬天网络雪块,努力改进饮水质量。对住在边远单位的职工,则定期用拖沓机拉着水箱,把水塘里的水送到那里。对中午在远处作业,不能回食堂就餐的工人,则让炊事员挑着担子,将饭菜送到地头。
农场领导每次莅临盆队检讨事情,晴天骑自行车,碰着雨天道路泥泞,只有步辇儿前往,到了中午用餐,则是走到哪里,就和那里的工人一样,吃用盐蒿种子做的窝窝头和胡萝卜稀饭。
三年自然磨难期间,农场也和全国一样,很多职工因饥饿涌现浮肿病,党委布告金汉章联络党委一班人,积极组织群众搞好生产自救,制订政策给每个职工,划出一分自留地种胡萝卜,以填补口粮不敷;发动职工开垦拾边地,养鸡养羊,搞好家庭副业;对老弱病残职工,每人每月发给一斤糖,一斤鸡蛋;有条件生产队,每月拿出一些大豆磨豆桨供应病号,使得全场在三年自然磨难期间,没饿去世一个人。
困难期间,薛华甫家里人也是吃得高粱、地瓜干、胡萝卜、盐蒿种,个别病灾户到他家反响灾情,他就用自己的人为和粮票帮助他们,他的家属有时难免抱怨,他却说:“钱是公民币,来自公民,再交到公民手里,才能心安理得”。
在平时事情中,场领导和工人们打成一片,和工人们吃在一起,干在一起,副场长周殿甫民平易近,事情中吃苦在前,享乐在后,被大家誉为“老黄牛”。
建场第二年,国家特地给农场分配了23位大学生,要知道当年一个县,每年能分到二三个大学生,就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了,可见当时国家对农场培植是何等的重视。这些知识分子的到来,对加速农场培植,发挥了不可缺失落的浸染,场领导对这些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培养,事情上放手,生活上关心,先后发展多人加入党组织,及时把他们放到主要岗位历练,很多人后来因事情须要,调出农场到更关键的岗位,成为全国农业战线方面的中坚骨干。一对大学生夫妻结婚,由于他们的父母不能来参加婚礼,场长汤承裕便亲自担当婚礼主持人,代表他们双方家长,对他们表示激情亲切祝贺并提出殷切希望,几十年后,这对夫妻回顾起来仍感激不已。
勤政廉明的好品质
建场初期的农场各届领导,大家都保持着在战役年代形成的清廉作风,1955年之前,场领导和技能职员实施供给制,人为以大米或小米为打算单位,后来实施人为制,场领导和技工的人为相差无几。大家一起吃食堂,一起喝咸水,一起住草棚,一起干农活,干群关系十分融洽。
建场初期,场领导对国家投资利用处处一个钱打二十四个结,在用度开支方面舍不得多花一分钱,齐心专心想把钱用在农场培植的刀刃上。副场长陈柏年身体不好,老花眼也很严重,为不延误事情,急需配一副老花镜,但当时买一副老花镜要九万元(合现在九元),这对付他那点微薄的人为来说,是一笔很大开支,不得已只好打报告向淮阴专署申助,专署为此事专门研究,特地发文批准,他这才如愿戴上老花镜。至今回顾起这件小事来,仍让人感叹不已,这份专署的批复,现在仍旧保存在农场档案室,当我看到这张泛黄的薄纸后,总以为心里有一种模糊作疼的苦涩之感。
五十年代,农场只有一台“吉斯”牌轿车,但却很少动用,运输紧张依赖骡马车,副场长薛华甫到灌云开会,险些每次都是用马车把他送到南城,然后再乘公共汽车去县城,有一次车队主动派车到新浦接他回场,却被他狠狠批评了一顿。他的儿子有一次偷乘农场车队汽车去新浦玩,违反了他一贯交待的“不准占公家便宜”哀求,回来后便被他训斥了一顿,并令其写出担保书,担保今后不再重犯。
这些农场的老领导,当年来场时大多属于县处级干部,但他们始终保持艰巨朴素以身作则的本色,场长周德之当时是15级国家干部,到农场后,每天凌晨都要背着粪筐外出拾粪,边拾粪边查看农作物成长情形,回家前再把粪倒在农场大田里,职工们看到后十分惊奇,都称他是“拾大粪场长”,他却笑笑说:“拾粪一可以积肥、二可以靠近群众理解情形,三可以查看庄稼,这是一举多得的好事!
”
结 语
光阴荏苒,岁月如歌,七十年过去,农场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变革,在欢庆胜利之时,回顾为农场初期培植做出巨大贡献的老领导,他们忘我事情的奉献精神,艰巨朴素的事情作风,心系群众的动听业绩,勤政廉明的高尚风致,让我们久久难以忘怀,永久值得我们东辛公民世代景仰;他们存心血、乃至用生命,谱写出东辛残酷的创业史,给我们供应了浩瀚的启迪;光阴如白驹过隙,虽然他们早已作古,但他们留下的浩瀚精神遗产,是我们东辛人的宝贵财富;他们那种冰清玉洁、动听肺腑的风致和操守,炳如日星,光芒永照东辛大地,不断勉励我们奋勇向前。
刊于2020年第二期《东辛文苑》,2020年8月建场七十周年论坛发言用)
六十年代的东辛农场场部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