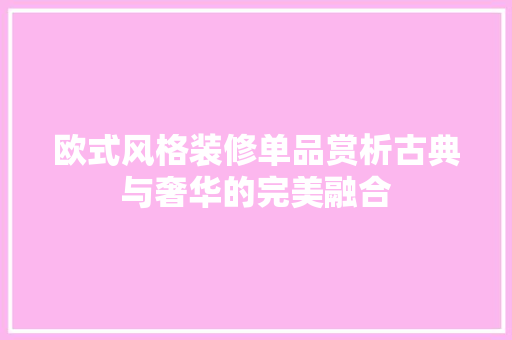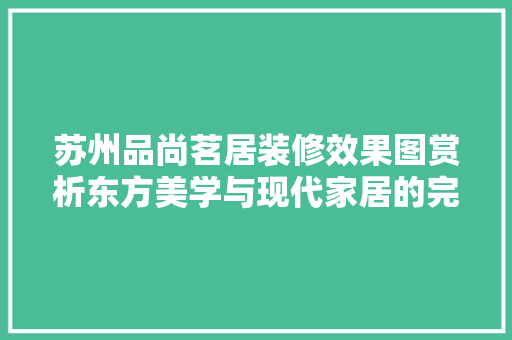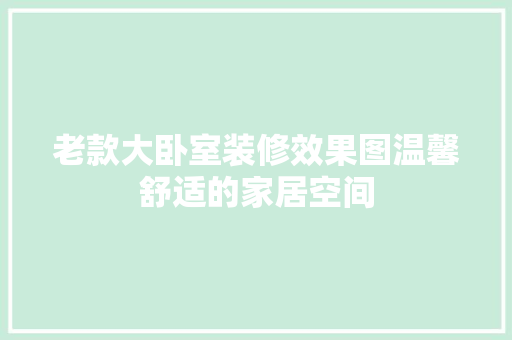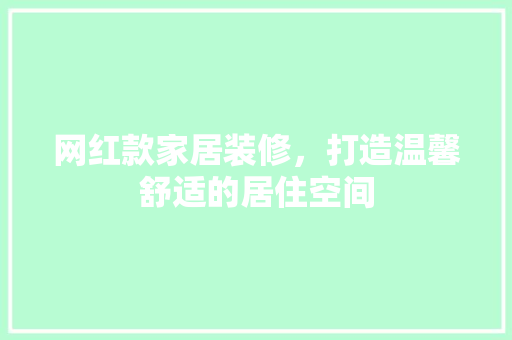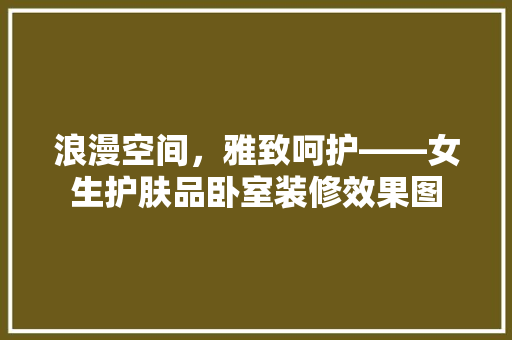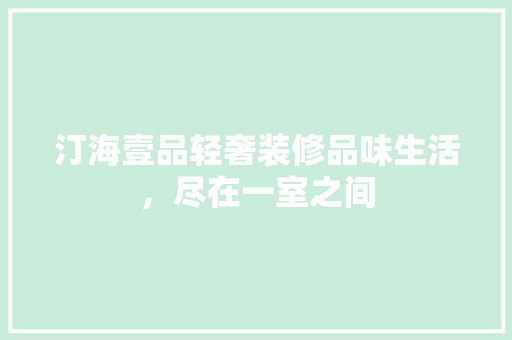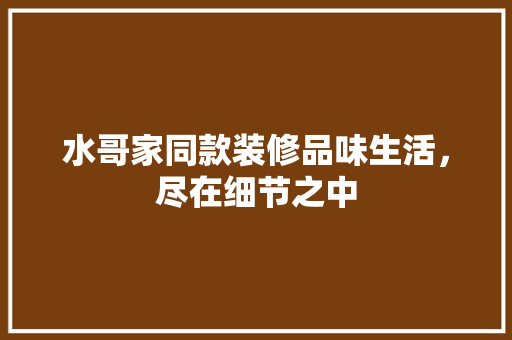疫情后,
85后设计师汪昶行开始在上海各地找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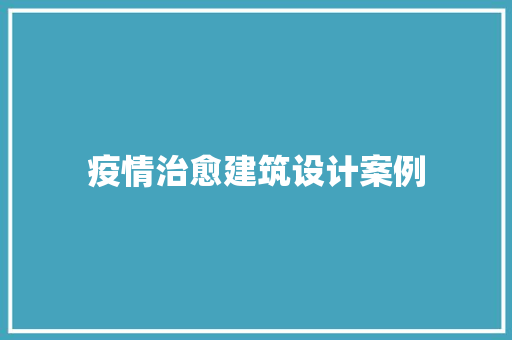
他想造一处空间,专门“独处”,
把自己收藏的物件、喜好的东西放进去,
喝一口安稳的茶。
▲
温润、内敛的独处空间
他租下市中央一栋小而美的老洋楼,
亲手设计、改造,
营造出一个“当代海派”的空间,
有东西方设计元素的碰撞,
整体氛围内敛、温润、舒适。
今年9月,他带着近50件藏品搬了进去,
平时太太也爱来这“做客”。
11月,一条来到这所海派老洋房探访。
自述:汪昶行
编辑:秦 楚
责编:陈子文
▲
“一见钟情”的老洋房外立面
2020年女儿出生后,家里逐渐变成属于她的空间,我爱收藏各种物件,但在她身高能触碰到的范围内,都不太敢摆放,怕砸了。而办公室事情节奏很快,自己可以逐步地喝茶的状态已经没有了。
我就想,是不是可以有一个既不属于家、又不属于事情室的“第三空间”——可以把我的收藏、喜好的东西放在里面,可以独处,喝一口“安稳的茶”。尤其这次上海春天的疫情,在家待了两个月后,越来越感到须要自己“独处”的空间。
在这样的空间里,一个人待着,看看书、听听音乐,或是和最好的朋友聊会天,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
独处时一个人听听黑胶是汪昶行的日常习气
于是,我开始找屋子。黄浦区、苏州河沿岸、外滩都看过,当时来到这,看到一块非常大的草坪,然后一棵很大的喷鼻香樟树,再涌现这样一栋小而美的上海的老建筑,像你看到一个很喜好的男生或者女生,一眼心动。屋子所在的街道两侧种满了法国梧桐,骑着自行车就能感想熏染到上海的时令变革。
我从小出生在上海石库门,又是室内设计师,以是对海派风格的空间有别样的感情。想在这栋屋子里,营造一个当代海派的空间。
没有犹豫,租下了这栋老屋子,开始全面的整修。随着疫情变革,断断续续地施工改造。今年9月,我带着藏品们搬了进来。
▲
一层开放的空间:会客区域
▲
二层较为私密的空间:吧台区域
当我把这个房屋构造打开之后,才创造这是全木构的屋子,就跟中国传统古建筑一样。
洋房一共156㎡,高下两层,通过老式双跑楼梯连接。
原始空间节奏感比较平淡,一楼没有挑空,二楼是平屋顶。我希望空间上有一些起伏,先压低再放高,通过旋转楼梯把两层串联。
▲
改造后的旋转楼梯带有老上海风情
我们东方的审美是“天圆地方”,很多上海老屋子里面,旋转楼梯都会有一些弧曲面,很优雅。但这个空间如果做一个桶状的楼梯,会有一种很强的压抑感,门一打开,一个楼梯朝你“扑”过来。
为了看上去不那么笨重,我选了镂空的钢构造。而上海很多老屋子里是木构造楼梯,就用玄色橡木包裹楼梯扶手和踏步。末了,有了这座钢构造包木皮的旋转楼梯。
其余,把楼梯位置改到房屋中央,重新分割室内布局。空间形成一个环形的“回字”动线,视线变得开阔,朋友来了以为这里至少有200㎡。
▲
一层空间:大茶台区域、餐厅
▲
二层空间:小茶台区域、书房
通过一个“巧”字来把空间做大。如果用传统建筑来类比的话,这栋屋子原来是三开间两进,改造后变为两进、三开间,在上海老洋房里也可以感想熏染到传统建筑的空间体验。
一层功能相对开放,二层相对私密。正门进来,进来左边是一个大茶台区域,再过去是餐厅,方便和朋友们聚会;随着旋转楼梯上到二楼,会看到吧台、小茶台和书房,多是自己独处。
▲
汪昶行自己家里的设计色彩张扬、繁复
我太太也蛮喜好来这的,她的评价是:这个空间不太像是我设计的。
我之前设计的很多项目,包括我自己家、事情室,相对比样比较浮夸的,然后里面东西多是多得连路也不能走。员工都跟我说,“汪总你可以把公司轻微清理一下了”,现在只有我们公司的猫能在里面走,由于它可以走猫步……
▲
克制的色调、材质让人的视线汇合中在室内藏品上
但这个空间在色调、软装上都比较克制,紧张是黑白红的大色调,利用莱姆石、黑檀木等偏自然系、温润质感的材料。
空间里最“跳”的是两个赤色的钢琴烤漆门,是故宫的朱砂红,夜晚看红里带一点紫调,有点像日落的色调。
地面利用苏州御窑的金砖,随着韶光表面的凹浆会变革,是很美的自然质感。
▲
一层空间地面铺设苏州御窑金砖
▲
较暗的室内空间反衬了室内的艺术品和室外自然环境
我希望这个空间通报出来最主要的觉得便是安静,一下子沉下来,特意把空间做“暗”一些。暗了后,你的视线会往亮的地方去看。透过一些小窗、墙体上的开洞,框出一些景,主角是室内的艺术品,和窗外的自然。
夜晚的时候,通过灯光的设计,包括二楼做了一个壁炉,氛围安静、惬意。
▲
玻璃渐变手工套杯,sghr
我是一个特殊喜好怀旧的人,很多东西我都不会扔掉的,包括朋友圈和微博我也不会删,昨天还在看自己2013年的朋友圈,我以为好傻,但也不删。
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过程比结果更主要。我收藏的这些东西,也是这样。它们都是我的经历和影象,自己收的东西都不会出掉。
从个人就喜好收很多东西,以前没钱就收喷鼻香烟牌子,后来收变形金刚、乔丹鞋,再后面收中古家具。
▲
日式老建筑上的梁拖,祥云图案,木质已分解呈现岁月痕迹
▲
一楼意大利纸艺术家Daniele Papuli用纸头做的花器
中间用一根钢丝串联起来,没有用任何的胶
螺旋形的形体非常具有层次美感
我收藏艺术品,也有12年的韶光了,家里已经堆得满满当当。
这个空间现在有三五十件收藏品,东方的、西方的、老的、新的家具,茶道具、灯具、雕塑、艺术装置,还有我自己设计的桌椅……藏品更多是跟生活干系,一定要拿来用。
荒川尚野,最早是在上海的一个艺廊理解到他做的生活器物,杯子、茶道具、花瓶等,后来逐渐理解到他的装置作品。他对玻璃的利用,我以为是授予玻璃生命了,便开始收藏。
▲
荒川尚野制作的“鱼”玻璃雕塑
一楼壁龛上摆放的这件鱼的动态玻璃装置,是专门请他定做的。我们中国人很喜好鱼,也讨个“年年有余”的口彩。
底座是类似金鱼形状的火山岩石,内部是机器构造,旋转发条,鱼会摆动起来,既精密又很艺术。
▲
鱼身精密的机器构造
艺术家烧制了无数个大样,前后做了一年多,在烧制过程中,从鱼头到鱼身、鱼尾,须要一气呵成,对穿孔精密度的哀求非常高,艺术家需同时与做铜、做机器构造的匠人相合营。
末了他不才面写了一句do you know if the fish is enjoy,中文便是“子非鱼怎知鱼之乐”,这个故意思、故意境。
二楼小茶台上是艺术家辻和美的玻璃套组杯,她用可回收的玻璃材料,处理后做成大海的深蓝色,在阳光下玲珑剔透。
▲
辻和美的玻璃套组杯
▲
William Morris的中古羊皮纸灯
黑胶唱片机一旁的台灯,是在伦敦的时候收的。艺术家William Morris是Art and Crafts运动(艺术与手工艺运动)的创始人,他的理念便是要将艺术与手工艺相结合。
他算是一个反当代主义的人,希望很多东西要靠自己的双手去创造,这盏台灯便是靠全手工敲打铁做出来的,灯罩的羊皮纸,也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近几年我收藏的东方器物比较多,尤其是海内新兴艺术家的作品。
▲
《木与火》,物木所作品,有机形态的四个山形烛台
表面做玄色大漆处理,山顶贴金箔
▲
《LOOP 2019-1》,高入云作品,艺术家在细线上弹墨
通过黑白、虚实表达水墨山水画的形态
把中国传统山水画用当代手腕表达出来
这幅大漆的画是意外收成,我空暇时喜好跑景德镇找朋友喝茶,通过朋友结识了这位大漆艺术家陈方。她很年轻,也还没太大名气,但当时在事情室第一眼看到这幅画我就很喜好,像看夜晚的大海。
你觉得它很沉着,但大海的波澜是藏在里面的,实在浪很大,你能听到声音,只是你在夜晚只看到一片漆黑。但近看,这幅画又像是树皮的纹路……不主要,对付作品每个人有自己的解读。
我特地配了一个玄色亚克力的框,营造神秘感。晚上一个人看它,配上一杯威士忌,听上交响乐,觉得能真正进入到这幅画里面。
▲
《山水-1》,陈方作品
收中古家具和我去,我也有自己的“小技巧”,太太常笑我,“逛古董店就像女人购买衣服一样”。
我看中一件物品后会一贯在店内徘徊,理解物品的历史与工艺,在老板面前刷存在感,末了和老板“聊”成朋友,顺便在价格方面得到一个小优惠。我很享受与店铺老板谈天的过程,能理解这件物品背后更多的历史与故事。
▲
《凝固的白》,吴靖文作品
▲
壶,荒川尚野
▲
神代杉茶叶罐,川合优
当我心情焦躁或者怠倦的时候,看着从天下各地收回来的东西,想起当时的场景、故事,会被瞬间治愈。它们千里迢迢来到我身边,见证了我不同年事层次、不同阶段的想法。
我的理念是,艺术品的收藏它千万不要随着价格走,一定要随着自己的觉得走。收藏的第一性,是这东西能不能打动你。
不贵的东西,但我很喜好,我也会收。很多茶道具,只几百块钱收来的,但放在我的茶桌上就很搭调。
一个很破的碗,放在一个打好灯光的壁龛中,也会显得“贵”。
很多东西看上去很便宜,但如果搭合营适,就可能改变它的气场,呈现出超过它价格的代价感。
疫情前,我是猖獗的旅游爱好者,至今跑过五十几个国家、三百多个城市。但是当我旅游的次数越多,在国外待的韶光越久,越以为自己国家的文化才须要我们去挖掘。
我在纽约、米兰的餐厅里都创造有很多外国人在喝茶,10桌里至少有8桌都在品茶,他们讲起中国文化乃至是滔滔不绝的,而我在喝咖啡。这让我开始思考,很多时候我们看自己的文化时,以为是天经地义,就像我生活在上海,一次也没去过东方明珠,反而想去看巴黎铁塔。
现在喝茶变成了我生活中不可短缺的一部分。茶没有咖啡来得浓郁,但手上搓杯的时候能闻到杯底留喷鼻香,是一种低调内敛的美。
▲
空隙时汪昶行会在书房写书法
近两年,我觉得自己作为中国人、作为一个上海人,骨子里的基因开始不断地往外“涌”了。
我现在都记得小时候我家住在弄堂什么地方,每天放学回去,一起上从弄堂口走到底,每一家人家的姨妈或叔叔都会跟我打呼唤,作业做完了没?晚饭的时候,你可以走到任何一家人家,去吃个菜。一个弄堂里的孩子会跟隔壁弄堂去玩,玩打弹子,玩拍喷鼻香烟牌子,玩各种各样。
▲
汪昶行镜头下的上海街头景致
包括我的父亲也是一个中国传统山水画的艺术家,小时候看父亲在家里放红木家具,我是很反感的,但现在越来越以为这些元素和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海派文化中有中西碰撞、中西领悟,但这种碰撞和领悟是在比较内敛的状态下进行的,而不像我之前设计自己家时,那种色彩浓郁、很外放的。
以是改造这栋老洋房时,从硬装就开始往退却撤退,更多展露出东方的审美。
▲
疫情期间支配的小阳台
疫情以来,我还创造空间的利用场景是要靠生活出来的。
今年上海疫情不能出门的那几个月,很明显觉得到自己总想坐在阳台上,那是离室外自然最近的地方。我家的阳台很小,但就在小阳台的一个小角落,我能从早上8点一贯坐到日落之后。铺一块老毯子,放一个小的条几,再在上面放一台电脑、一壶茶,几个小抱枕,就可以过一天。
我女儿才两岁半还不太会说话,她也跑到阳台上和我挤在一起,玩她的小车,从来没有人教她,但是她的身体已经“说话”了。
搬进这栋屋子后,原来设计二楼是更个人私密的茶肆,但实际待得更多的地方反而是楼下,它间隔室外草坪更近,更贴近自然。中国人永久是天人合一的思维,人与自然相领悟。
希望这栋老房的设计,再过5年10年看它,也不会以为过期。
本文章为“一条”原创,未经许可不得编削、盗用至任何平台,否则将深究法律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