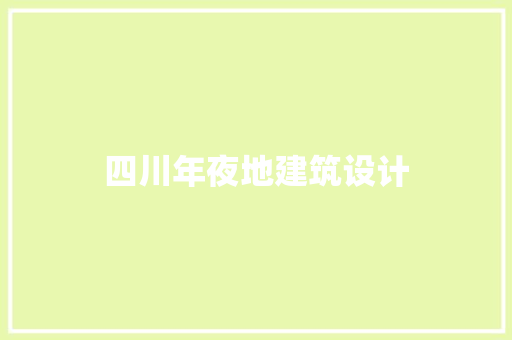徽州文化内容极其深邃、博大、全面,涉及社会经济、教诲学术、文学艺术、工艺美术、建筑雕塑、哲学、医学等诸多领域。尤其在徽州地皮制度、徽州哲学、徽商经营、新安医学、新安理学、新安画派、徽派建筑等自成体系,纷呈于世,无与伦比。特殊是遍及徽州大地近五千个保存无缺的徽州村落成为人文、自然奇不雅观,更是中国独一无二之绝响……各领域产生著名思想家和精良历史人物近千人,当为中华传统文化之精华和范例代表。
独树一帜的徽派建筑作为徽文化的主要载体,承载了古徽州几千年文明史。是古徽州社会历史的政治、经济、地理环境、自然条件、生产办法及生活习气等在物质形态和精神理念上的反响;是在特定的时空文化状态下造就出来的物质实体,它表现出三大性征:实用性、象征性、环境性,并形成特有的徽派建筑哲学理念:人与建筑、建筑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人与人、人与自然最实质、最直接的联系空间。它集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于一体,充分表示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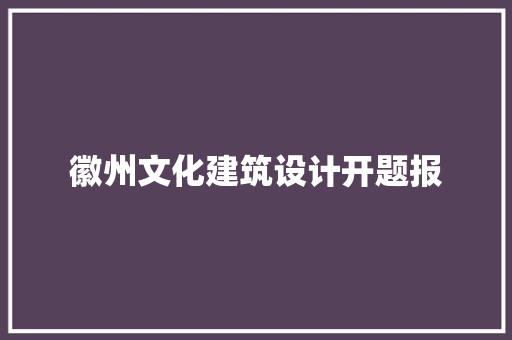
徽派建筑有以下几点详细表征:
1、显山露水。村落镇聚落、民居建筑与自然山水打成一片,相生相安。
2、淡雅简约。建筑色彩——黑、白、灰,建筑元素——点、线、面。建筑空间——外实内虚。
3、亲切宜人。建筑空间以人为本、尺度合适、至理人性、表情丰富、文化溶入。
4、自由伸长。以天井空间为扩散节点,有形无形地变幻着建筑体型构造,适应并充分利用地形。
5、有机整体。与自然大地环境紧密结合,充满一种秩序感、整体感、统一感。表现出合目的性的场所精神。
6、开放兼收。表示在对外来文化原谅和兼收并蓄,包括室外空间的开放性和室内空间的外向性。
这些理念表示在宏村落牛形建筑空间、西递船形构造中及屏山村落山、水交融中;表示在歙县斗山街、唐模水口园林及街巷空间中;表示在休宁万安、五城古镇的环境情态中……不一而举。这些正是我们徽派建筑文化的气韵,也是徽派建筑的特质。
以上理念与特质并存于以下九大村落空间体系中:1、村落空间;2、村落形态;3、村落道路;4、村落水口;5、村落祠堂;6、村落社屋;7、村落水系;8、村落生态;9、村落遗存。
徽派建筑经历了形成、发展、壮盛、衰落、崛起几个期间,表现在:
1、形成期:上古-东汉末年,即山越文化时期,以古山越人干栏式山地建筑为主。
2、发展期:东汉末年-北宋末年(快速发展期),期间保留“干栏式”建筑特色,单层落地、当地砖、木、竹、石建造,大略的居住建筑形态。
3、壮盛期:明清时期,二、三层构大量涌现,民居建筑平面呈“凹”、“口”、“h”、“日”字型及自由型、复合型的多变形态。这一期间徽派建筑文化、技能、艺术发展到高潮。程且硕《春帆纪程》曾这样描述:“村落庄如星列棋布,凡五里十里,遥望粉墙矗矗,鸳瓦鳞鳞,棹楔峥嵘,鸱吻耸拔,宛如城廓,殊足不雅观也。”大型村落、公共建筑勃然崛起,商业市镇雨后春笋……
4、衰落期:清末-20世纪八十年代,建筑特色以二层木构阁楼为主,形态大略,天井转化前园,大型村落聚居形态逐步消逝减少。
5、崛起期:20世纪八十年代至今,以弘扬与传承,保护与发展,创新与利用为标志。对徽派建筑特色代价的认识在社会各界形成强烈认同,文化特色竞争代价属性已深入民气。
拉普普曾指出:“民俗传统直接而不自觉地把文化——它的需求和代价、公民的希望、梦想和情绪——转化为本色的形式。它的缩小的天下不雅观,是展现在建筑和聚落上的公民的‘空想’环境。”
徽派建筑作为徽文化的表现,无时无刻不表达徽州文化的范例特色。凝聚着无数创造者的非凡聪慧和寄托着人们深刻的梦想。在其村落的选址、空间的组合、功能的支配、室内装饰等无不表示出了丰富的空间表情,这种表情相解于人的心灵深处,是人性至理化的表现。表现在建筑形态的大多依山傍水、枕山面水,山、水、建筑相互融渗,体形严谨但又变革多端,以适应自然地形……正因如此,徽派建筑这种与自然相生相安,与大地统一延伸的和谐一体品质,正是当代化发展过程中人们日益失落落的人本环境及空间需求,亦即人与人、人与自然最直接、最实质的联系空间。它表达的是人的自然空间属性的呼唤,表达了人与自然和谐的需求,以是有内外同等的空间吸引力,正因这种地域的差异性、独特性,徽派建筑已成为一种精良的地域文化标志,一种文化传统的名片,已从一种历史传统转化为一个当代国际旅游城市的资源,一个城市文化的成本。这种资源代价表示在二十一世纪高消费是回归大自然、回归传统、回归生态的理念上,谁拥有和谐的自然生态谁就拥有“高品位”生活。
作为徽州文化生态赖以存天生长主要根本平台的徽派建筑,对付弘扬徽州文化,传承历史文化信息,增强民族自傲、自傲、自强。丰富完善城市文化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主要人类文化生态代价,以是徽派建筑有其与时俱进的当代生命力,这种生命力的核心便是越是地方的就越是天下的。
唯物辨证法见告我们:任何事物“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建筑的多样性与同一性也决定了天下万事万物都是不断变革发展之中,只有不断地摈弃自我,超越自我才能得到重新的发展,才能适应历史的哀求。徽派建筑作为一种文化征象也应是在永久的不断发展变革之中,传统历史建筑应严格保护,在此条件下新建筑应积极创新,只有这样才能适应当代城市发展功能需求;才能知足当代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求;才能延续历史传统给其注入新鲜活力。
本文源自中国青年报客户端。阅读更多精彩资讯,请下载中国青年报客户端(http://app.cyo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