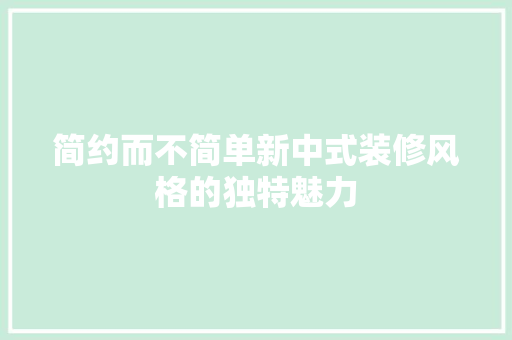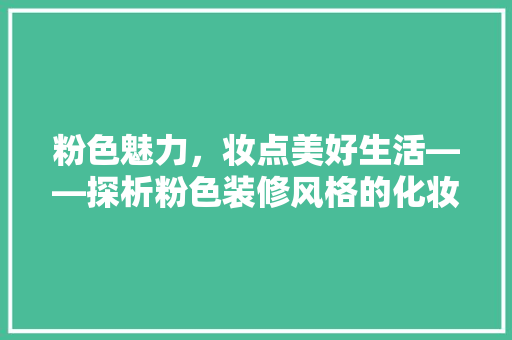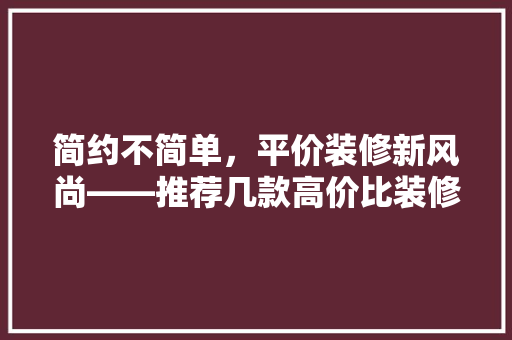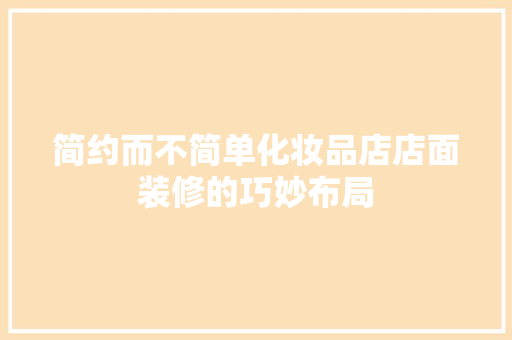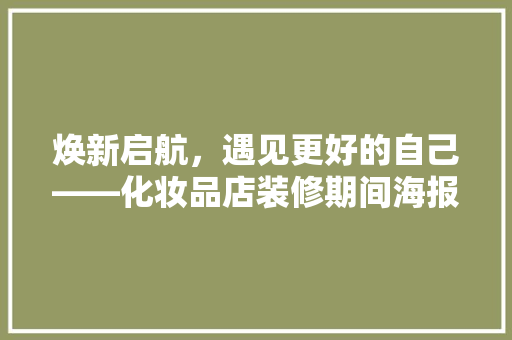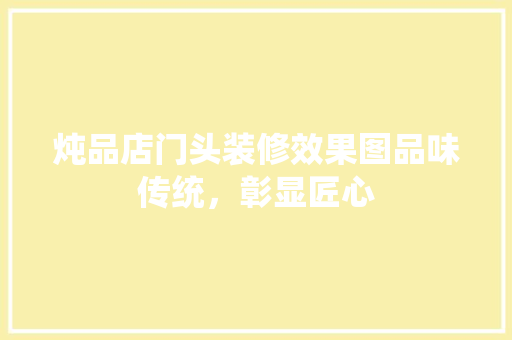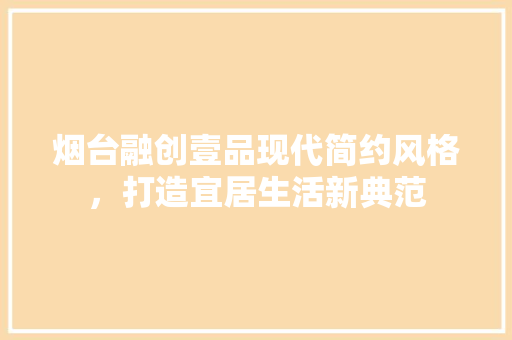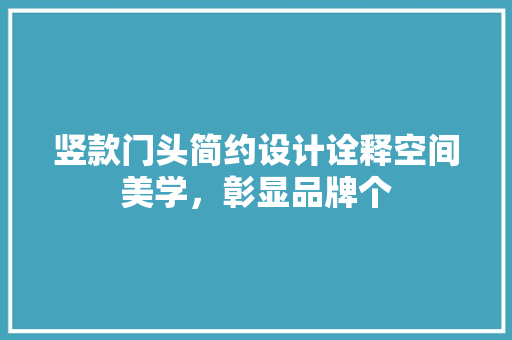潘天寿故居,坐落在杭州南山路景云村落一号,紧靠路边。我们游览西湖走到这里,见一块黄色大石,上刻“潘天寿纪念馆”五个大字,便走了进去。
潘天寿,是我国著名的画家、美术教诲家。原名天授,字大颐,号寿者,晚年多署颐者、雷婆头峰寿者。1897年生于浙江宁海冠庄村落。自幼好学,7岁进学堂,喜好写字,从描红格开始,每天中午写一张,从不间断。又热心于临摹《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插图,连乡里祠庙墙壁门窗上的彩绘人物、山水、花鸟,也都一齐心专心记而加以摹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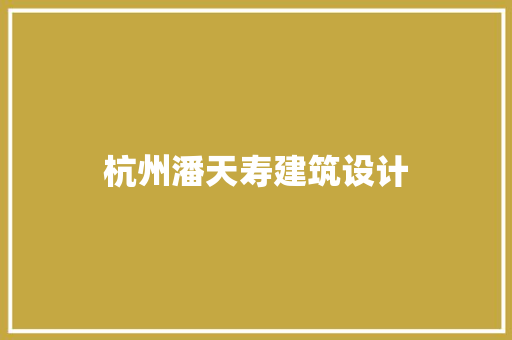
14岁,进入宁海县城小学读书,特选购《痤鹤铭》和《玄秘塔》,朝夕临摹。又购得《芥子园画传》一卷,便成了他学画的启蒙老师。“有志者,事竟成-------百二秦关终归楚。”事情便是这样,有心人才能造诣一番奇迹。从此,他下决心,要一辈子学习、研究中国画。
18岁,又以精良成绩考入浙江第一师范。这可是著名民主革命家、精良教诲家经亨颐担当校长的学校,聘请的都是风致高尚、学识渊博的一流西席。上虞春晖中学我去过,那也是经亨颐创办的学校,当时“北南开,南春晖”,享誉全国。
经亨颐不仅精于书法、篆刻,而且还对传统绘画深有研究。也就在这个期间,享誉中外的李叔同教授音乐美术等艺术门类知识。“名师出高徒”,这都对潘天寿受益匪浅,诗、书、画、印,得以并进。
转眼到了1923年,潘天寿经师友先容,来到了上海,任教于民国女子工校。上海是江南文化中央,人才荟萃,画家辈出,他便边授课,边潜心研讨,广收博采,画艺精进。不久,即被聘为上海美专国画系教授,教授中国画及绘画史课程,并编写出版了《中国绘画史》一书。
1928年春,杭州国立西湖艺术院创办,潘天寿即转杭州任中国画主任教授,并定居于杭州。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潘天寿迎来了新中国的建立。他负责学习新的文艺方针,深入雁荡山、黄山,汲取艺术素材,创造出歌颂祖国,反响时期的好作品,被国家和公民所重视,被保举为浙江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美协浙江分会主席。
潘天寿经由长期研究探索,终于形成了沉雄奇崛,苍古高华的自家艺术风格,还著有《听天阁诗存》、《听天阁画谈随笔》、《潘天寿谈艺录》、《中国绘画史》等,诗、书、画、印享誉海内外。
进了院内,有两座小楼,一座为潘天寿晚年寓所,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青砖老楼,一座为九十年代初期新建的佳构陈设楼。小院也非常新奇,冬青翠柏,紫藤凌霄,楼西草坪,正中还静竖着一块洁白的大理石,似碑似石,纯洁无瑕,不留一字。讲解员说:“这个院子,全体布局便是一幅画,这个地方恰好是盖章的地方。”按她的说法,这块洁白的大理石便是一枚图章了,形象思维,很故意思,艺术家便是别有情趣。
故居楼门口应是坐东朝西,上书匾额“潘天寿故居”。一进屋,便是八仙桌,两边分有座椅,墙上挂一幅中堂,看来是潘天寿的题字画,不明白的是,一样平常中堂两边挂的都是一幅对联,可这里不是,一边一幅题写的字。左侧是“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右侧是篆字,我还认不太好,只好悬念。
书房中有一幅对联,“戒是无上菩提本,佛为统统聪慧灯”,为李叔同——弘一法师书写的赠言。听说,潘天寿上学期间,遇上了李叔同出家。李叔同不仅是音乐家,也是字画大家,有着较高的艺术成绩,对潘天寿影响不小。对付李叔同——弘一法师,我也是比较欣赏的人物。天津的故居我去过,杭州虎跑寺我去过,上虞白马湖“晚晴山房”我去过,泉州开元寺我也去过,有人说李叔同——弘一法师便是在泉州圆寂的,我们在开元寺跑了一圈也没有找到灵塔。
还有一幅赖少其的题字:“应培养出像潘天寿师长西席那样民族的有独创性天下伟大艺术家。”赖少其,我在黄宾虹老家——歙县潭渡村落就见过他写的字——“公民画师”、 “钦治学维勤,仰画风独创”。 解放初期,赖少其是卖力华东文委事情的。在这些大师的影响下,后来,他自己也开始了国画生涯,成为当代著名的字画艺术大师。真是“近朱者赤”。
这里还有1995年5月16日,江泽民来馆察看时的夸奖:“潘天寿的艺术真了不起”、“这座小型纪念馆搞得很好!
”看来真是不错。从1944年接任国立艺专校长,到1971年逝世,潘天寿一贯居住在这里。室内依然井井有条,靠西窗有一大画案,摆放着一方特大雕花砚、以及常用的羊毫,书柜里满是文史籍画类书本,还有一帧潘天寿大幅作画的相片,我特意站在一旁照了一张相片,沾沾灵气、仙气。咱也是喜好字画职员,字还有些进步,画就不敢拿脱手了,只好自我陶醉,自我欣赏,玩呗!
最让我冲动的是,1984年4月,中华公民共和国文化部颁发给她们家的证书:“何愔师长西席及厥后代,向国家捐献一百二十幅潘天寿字画遗作,表现了高尚的爱国主义思想风致,特授此状,以资表彰。”这奖状,充分显现出一家人的高尚风貌。当然,潘天寿的儿子潘公凯也是非常精良的,较好地继续了老一辈画家的优秀传统,他也是中心美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父一辈,子一辈,一脉相传,可以了。
我总认为,自己干得再好,不如有一个好下一代,下一代干好了,你就少受点罪,下一代如果是个败家子,你就受大罪了。在生活、交往中,我颇有感触。好的下一代能把父辈的好传统都继续下来,发扬光大;不好的下一代都会把父辈的东西挥霍掉了。
参不雅观之余,我又负责欣赏了潘天寿的论艺,在学习、传授教化中,他有好多深刻的体会、履历告诫着人们。“高尚之艺术,能使民气感悟而渐进于至真、至善、至美之田地------”“艺术为人类精神之结晶,又为人类精神之食粮。”“艺术是人的精神产品,反过来又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对付中国画来说,书法也是根本演习,诗文也是根本演习,要相互合营在一起。”
这句话我特殊爱听,有的人画画可以,写字弗成,诗词更不懂。一个好画家,题款、题诗,随手就来,珠联璧合,相得益彰,那才美呢!
好呢!
让人喜好。潘天寿讲:“学之不深,行之不远。”“画画的人,不能局限于画画一壁,对诗文、书法、画论、画史等等方面的学识必须很好研究。学识要博,见闻要广。”
1962年6月,潘天寿作为中国书法代表团副团长赴日本稽核回来,有感于中国高校书法教诲的欠缺,在出席全国高档艺术院校教材会议时就提出,“目前老书家寥寥无几------后继无人,出息堪虑,我建议在美术学院设置书法专业,包括金石、篆刻,以便迅速继续。”自1963年秋,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便正式设立了书法篆刻科,对中国高档书法篆刻教诲奠定了根本。
当然在参不雅观中,我对潘天寿的画作也拍照不少,留着自己逐步学习、欣赏。参不雅观便是学习,学习便是教室,愿这样的教室越多越好。
九口202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