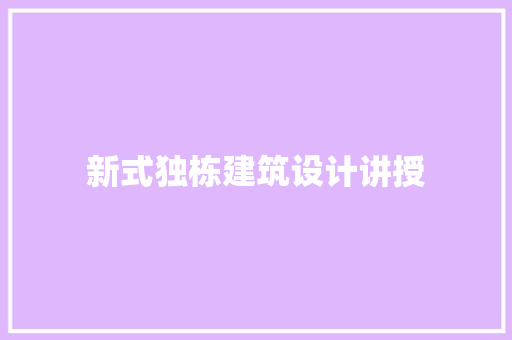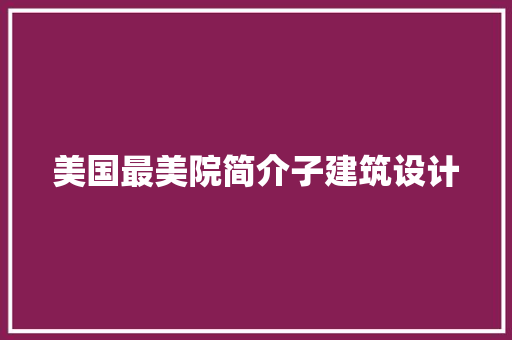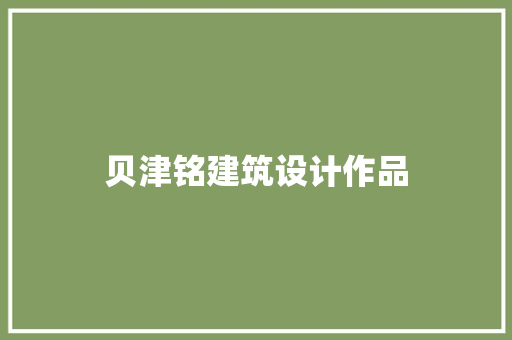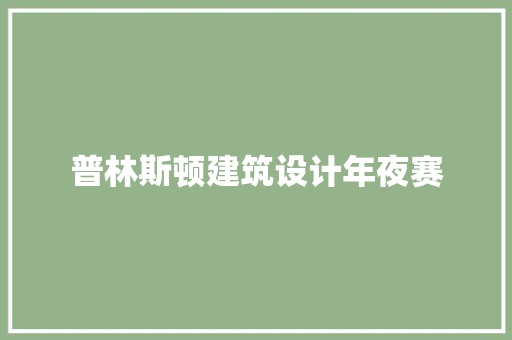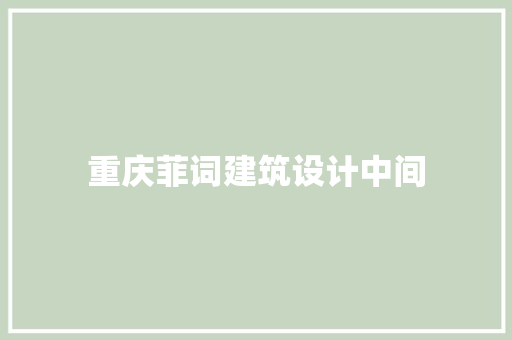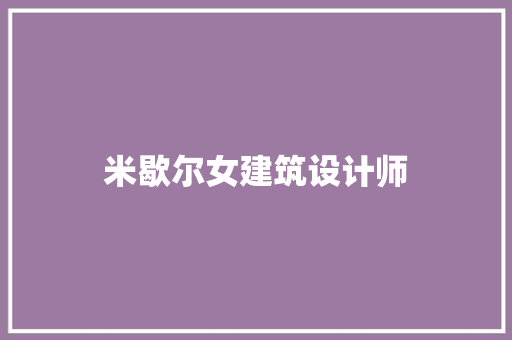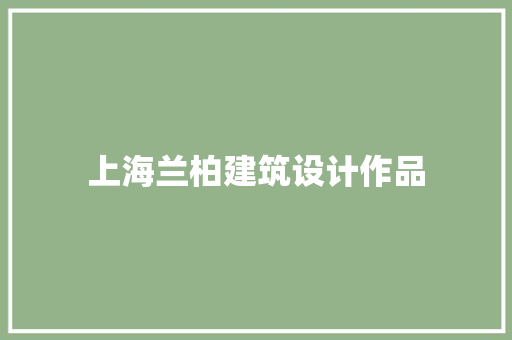而在同年6月的一篇《New Yorker》中,文章作者将爱德华·霍珀称为“美国孤独的视觉吟游墨客”,并直接点明霍珀的艺术的实质:孤独是他的伟大主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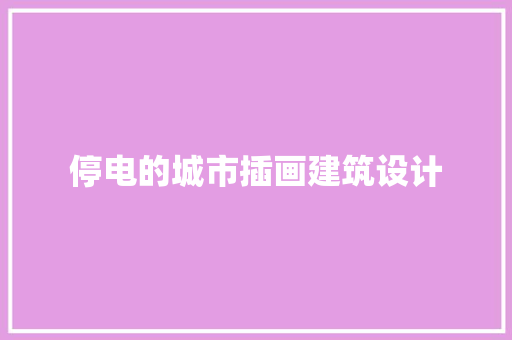
是啊,在霍珀的画中,浓郁的孤独感总是逼仄而来,挥之不去。对付这位19世纪末出生、1920年代步入美国画坛的画家,孤独是他毕生的课题。当与他同时期的菲茨杰拉德在小说中记录美国爵士时期的鎏金派对时,霍珀在画中描述的却彷佛是一些从未被约请参加派对的人。
霍珀选择的绘画主题是他那个时期特有的。他终其生平的活动范围也险些只局限于纽约到新英格兰,美国东北部的部分地区。然而他通过绘画对天下的核阅,不仅适用于当时的全体美国,也让半个世纪后的我们难掩心中的共鸣。他的艺术无疑是永恒的,超越了韶光的所指,在艺术史上投下一道长长的阴影。
爱德华·霍珀自画像
爱德华·霍珀被公认为二十世纪美国最主要的现实主义画家。但他对现实的意见是有选择性的:他选择描述空旷的城市景不雅观、郊区风景,以及伶仃的、原子化的人物。这些作品反响了艺术家自己的气质,同时也表明,现实主义不仅仅是对我们所见事物的复制。
爱德华·霍珀也是一位美国当代画家,然而他的艺术显得很不“当代”:它们内容写实,既不抽象,也没有技法的创新,在当时愈演愈烈的立体主义、野兽派等运动中显得不为所动。那个西方艺术天翻地覆的期间,在霍珀的天下彷佛戛然而止。
爱德华·霍珀1882年出生在纽约州奈亚克(Nyack)镇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一名贩子。霍珀从5岁起就迷恋上了绘画。在他画于9岁的一幅画中,一个小男孩双手背在身后,站在空无一人的海滩上,萦绕着他的背影的是深深的孤寂感。彷佛从这时起,霍珀的创作风格彷佛就已经展露雏形。
看海的小男孩(1891)
在父母的支持下,1900年到1906年,霍珀在纽约艺术学院学习商业艺术。在此期间,他受到了“垃圾箱画派”领袖罗伯特·亨利(Robert Henri)的主要影响。完成学业、并短暂地从事过一段期间的插画事情后,霍珀厌弃了商业艺术,而当时的美国能给他的灵感彷佛已经穷尽,于是,前往欧洲成了很自然的选择。
霍珀曾三度前往欧洲,在这里度过了漫长的旅行。那时,欧洲对爱德华·霍珀来说意味着法国——更详细地说,是巴黎。当他于1906年抵达法国时,巴黎是西方天下的艺术中央。艺术已经开始向抽象绘画转变。立体主义开始了。1907年,毕加索在那里画出了他的传世之作《亚威农少女》(Les Demoiselles d'Avignon)。
霍珀绘于欧洲求学期间的作品
但霍珀坚称,他在巴黎时从未听说过毕加索。对付霍珀,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并不是立体主义,而是与印象派的相遇。印象派画家对光芒、建筑和自然主题的处理,影响了他此后的所有作品。
《航行》(Sailing, 1911),霍珀卖出的第一幅画作
从这时起,他将学生时期创作过的颜色暗沉、风格古典的作品抛在脑后,离开了维米尔、卡拉瓦乔、伦勃朗和委拉斯开兹的传统,转而投向印象派的阵营。莫奈、塞尚和梵高是他的老师了。他的调色板亮了起来,他开始用轻快的笔触作画,让自己的画面具有不断变革的色调比拟和不平衡的构图。
1962年,霍珀说,“我想我仍旧是一个印象派。”
回到美国后,霍珀一边靠商业插画家的身份自主,一边通过蚀刻找到了提高的道路。《铁道旁的房屋》(House by the Railroad, 1925)是最早让他“出圈”的作品,也是纽约当代艺术博物馆(MoMA)收购的第一幅霍珀。
《铁道旁的房屋》(1925)
在画中,通亮的阳光照射在屋子上,投下深深的阴影。铁轨上没有列车经由,四周一片寂静,这让屋子显得更加突兀和巨大,弥散着悲哀的氛围。
作为霍珀“荒凉都会画作”的起始点,《铁道旁的房屋》所表示的风格将在霍珀日后的职业生涯中一次次涌现,构成他作为职业艺术家的根本。这幅画也启示了电影大师希区柯克。在他摄于1960年的电影《惊魂记》中,贝茨旅社的外部景不雅观就取自这幅画。
《惊魂记》(1960)
事实上,霍珀的一个特点就在于,只管他没有掀起或参与任何绘画革命,但我们总能一眼就能辨认出他的画。“一旦你看到了一幅霍珀,它就会留在你的脑海中”,《New Yorker》将此归结于“一种非凡的风格聪慧”。霍珀本人曾有过类似的表达:“我试图以对我来说最亲切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形式呈现我的觉得。”
就像梵高的向日葵、莫奈的睡莲,霍普也有他热爱和不断回归的主题。个中一个主要的关键词,便是光。
霍珀对光芒的处理非常敏感。无论是清晨或薄暮时的阳光,还是投进宾馆房间或办公室里的微弱日光,他总能让画面中的光芒营造一种戏剧感。
《杂碎》(Chop Suey, 1929)
《布鲁克林的房间》(Room in Brookly, 1932)
《二楼上的阳光》(Second Story Sunlight, 1960)
《阳光下的人》(People in the Sun, 1963)
但他并不像印象派那样,关心不同光芒下物体的颜色,而是把光当作工具——尤其是光的色彩、亮度、以及强光下的阴影,都是他把场景戏剧化的手段。
有时,这种光芒是阳光或自然光。例如《科德角的清晨》(Cape Cod Morning, 1950):
冷调色盘呼应着光芒下的建筑物,形成强烈的明暗比拟。画面中,一个女人被清晨的阳光引向窗外,向外张望,在通亮的光芒面前眯起眼睛。这是一个充满无限期待的时候。然而对付一个反复描述晚景的空虚和孤独的画家,如此巨大的期望注定会落空。
还有《海边的房间》(Rooms by the Sea, 1951):
画面中的阳光非常强、却非常冷,乃至让人感到“冷冽”。再配上房间里的空旷,窗口的空洞,让全体画面呈现出一种诡异的冷感。光影之下,墙壁与门窗、家具与摆设,将画面切割成大大小小的几何形状,以隐晦的办法呼应了绘画形式的当代风格。
在描述都邑生活时,霍珀更方向于非自然光与人造光。个中最范例的是《夜游者》(又译《夜鹰》Nighthawks, 1942):
这是爱德华·霍珀最有名的代表作,创作于1942年,后来多次涌如今电影场景中,被普遍视为孤独一词的最好诠释。
画面的主题是一家亮着刺目灯光的街角酒吧。酒吧里有一个做事生和三个客人,他们彼此之间彷佛没有任何互换,我们也看不出他们的关系。
四个人物被酒吧内通亮的光芒笼罩着,室外则生僻,安谧,寂寥,没有半个人影,也没有其他光源射出的光芒。它呼应了一个背景,即二战期间、珍珠港轰炸之后,城市陷入大停电,被阴郁包围。
由于光照,画面被分割身分歧的块面,边界清晰分明,乃至非常锐利,更富有立体感。画面中亮到诡异的光,没有让人觉得到丝毫温馨,却透露出一种无处倾诉的寂寥。
伴随着对光芒的执着,霍珀的画作另一个显而易见的主题,是孤独。
从巴黎游学归来后的霍珀,恰好迎上了美国的“黄金20年代”。这时一战刚结束不久,美国经济迎来高速发展,大批人来到城市追寻美国梦。这时也是猖獗享乐的“咆哮20年代”。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曾这样描述:那个时候人们猖獗派对,连榨汁的橙子皮和柠檬皮都可以堆成小“金字塔”。
与此同时,好莱坞电影开始崛起;以雷蒙德·钱德勒为代表的推理小说迎来黄金时期;以帝国大厦为首的摩天算夜楼拔地而起……然而社会的飞速发展与飞腾的享乐主义,也造就了孤独和迷惘的一代。人们背景离乡,不再奉行上一辈所坚持的传统不雅观念和生活办法,城市内部也逐渐形成了一个个“陌生人社会”。
如果说此时的美国社会是鼓噪的、多变的,霍珀笔下的美国与美国人却是寂寞的、冷漠的、疏离的;如果说当时人们普遍追寻着“美国梦”,霍珀笔下的美国人却在经历着“美国失落眠”。
在霍珀的画中,当代城市和景不雅观的构培养像一台制造孤独的机器。例如《旅社房间》(Hotel Room, 1931)中,女人坐在巴黎面积局促的小酒店里,腿上平摊着一本厚书。她头低垂着,感情低落,彷佛是被生活打败了:
类似的还有《清晨的太阳》(Morning Sun, 1952)。女人穿着短睡裙起身坐着,窗外的阳光非常刺目耀眼。女人彷佛刚刚被阳光叫醒,愣愣地看着窗外,还在回味刚做的梦:
以及《夜游者》。画中的四个人物同处一个空间,彼此之间近在咫尺,却无话可说,忧心重重。巨大的窗户没有任何遮蔽,而是拥有一层完全的玻璃,它让这个空间看似洞开,实则隔绝。
与封闭式构图相结合的,是夸年夜的冷暖色比拟。在这幅画中,颜色本身就构成一种措辞,它比人物的动作更具有表达力。
没有了白天的繁盛热闹繁荣作为掩饰笼罩,巨大的孤寂感已经无处躲藏。就连霍珀本人也说:“不知不觉中,大概,我的确是无意识地在描述一座大城市的孤独。”
这些画面将绘画的互换能力推到了极限。这便是霍珀:他让我们独处,也让我们屏住呼吸。他的画不仅是对美国社会的深奥深厚不雅观察,也揭示了一种普世的人生原形:没有任何地点能够真正属于我们。孤独是我们的宿命——无论我们是否独自一人。
(本文来源于"大众年夜众号·艺术与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