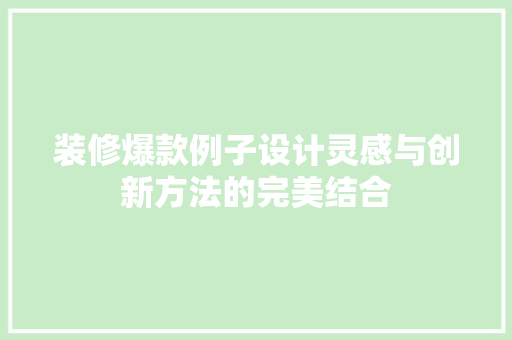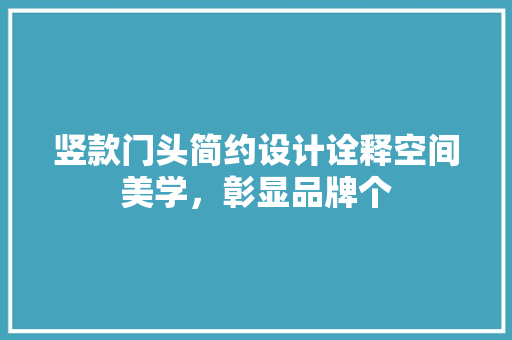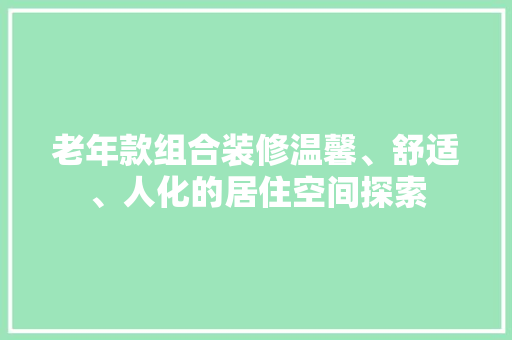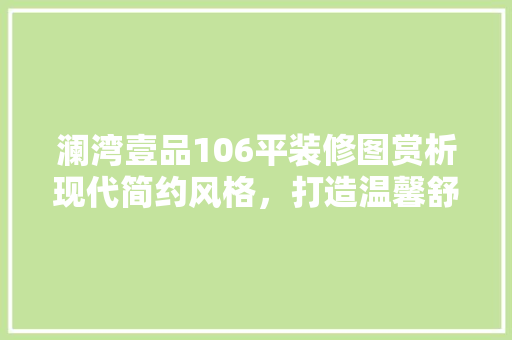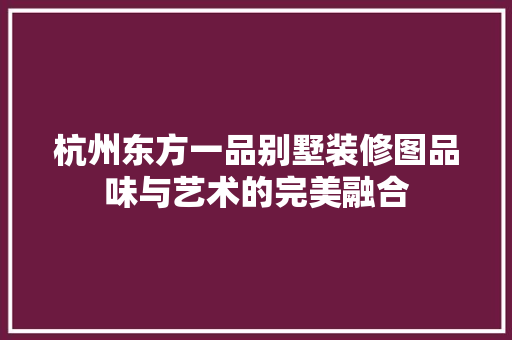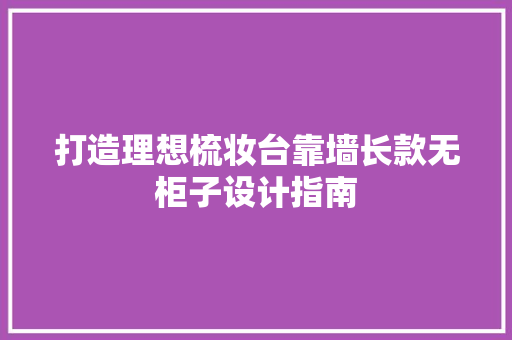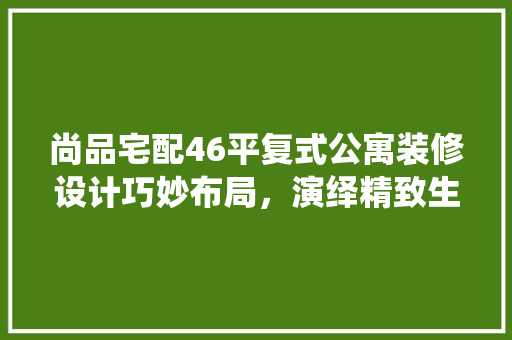英国维多利亚期间的著名墨客、设计师、社会主义者威廉·莫里斯认为,工业化时期的阶级压迫和劳动分工不仅对人性造成了压抑和分裂,也对原来的“物”的本性造成了严重的毁坏。艺术和设计是人的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通过朴实纯粹的艺术和设计,人的知觉敏锐性会得到提升,道德感将得到加强,能重获温暖和肃静,达到社会的平等和人类的幸福。克劳福德认为,在以莫里斯为主导的工艺美术运动的设计中,用一个词来概括其审美特性较为准确,即“物性”,也便是“物的设计反响了它的性子和目的,在这个过程中,物不会被过度地润色,也不会使它看起来像别的东西”。莫里斯的设计美学中的“物性”表示出存在论的特色,即通过设计和生产行为,使物的本性如其所是地显现出来,物既是静态的,也是天生的,它是一种生命的延展和聚拢。莫里斯的设计美学还展现了“物尽其用”的品质。这些都表示出其设计中“物之为物”的美学实质。
如其所是:设计使物展现自身

设计的“物性”首先指称“物”的朴实性和真实性,即通过工艺和设计,将“物”的内在朴实性和真实性如其所是地显现出来。莫里斯所在的维多利亚时期,是大英帝国繁荣自傲的期间,1851年的伦敦天下展览会显示了工业化、标准化和规模化的巨大胜利。当时的“水晶宫”在海德公园快速建起,来自天下各地的10万多件展品在近100万平方英尺的空间里展出。但对莫里斯来说,水晶宫连同它的展品犹如巨大的“侵入物”和“令人惊骇者”,摧毁了英国传统的道德不雅观和审美认知,也摧毁了人们对中世纪、田园、自然和纯朴感想熏染的切身归属感。在年轻的莫里斯看来,工业化造成了人与天下的分裂,原来纯朴自然的装饰和设计失落去了存在的空间。当设计无法使“物”回归到它最好的品质时,人也会逐渐失落去对生活贴近的温暖感想熏染,无法从对“物”的持有中得到肃静和代价。
在莫里斯的美学不雅观中,朴素自然的“物性”仿佛有着人性的特色。他认为,设计中不应该掺杂太多浮华或自我表现的技能,也不应该涌现任何异想天开的、过度的抱负。相反,设计应是“工匠般的”和“谅解的”,它既不许可大脑,也不许可手的“过度劳累”。设计是通过工艺和装饰的一系列过程,将“物”的“物性”呈现出来,人通过“物”得到存在感,这是生命和生活中十分主要的感想熏染。
正如莫里斯在《艺术的希望与恐怖》中所讲到的:“不要把木头和瓷砖混在一起;让木制品看起来像墙面的一部分,让瓷砖看起来像烟囱的一部分。”莫里斯认为,一间餐室不应该整洁持重得犹如牙医诊所,一间客厅也不能看起来令人无聊。让人们从他们必须利用的东西中得到乐趣,这是装饰艺术的一个伟大功能。在莫里斯眼中,“物性”与“德行”有着共通性:好的设计物拥有天生的“道德品质”,而糟糕的设计就像道德上的污点。“物”的自然性和纯朴性是好艺术的根本,而好艺术又是道德社会的根本。设计师该当“节制”他们的材料,使其“表达意义”和“做事美”,但如果让人们盯着处理形式的机动,则又忽略了“物”本身的权利。
成长和聚拢:设计使物的生命呈现
在莫里斯的设计美学不雅观中,“物”不纯挚是现实存在物,也是此在的存在状态。好的设计是将聚拢于“物”中被遮蔽的生命展现出来,并使其按照生命的规律去成长。
莫里斯的花卉图案设计美学的原则有两个,即“秩序”和“意义”。“秩序”便是指设计师或工匠必须对物的约束和限定有深入的理解和把握,以进行形式的布局,从而得到构造感和秩序感。莫里斯的图案抵制静态的重复,通过设计和编排,迫使不雅观者从不同的角度不雅观照和创造物之美感。这种引发感知的办法,使人仿佛面对迄今为止未被把稳的天下,以一类别致的眼力去看待“新天下”,得到新感想熏染。
而“意义”是指在秩序的根本上生命的可能性展开,是通过形式呼吸的具有生命力的精神,它的至关主要的指向是发展和变革。在孩提时期,莫里斯就培养了对花卉的强烈兴趣,植物作为颜色、质地、气味、构造和生命力的聚拢地,带给莫里斯超乎平凡的审美感想熏染。在发展的过程中,他在浪漫主义和达尔文主义之间保持平衡,这授予了他强烈的好奇心和对有机生命的热爱。莫里斯在《无名教堂的故事》一文中表达了他对自然花卉中生命美的由衷惊叹:“花园里的棚架上爬满了玫瑰、旋花和大叶火红的旱金莲;特殊是在杨树的阁下,一贯都有一些棚架,但是在这些棚架上只长着深樱玫瑰……蜀葵也开满了花,有粉赤色的、橙色的、赤色的、白色的大尖顶,还有优柔的绒毛状叶子。”这些花卉按照自然所规定的路径去成长,并以各种形式在莫里斯的图案设计中身姿曼妙地呈现出来。莫里斯的设计既有物的静态浪漫,又强调内在生命力的磅礴变革,就犹如图案中的藤蔓,仿佛有足够的能力自发地按照自我的自性不断成长下去,穿插环抱,永一直息。对莫里斯来说,设计美中的“意义”和“秩序”是紧密相连的,只有当“发明和想象力服从于秩序的束缚”时,这些发展和变革才有实体与可见的存在。
物的民主化:通过审美走向平等
莫里斯的设计,尤其是植物图案的设计采取几何根本上构建的重复模式,事实上表达了一种潜在的社会主义的平等不雅观念。这里没有等级的层次,没有一种主导的形式,花鸟、藤蔓、纹理相互支持和彼此造诣。莫里斯接管了社会主义者卡莱尔和约翰·罗斯金的思想。卡莱尔第一个提出了“英格兰状况问题”,责怪统治阶级未能对公民卖力,他将19世纪的英国与中世纪的英国进行了比拟,认为前者是一个物质主义和冲突的社会,而后者是一个想象中的秩序的天下,由真正的道德引领。批评家约翰·罗斯金对莫里斯的影响尤为深刻,其《威尼斯的石头》的第二卷“论哥特式的实质”对莫里斯早期的审美和智力构成了至关主要的影响。通过这些,莫里斯认识到艺术应成为"大众年夜众关注的问题,它不仅是精英们的个人爱好,也是全民道德水平和社会平等与否的标志。艺术标准的低落,是一种深刻的文化萎靡。罗斯金开启了莫里斯的智性之门和不雅观看天下的眼睛,让他窥见哥特艺术的奇迹以及粉饰当代天下的残酷剥削。这使得莫里斯希望通过设计革命达到政治改良的目的,即借由“审美的转变导致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变革”。
在维多利亚时期,“高等艺术(绘画和雕塑)”和“低级艺术(建筑和装饰)”被严格区隔,人们将绘画和雕塑视为高档艺术,置于顶端;而将建筑和装饰艺术置于较低的位置。作为设计师和社会主义者的莫里斯倡导“艺术的民主”或“公民的艺术”,即无论何种艺术,都应由制造者和鉴赏者共同参与,当这样的群体遍布全体社会时,艺术,尤其是作为“低级艺术”的工艺和装饰就会成为日常事情和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人们才会通过制作和利用它们而得到事情的乐趣,并提高审美鉴赏力和对天下的判断力。莫里斯认为,艺术本身只有通过"大众对艺术的广泛参与才得以生存和延展,人们在参与中得到体验和感想熏染。只关注少数精英群体会使艺术变得过于薄弱,末了将走向艺术的反面。只有使艺术变得遍及和共享,并触及每个人的生活,才能通过改变审美意见意义得到改变天下的可能性。
综上,莫里斯设计美学中的“物性”不仅指物的本性和存在办法,更指向通过设计实现物的“如其所是”的存在状态,并展现出生命的聚拢和成长。“物性”强调统统生命的“去遮蔽”和“展开”,在非异化的条件下,设计师、不雅观者、利用者和作品(物)共同参与艺术的创造,共同建构一个成长的天下,这个天下美好、民主、平等,并充满了莫里斯所倡导的道德行。对莫里斯的设计美学中“物性”的挖掘,对当下的纯艺术与设计艺术、设计与社会、设计美学与日常生活美学之间的关系磋商,具有主要的意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当代性的视觉秩序研究”(20AZX019)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广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教授)
本文来自【中国社会科学网】,仅代表作者不雅观点。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供应信息发布传播做事。
ID:jr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