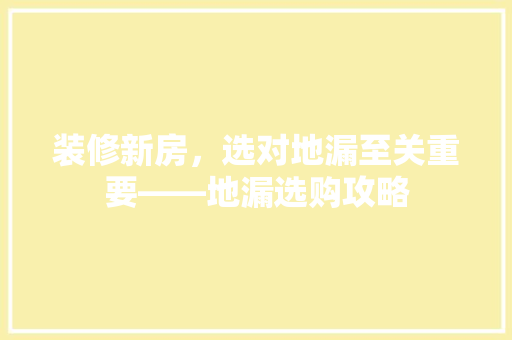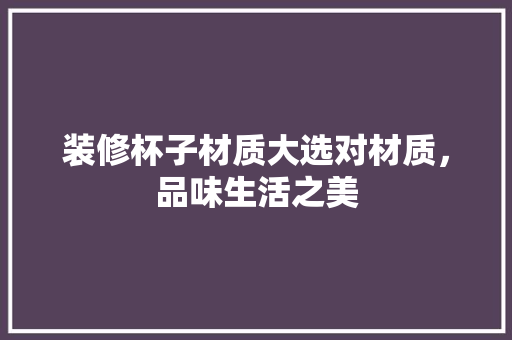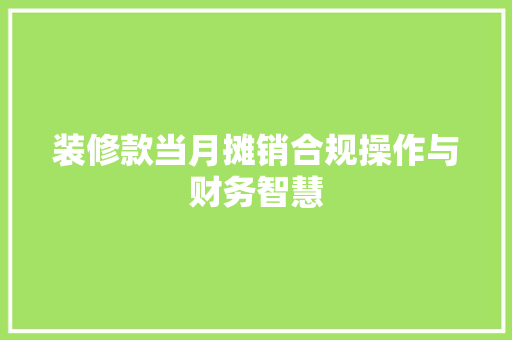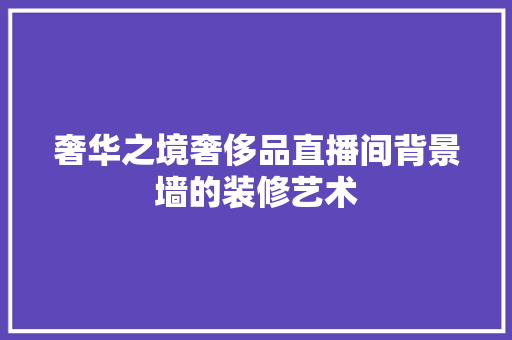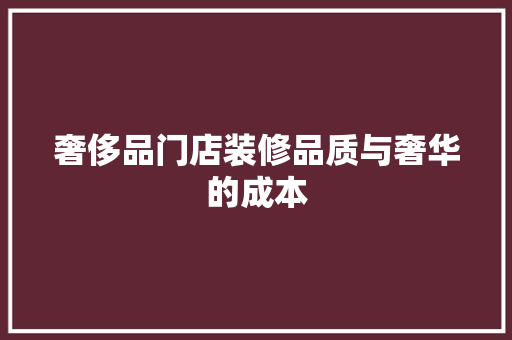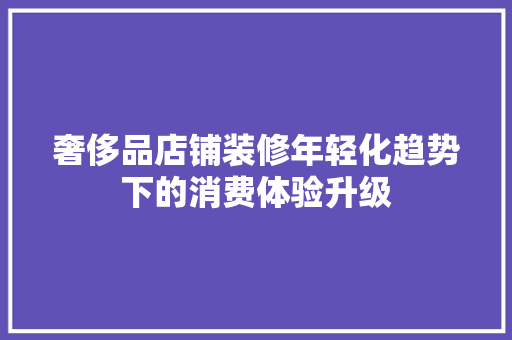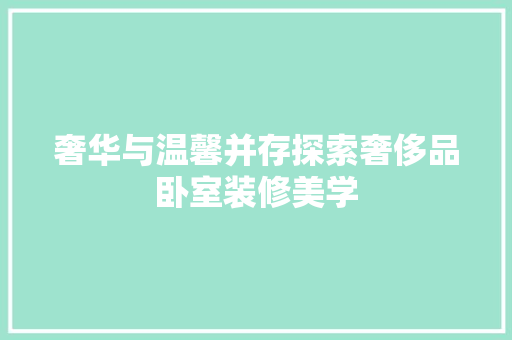紫蓬山地处江淮分水岭,其义有广、狭之分。广义的紫蓬,大抵有120平方公里,涵括清代的“三山”片区,为淮军故里。这一带崇冈峻阜间,错落有致地分布着刘铭传、张树声、周盛传等淮军将领家族的圩堡,选址都极富微地理之美、堪舆之妙。狭义的紫蓬,则仅是西庐寺坐拥的那个山头,约6平方公里。这片一僧衣之地,俗称“李陵山”,海拔不敷200米,是安徽众山里的“小个子”。但,山不在高,紫蓬山却有着与合肥的名胜古逍遥津、古教弩台一样悠久的历史,颇可引人发思古之幽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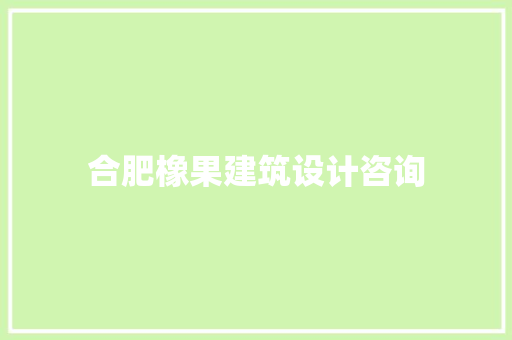
紫蓬山,相传在东汉末年曾为李典驻兵处,似与曹魏干系。然又由于山介江淮之间,自古多兵戈之事,文献极匮,常常又混沌不已。大约因此之故,晚清李恩绶在纂辑《紫蓬山志》时,也不好措手,于是“不必远引,断自有明”……明代以前,确实不好整,纵然硕学如李恩绶,也不大好落笔。不过,那些零散的细枝末节,仿佛紫蓬山的鳞爪,也是值得一记的。这篇小稿,就有狗尾续貂之意,且不惮于贻笑大方。
《紫蓬山志》书影(来源 | 孔役夫旧书网)
不管咋样,都该当感激这位京口李亚白师长西席,是他为紫蓬山(李陵山)留下乡邦文献,使子弟登临者,不致有“文化荒山”之感。我乃至主不雅观地认为,是否可以称作“名山”,最少得有一部山志。这个意义上,紫蓬山是幸运的。
林泉丘壑《紫蓬山志》初辑竣于光绪乙未(1895)。在此之前,山顶的西庐寺“大山门”就已悬有一匾,由歙县籍的洪福(字海如)题额:庐阳第一名山。这位洪海如,可见资料甚少,山志载其为“文籍”,推测应是国子监文籍,大概相称于本日PKU图书馆馆长吧。洪可能是应山下周老圩主人周家谦之邀来游紫蓬山的。周也是一位雅擅书法者,匾由洪题,足见洪的笔力非孱。此匾的书写韶光,当在1884-1890之间,即西庐寺获颁《龙藏全经》之后数年内。
西庐寺(来源 | 西庐寺)
“庐阳第一名山”的第一重涵义,当是指的“获颁《龙藏》”这一盛事给紫蓬山带来的有名度、美誉度。“荷哲后之洪恩”——御赐《龙藏》,还与慈禧有渊源。
本日,站在后世的角度,名山之“名”,有了更多内涵。比如,山志的纂辑、存世;比如,山中的林、泉、丘、壑;再如,本日的风景名胜区、旅游度假区、地质公园等多项名誉的加持……无疑都给了“庐阳第一名山”以真切的支撑。
林草长莺飞的仲春天,是前来紫蓬山游览或礼佛的春秋佳日之一。此际的紫蓬山树木蓊郁,满目葱茏,处处春气蓬蓬,然而最养眼的却要数山顶的那一片橡树林——纯然一色的古麻栎林。树干吊颈挂的保护牌显示,这片壳斗科纯林树龄逾150年。相较之下,这片橡树林树杪的颜色偏于鹅黄,要异于周遭林木的青翠,实在是显著的标识。
白云古道(来源 | 紫蓬山风景区)
西庐寺踞于山巅,有“树包寺、寺包山”的方案特色。正是这片林子,造诣了紫蓬山西庐寺的这一特色。设若是寒山红叶的深秋来游,则铁干虬枝,秋意疏钟,又别有一番浑穆的道场气候,令人不忍喧哗,乐不思蜀。据《西庐寺善后碑记》,百多年前的晚清期间,这片树林该当是属于西庐寺的佛田、寺产,起先或为某个土著大姓(当地有卞、程、吴、刘、汪、周等)所施山场。
苟能偷得浮生半日闲,并于明净的秋色里,徜徉山中,漫无目的,纵然只是捡拾散落于草窠里的橡果多少枚,也是一件饶有清趣之事。林是旃檀,更无杂树;花为薝卜(草字头加匐),不嗅余喷鼻香——光绪十二年(1886),晚清名臣李鸿藻撷取《六祖慧能禅师碑铭》中的句子,为通公塔题联,彷佛是为这一片禅意之林量身定制的,暗合了紫蓬山西庐寺的周边环境。每一棵橡树都是一个天下,“似满天星斗,个个都是神,自由又互为一体地生活在一起。”——紫蓬山巅的橡树林,令人想起荷尔德林笔下的林子。
泉紫蓬山是有泉水的,至少是有泉脉的。山志所载的就有两处:一在千字山腰,一在李陵山东岩(又称“东崖”),为“四川井”。
千字山泉,其味甘洌。一代画僧
四川井泉水,极清澈,“土人沿为今名,亦不知其所始自”。久未修订的官方《紫蓬山导游词》里,说是与虚腹和尚有关,显然不敷采信。释虚腹曾栖居芜湖广济寺,光绪初年渡江来紫蓬山,“与通元长老谈禅最契合,有终焉之志”。通元即袁宏谟,为西庐寺复兴一代开山祖师。
山志的修纂,释虚腹该当是策划人之一,这从李恩绶《答虚腹上人书》《与虚公书》并虚腹所作《紫蓬山志序》可一窥始末。这位高僧大德俗家为四川成都人,山志中有交待,但“四川井”与其无关却是昭然明白的。西庐寺东南,旧时有一块菜圃。四川井的存在,应是寺僧灌园艺蔬的水源。农禅并重、禅茶一味,此应系曹洞宗风。
二泉皆从石罅流出,“异于他水”。
山泉溪流(来源 | 今日头条)
江淮之间,同为大别山余脉的诸山多有泉水。譬如,八公山有珍珠泉,琅琊山有酿泉,巢湖汤山有温泉,庐江发谼山、无为轩车山等有笑泉……间隔紫蓬山(狭)甚近的大潜山、龙穴山亦有泉,个中龙穴山早在北宋即以泉水著闻,时称“龙池山(泉)水”,见载于欧阳修《文忠集》等文集中。
关于泉水,对付跻身地质公园的紫蓬山而言,或是一个有研究代价的课题。
丘·壑紫蓬山一带,有一则迴龙庙的传说,又称“五龙簇珠”——唐时,新罗人金乔觉游历庐州,见兹山形胜,拟于此地草创道场,奈何甫一打坐,地身发穰,冈陵震颤。五龙见状,亟来护持,然稍迟滞,地已陷为河陂。于是辞别而去,后来卓锡九华,为地藏菩萨。留而不得,老龙殊觉惭愧,化身为丘陵。后人感佩,为之立庙。
金乔觉(来源 | 网络图片)
迴龙庙旧址,即今位于紫蓬山东北一隅的紫蓬商业街,惜乎老地名不存。今山前的停车场附近,尚有名为“中陷塘”的水面,也是导源于此民间传说。不足为奇,据闻六安的大西岳云峰寺也有类似传奇。可见,金地藏的游踪不止一处。又或许,大约这是民俗中的异文征象吧?
“五龙簇珠”,不完备是出于古人的天真,也是可以与实际相推求、印证的。大体上,按顺时针分布的羽士山、石佛山、狼(郎)大山、杨大山、甘家洼大山,可视为“五龙”。这些培塿小山,环伺紫蓬(李陵山)旁边,如众星拱月,使得紫蓬山愈显气候巍然。于此,彷佛又可窥见古人对付环境的体察,是如此之细腻和富于温情。
因着这些小山们的簇拥,周遭之内诞育了一系列的山中秘境——紫蓬十八洼,令人一见爱慕,歆羡不已。李陵山洼、吴山洼、甘家洼;大孙洼、小孙洼、囫囵碾洼、流波洼、周山洼;中洼、高门槛洼、朱家洼;东陶洼、西陶洼、千山洼、打子塘洼、檀树洼、端公洼、陶家洼,洼洼有人家。洼者,山隈也,多凹然而深秀。伴聚落而生的,山洼里每每还有一口水塘。于是,渔樵耕读,四季如画。
千山洼(来源 | 四海钓鱼)
在紫蓬山浩瀚风景幽然的丘壑中,石佛山与打子塘洼这一丘一壑,尤值得一提。据《天下名胜志》《南畿志》等载,李陵山之东有石佛山。本日,石佛山埋没无闻,然而在元代,这里曾设有“竹林关”,与“长城关”同为古庐州府城西南主要关隘之一。
曾有学者撰文推测,古石佛山在今“佛园”景点一带,实属误读。文中作者将“李陵峡”解读为囫囵碾凹地点的峡谷。然而,李陵峡的“峡”却非峡谷之谓,实际是一堪舆名词,指的是“龙过峡”,所谓“蜂腰”“鹤膝”一类。
古籍见载的“石佛山”,准确的位置是今程大关、朻藤湾、店塘坎、槽坊郢、高门槛围合起来的那一座山。古竹林关,即今程大关、小关附近。发源于此山的丰乐河左岸支流赵小河,旧名“竹林关水”。程大关背倚的小山包,古称“竹冈”,当年有一古径,由此经烧脉岗、长安集、大蜀山,迤逦至合肥西平门(另有一径由三十岗、桃花城,至德胜门)……虽然考稽起来,颇显冗长,却是可以钩沉的。石佛山-竹林关,就像遗落山中的合肥地域文化的一枚书签,独具历史代价。
紫蓬山(来源 | 档案不雅观止)
打子塘洼,位于国师岭下,是旧时经由紫蓬山南麓朝山进喷鼻香者的歇脚处。打子塘是一口水不甚广的山塘,俗相传:求子的喷鼻香客在此稍憩,可以撇石子(“撇撇溜”)以卜所许之愿,颇灵验如斯。个人所感兴趣者,是“国师岭/國師嶺”的得名由来。很可能,这位国师便是那位“喫茶去”的赵州从谂禅师。前往参访的舒州投子禅师,或许便是禅宗史上的大同禅师,有“投子打油”公案一段。
据释三惺《西庐寺源流序》,这座庐郡名蓝是“到李唐间始赐额,曰:西庐寺……”以此不雅观之,紫蓬山在唐代,至少在晚唐,已经是“天下名山僧多占”了。另一处历史的遗痕是,今蜀山区鸡鸣山古有显应寺,李唐时曾名“上庐禅寺”。西庐、上庐,唐代的庐州人(地名办?)倒是甚为钟爱一个“庐”字,呵呵。国师岭的传说,兴许未必完备是“扯犊子”,也可能是其来有自呢。
西庐寺庙会(来源 | 档案不雅观止)
随着旅游开拓的推进,多少年往后,或许这些个小而散的自然村落终将拆而迁之。这类传统的、有别于“绿草如茵、别墅如林”的特色景不雅观,或将成为人们新的乡愁。
紫蓬山的林、泉、丘、壑,经纬绮错,织就合肥暨肥西的文脉标志,又岂是肉眼所见识到的那一座憨憨的矮个子小山呢?
山不在高,诚哉斯言!
欢迎读者粉丝加入头条圈子「庐州历史文化研究中央」,更多话题互换和线高下活动等着你~
(此处已添加圈子卡片,请到今日头条客户端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