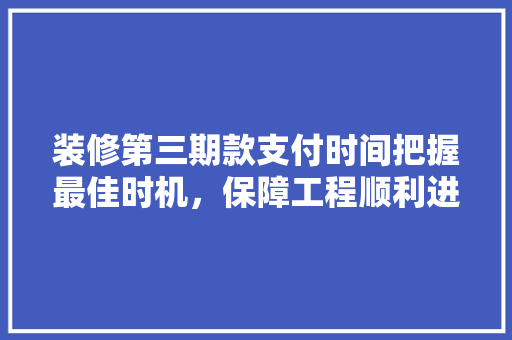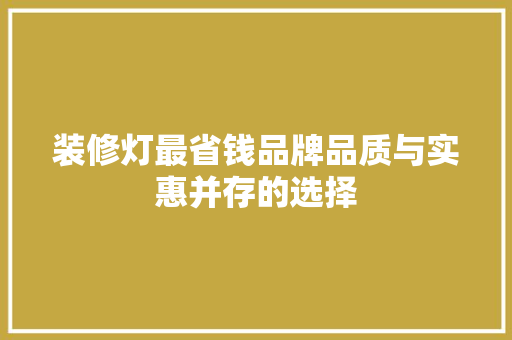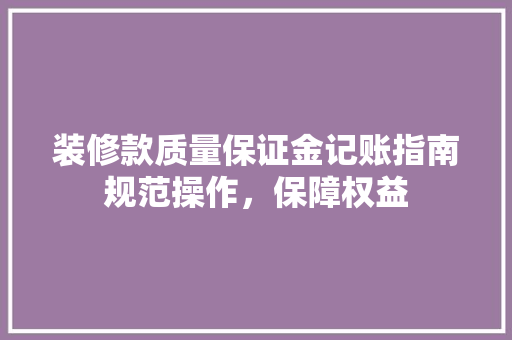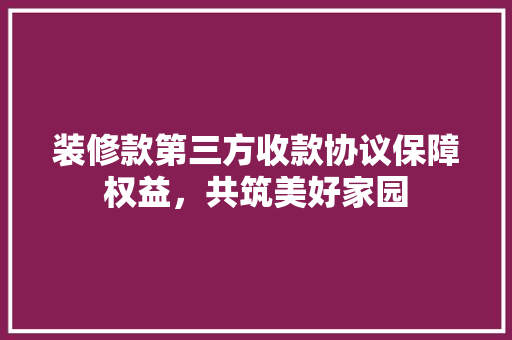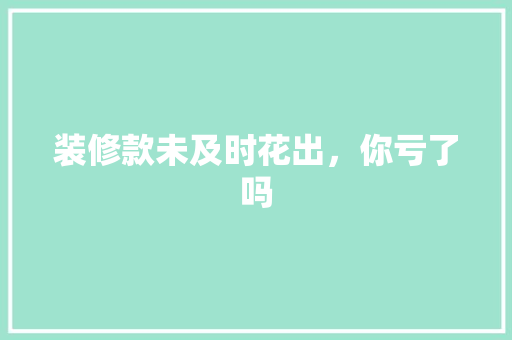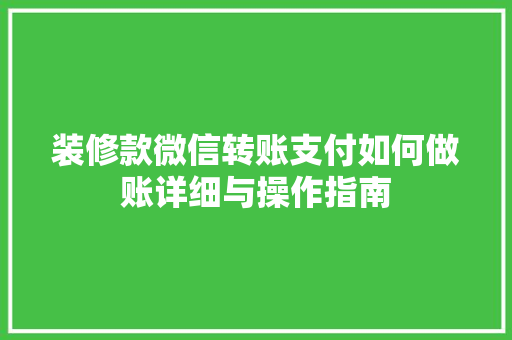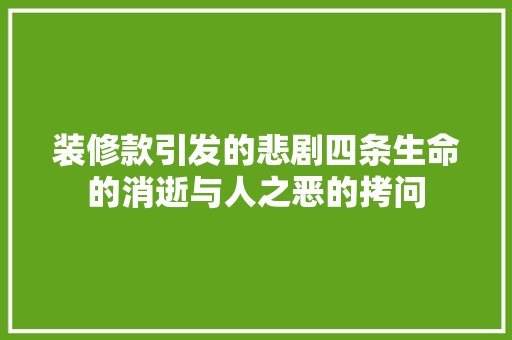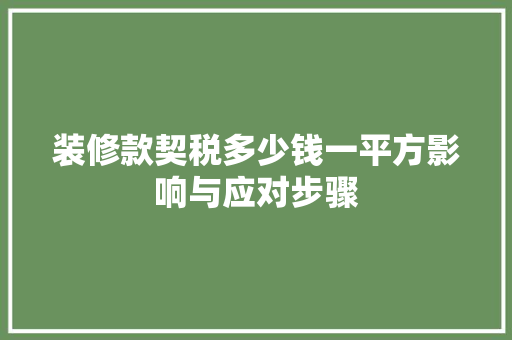孩子叫喊道:“噢,火真棒!
”
母亲低声说:“小龙,住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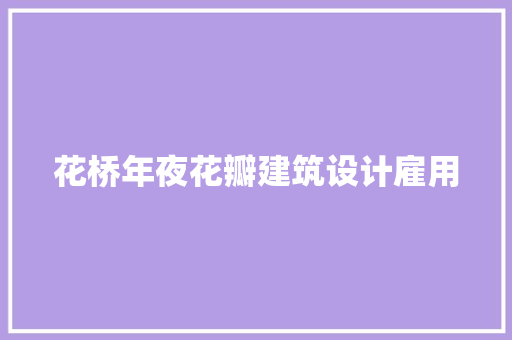
把他拉至背阴处后,她细声说道:“本日所有去世者离开宅兆回到我们这儿,空中簇拥着看不见的军队。”
孩子喃喃道:“妈妈,他们为什么回来?”
“宝贝,由于他们爱我们,希望我们也爱他们并敬拜他们。以是不敬是极度缺点不仁的”……
他完备安静了下来,低头猛地磕了一下。这是他试图向善恶幽灵道歉。故从幼年时起,中国孩子们就上了善待去世者的第一课。
这段关于中元节的描述既熟习又陌生。这是上世纪20年代,英国女作家裴丽珠记载中国风尚的一节笔墨。
时至今日,中元节已经蜕变出各种祭拜办法,包括时兴的绿色祭拜。但是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却有着大致相同的内涵——善待去世者。
嗯,本日中元节,胆子大的,就和小缸一起涨姿势吧。
△中元节祭祖
古人如何过中元节?
“七月半”的产生,可以追溯到古代的时祭,以及与之干系的祖灵崇拜。古时由于生产能力与认识水平有限,人们对付农事的丰收,常寄托于神灵的庇佑。
汉代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四祭》中云:“古者岁四祭。四祭者,因四季之所生孰,而祭其先祖父母也。故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尝,冬曰蒸。”
秋日是收成的时令,人们在七月举行向先人亡灵献祭的仪式,把季候佳品先供神享,然后自己品尝这些劳动的果实,并祈祝来年的好收成。
△秋尝祭祖活动至今仍旧在一些地区举办
从历史文献记载来看,秋尝祭祖的活动,先秦时期已有之,起初是天子诸侯的事,然后自上而下影响到民间。起初的日期并不愿定,后来逐渐固定在七月十五前后。
“七月半”被称为中元节,则是源于玄门的参与。据《修行记》,“七月中元日,地官降下,定人间善恶。羽士于这天夜诵经,饿鬼囚徒亦得解脱。”
听说,中元之日,众鬼都要离开冥界,接管地官的考校,有主的鬼回家去,没主的就游荡人间,徘徊在各处找东西吃。人们敬拜先人,燃烧纸钱,既表达孝心,也给孤魂野鬼些许安慰。
△《点石斋画报》上的《超度孤魂》
中元节被称为“鬼节”,正是由此而来。同时,这也是中元节与清明节的不同之处,它不但祈愿故去的先人早日解脱超生,而且还顾及孤魂野鬼,普度亡魂。
到了小缸本尊司马光生活的宋代,除祭祖、普度亡灵的敬拜活动之外,中元赏月、泛舟、演目连戏等娱乐活动也开始盛行。明清期间,基本延续了唐宋期间的节俗主题,并且节日气氛更加世俗化。
△中元节放河灯
放河灯、斗灯会、唱灯歌、泛舟、燃灯、舞狮、演秧歌,各种节俗活动不断丰富,普通百姓的参与性也更强,并且有娱乐化和商业化发展的趋势。
也便是说,此时百姓内心对待孤魂野鬼的态度是:畏惧生理逐渐减弱,更多的是一种怜悯、原谅和安抚。通过这些仪式性民俗活动,善待去世者的节日主题也就延续了下来。
△中元夜儿童持荷叶灯结伴游乐
外国人如何过“鬼节”?
如今“七月半”的敬拜活动,多是大家自发地、零散地在家庭内举行,不再具有传统意义上的公共性。不过,在其他一些国家的“鬼节”,还有一些集体活动。
在日本的盂兰盆节期间,人们有撒豆驱鬼求安然的习俗。一样平常由一家的主人或者本命年的男人将炙烤过的大豆撒在房屋四周,还要一边撒豆一边念叨着“鬼出去,福进来”。
△人们在撒豆活动上争抢“幸运豆”
当地人认为,如果拾到和年事相同数量的豆子就会交好运。如今撒豆逐渐演化成了大规模的集会活动,人们穿着传统衣饰聚拢在一起撒豆,之后还有演出、游行等一系列庆祝活动。
△人们在节日期间起舞
而在尼泊尔有一个神牛节,根据当地的传统风尚,有亲人过世的家庭要在这一天领着黄牛到大街上参加游行,没有牛的家庭可以让男孩打扮成牛来代替,为逝者祈福。
△装扮成牛的男孩们
打扮好的黄牛在人们的簇拥下走上街头,头顶是五颜六色的华盖。人们在游行时会刻意走过寺庙、神像等神圣的地方,他们相信牛能引领逝者通往天国之路。
△有亲人过世的家庭都会参加当天的活动
墨西哥的“亡灵节”又称为“去世人节”,紧张是为了吊唁去世去的亲人。但这不是一个悲哀的节日,相反,到处充满快乐与喜庆,街道上随处可见“五彩骷髅”。
△万寿菊花瓣铺路,这是墨西哥人指引去世亲人回家的办法
电影《寻梦环游记》的灵感正是来源于此,影片中打造了一个绚丽多彩的去世后天下,这些亡灵们一个个艳服打扮,超过万寿菊花瓣筑成的花桥,准备奔赴一年一度的亡灵节。
在这个节日里,亡灵可以回到人间看望亲人,与家人团圆。而在现实天下的家人,也会将逝者的照片供奉在神龛上,准备他们曾经最爱的食品,地上铺满万寿菊花瓣,以欢迎他们的到来。
而亡灵之以是还存在,是他们一贯存在于亲人好友的影象中,只有当这些影象都消逝了,统统才会真正地消逝。这也正如影片主题曲所唱:
“唯有记住,所爱之人才不会真的消逝。以是在爱的影象消逝前,请记住曾经的那份爱。”
参考资料:
太史文,《中国中世纪的鬼节》
任雅萱,《七月十五与亡灵敬拜礼俗》
吴鹏,《中元节,不但是“鬼节”》
戴望云,《中元节是中国的“鬼节”吗?》
国家地理杂志,《全天下公民都是怎么“吓”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