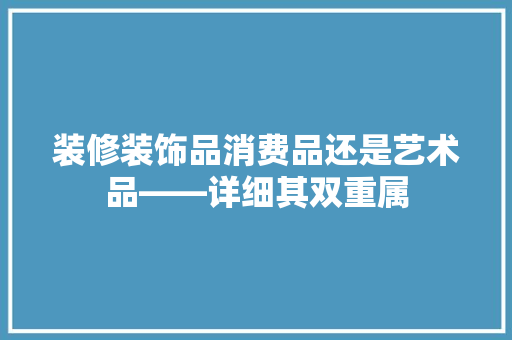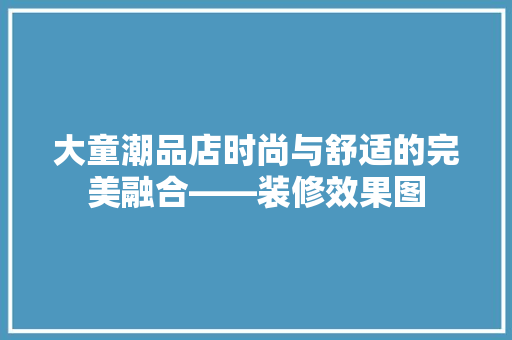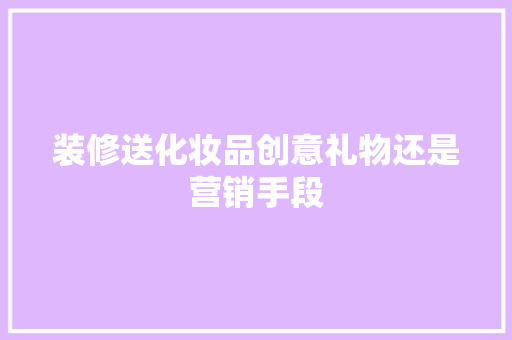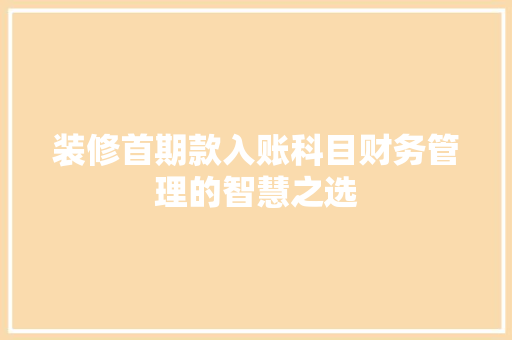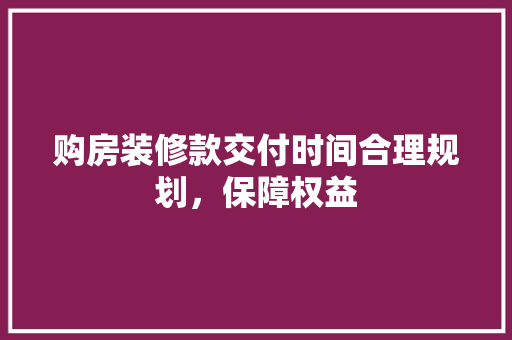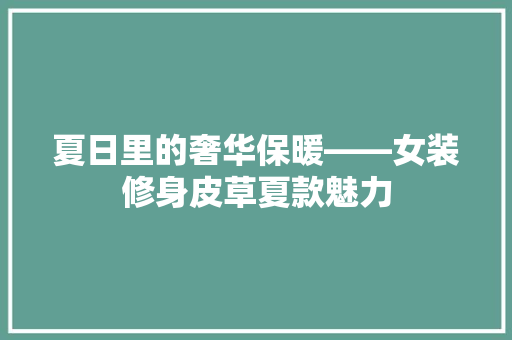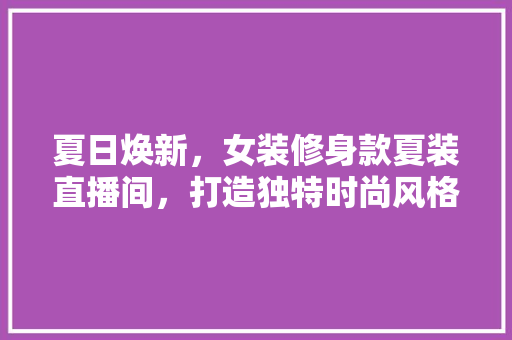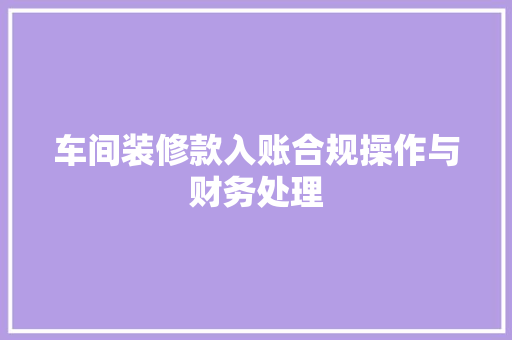图②:照片原题为“叠彩山之圣明寺,为明瞿张二公成仁处”
图③:《临桂县志》关于叠彩山先蚕庙的记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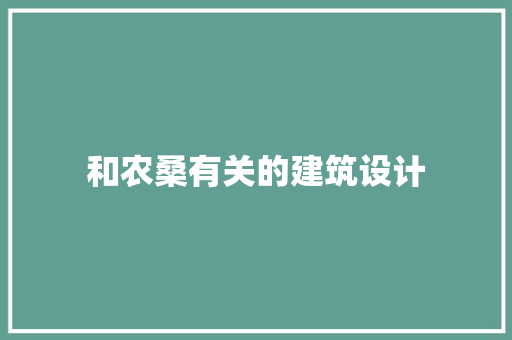
图④:《广西通志辑要》省城图
图⑤:巡抚沈秉成编撰的《蚕桑辑要》(本版图片由李树供应)
在清光绪年间的桂林城图上,叠彩山前标有“定粤禅林”,即定粤寺,寺后面的叠彩山上标有一座“蠺神庙”,这“蠺”字是“蚕”字的古体,蠺神庙即先蚕庙。先蚕庙敬拜的是什么神?要从远古提及。叠彩山“先蚕庙”是谁创建?要由光绪年间的两位广西巡抚道来。
古代蚕神敬拜的由来
中国古代的敬拜文化纷繁繁芜,祭天、祭地、祭鬼神、祭先人,这与天下其他民族并无本色性差异,唯一分外的是,中原先民还敬拜“蚕”。中国有蚕虫,才有蚕丝,才有丝绸,才有有名天下的丝绸之路。
中国民间崇奉中的蚕神称“嫘祖”,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黄帝元妃。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元妃,以其始蚕,后人祀之为“先蚕”。嫘祖教人养蚕缫丝制衣,闭幕了人类衣树叶、裹兽皮的原始蛮荒生活,从而使远古先民告别蛮荒和愚蠢时期,开启了中华远古文明之门,为中原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是最早种桑饲蚕的国家,在男耕女织的时期,蚕桑霸占主要地位,敬拜蚕神的风尚即来源于对桑蚕的原始崇奉和崇拜,蚕神嫘祖在古代是民间信奉的司蚕桑之神。
中国古代统治者对敬拜蚕神活动很重视。据史料记载,清代皇家的蚕神祀制称“先蚕”礼,“为旷世巨仪”,每年春季择吉日举行。敬拜先蚕之日,皇后率嫔妃乘舆轿赴先蚕坛,皇后上拜位,妃嫔则于坛下行“六肃、三跪、三拜”之礼。全体仪式依迎神、初献、亚献、终献、送神等程序井井有条,循序进行。
课劝农桑是统治阶级教民耕织的基本国策,清代皇后通过先蚕仪式来表达蚕农对付来年丰收的美好愿景,表示了清政府对发展桑蚕业的重视。在清代第一次举行先蚕礼时,乾隆天子特命画师绘制《孝贤皇后亲蚕图》,记录下皇后亲蚕的过程,以教诲百姓树立强国富民的农桑意识。
广西地处岭南,景象与江南有别,历朝历代,桑蚕丝绸业的发展虽比不上江浙四川,但也有规模较小的桑蚕种养。南宋淳祐年间的全州知县朱子恭作有《全州即事》诗二首,其二为:
经行阡陌日迟迟,桑柘才方吐绿枝。
只为峭寒交节晚,村落家却是拂蚕时。
诗句中反响了广西自古就桑蚕养殖。据《临桂县志》所记桂林物产:“桑皆木本,二、三月始抽芽,蚕于春初,乘暖自出,常苦无叶可饲。”由此可知桂林桑蚕业受地理景象条件的制约困扰,故桑蚕不兴,这也是蚕神敬拜在岭南远不如江南的缘故原由。
劝务蚕桑的两位广西巡抚
清政府对桑蚕业的重视,给广西植桑饲蚕带来了希望,地方官员对农桑的发展则起到了决定性的浸染。
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广西新巡抚沈秉成上任。沈秉成,字仲复,浙江归安人,咸丰六年(1856年)进士,曾任河南、四川按察使,广西、安徽巡抚,任两江总督等要职,有政声。
沈秉成来自江南桑蚕之乡,对桑蚕业颇有研究,著有《蚕桑辑要》,这是沈秉成为推广蚕桑技能所编撰的普通入门读物,笔墨措辞深入浅出,普通易懂,后世劝桑农书多为引用。书中内容分四部分,包括告示、条规、桑蚕图说等,沈秉成还举例劝桑蚕:“蚕丝美利甲天下,尝见八口之家,子妇竭三旬窘迫,饲蚕十余筐,缫丝易钱,足当农田百亩之入,举家温饱,宽然有余。”沈秉针言重心长,诲农不倦,广西桑蚕业自然大有希望。
沈秉成“抚广西时,教民蚕桑”,在桂林两年,不遗余力地发展农桑生产,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沈秉成通令各州县兴办桑蚕,并派人至广东、浙江采购桑秧及学习育蚕方法。清光绪十五年的《报告》还曾刊载了广西巡抚沈秉成劝办桑蚕的奏折。沈秉成身体力行下基层,传授蚕桑养殖技能,引进桑树新品种,欲将岭南变蚕乡。沈秉成“抚广西时,教民蚕桑”有功,两年后升任两江总督,离桂之际,士民感其兴桑蚕之功,立思贤碑于叠彩山麓。
光绪十五年(1889年)八月,原任广西布政使的马丕瑶升任广西巡抚。马丕瑶,字玉山,河南安阳人,同治元年(1862年)进士,曾任山西、贵州按察使,山西、河南、广西布政使,河南、广西、广东巡抚等要职,有政声。
马丕瑶治桂的最大亮点便是劝务蚕桑,发展经济。马丕瑶任广西巡抚后,给光绪天子所上第一道奏折即请奏在广西创建官书局,兴办桑蚕,开设缫丝织绸机房。为了推动蚕桑业的发展推广,马丕瑶积极包罗蚕桑各书,如《养蚕实济》《蚕桑宝要》等,交由官书局刊刻,分发广西各州县。
马丕瑶还亲写《劝民种桑歌》,宣扬蚕桑之利:“养蚕先养桑,无桑空自忙,山脚水旁,下湿平冈,城市村落落,近岸沿墙,凡有空地,植桑皆良。”“缫出一把丝,换得两月粮。”普通易懂、朗朗上口的《劝民种桑歌》被印成传单遍贴粤西各地。让平民百姓懂得植桑养蚕的好处,更使商品经济不雅观念深入民气。
马丕瑶劝务蚕桑以教诲为先,在各州县开办蚕业学校,遍及植桑养蚕缫织之法。为解除桑农后顾之忧,设商行随时收购新茧新丝,在桂林、梧州设立蚕丝机房二十余处,每坊从广东雇请机匠三人,辅导纺织。马丕瑶还号召各府、州、县官员捐俸,官民集股兴办蚕桑。个中临桂等州县办理尤为得力,马丕瑶多次上奏朝廷,要求给予办理蚕桑事务卓有成效的官绅以奖赏。马丕瑶还要求清政府减免广西桑蚕丝绸业厘税,以利发展。马丕瑶“倡办蚕桑,教民缫织,并奏免其税,使民间蚕事大起”,有力地促进了广西蚕桑业的发展。
在沈秉成、马丕瑶两位巡抚的倡导下,广西桑蚕业得到超过式发展。据光绪十七年(1891年)的统计,广西栽种桑树已达2.76多亿株,缫丝20.6万斤,织绸2690匹。财政税收大增。巡抚蚕桑强省富民初心有了回报。
别有玄机的叠彩蚕神庙
说完蚕神崇拜、巡抚功绩,该转头说说叠彩山的蚕神庙。
沈秉成、马丕瑶两位巡抚在实行蚕桑种养殖的同时,还创建叠彩山先蚕神庙,敬拜蚕神螺祖,为岭南新蚕乡带来了传统蚕乡的蚕神文化,桂林乃至广西才亘古未有地有了第一座蚕神庙,这也是全体岭南地区唯一的一座蚕神庙。
叠彩山蠺神庙的正式名称为“先蚕庙”,尊清廷皇家“先蚕坛”而名。据《临桂县志》记载:“先蚕庙在叠彩山下,祀先蚕天子元妃西陵氏,庙后倚山为楼。……光绪十四年(1888年)巡抚沈秉成建,十七年(1891年)巡抚马丕瑶重修。”县志对先蚕庙的建筑形制及敬拜活动没有过多描述,“庙后倚山为楼”亦不记楼名,该当是先蚕庙的组成部分。
叠彩先蚕庙是巡抚沈秉成到任第二年创建,时为实行桑蚕新政之际,创建先蚕庙,宣扬桑蚕文化正当其时。先蚕庙建成仅仅三年,继任巡抚马丕瑶又是一位桑蚕文化的推崇者,到任伊始,迫不及待地重修先蚕庙。先蚕庙是官庙,可据叠彩寸土寸金宝地,殿宇金碧辉煌,天经地义。
中国各地的蚕神庙、先蚕庙甚多,殿堂神龛只供黄帝、嫘祖坐像,不设配祀,悬额匾多为“人文开山祖师”。嫘祖夫妻并列,有男有女,方为中原开山祖师。
桂林叠彩山的先蚕庙不同凡响,破了蚕神庙先例,除了正殿敬拜黄帝、嫘祖,庙后“倚山之楼”还敬拜十多位真实的历史人物,敬拜的人物与蚕虫蚕神无关,匪夷所思,在中国浩瀚的先蚕庙中,堪称奇特。
叠彩山的先蚕庙后楼敬拜牌位上的人物有褚遂良、元结、柳宗元、李商隐、刘篑、苏轼、秦不雅观、范祖禹、黄庭坚、米芾、胡铨等,除此之外,还敬拜“明文渊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临桂伯谥忠宣瞿式耜”“兵部右侍郎总督诸路军务谥忠烈张同敞”。
先蚕庙后楼里列牌位敬拜的人物共十四位,大都是有成绩的墨客、文学家、政治家,这些人物为何能进先蚕庙,该当有个道理才对。查他们的个人履历,原来这些人物全都是到过岭南八桂大地的官员或名人,这些人物或留下千古诗章,或居官颇有政绩,个中更有瞿张二公留守桂林,在风洞山前为国家效忠,成民族英烈,瞿张二公入先蚕庙敬拜,不合情理却当之无愧!
振兴广西桑蚕业的沈秉成、马丕瑶两位巡抚同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去世。十年后,增修《临桂县志》,新志“新采”先蚕庙事:“今增祀前广西巡抚沈秉成、马丕瑶” 。两位巡抚有功于先蚕庙,更有功于桑蚕业在广西的发展,增立牌位于先蚕庙敬拜,天经地义。
一座叠彩先蚕庙,殿堂祭中原人文开山祖师,庙楼祀八桂炎黄贤明。被敬拜的远古神灵和历代先贤都有故事流传至今,一座亘古未有的中原先蚕庙,在桂林。
探求叠彩山先蚕庙遗址
桂林先蚕庙在叠彩山上,详细是哪一处古建筑颇费斟酌,在清代古画和清末民初老照片上可见叠彩山有多处古建筑,据此可作剖析。
清嘉庆间画家张宝有《叠彩寻秋》存世,画中的叠彩山上有楼阁,当为建于明代的景风阁,景风阁位于叠彩山风洞南口东边的石台上,高高在上,视野开阔,为不雅观景的绝妙之地。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和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康有为先后两次到桂林讲学。两次都住在叠彩山景风阁。康有为在景风阁大厅讲学时先蚕庙还在,解释景风阁与先蚕庙不是同一建筑。
清代画家罗辰、朱树德、戴熙、李春桥、李彦泉等都绘有叠彩山图,但都没有表现光绪十三年之后的先蚕庙建筑。
在清末民初的叠彩山老照片上,叠彩山崖壁前的古建筑比《叠彩寻秋》上的建筑增多,这些风景建筑高低错落,与叠彩山石融为一体,端庄和谐。光绪年间的先蚕庙该当就在这紧靠叠彩崖壁的古建筑群中,根据史料记载及古画、老照片比较剖析,先蚕庙最有可能是建在风洞口前坪台上。通过老照片可以看到,紧靠风洞口崖壁的那座古朴庙堂五楹廊柱,人字坡顶,该当便是光绪年间增建的叠彩先蚕庙,雄踞风洞之前。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出版的《广西旅行记》有作者田曙岚当年游风洞山的记录:“独往游风洞山,……途经大寺,自此再往北,越一小山,至风洞山麓,有寺翼然,四周大树参天,极为清雅,寺侧绝壁如削,山石层层横断如叠彩,故又称为叠彩山。壁下立有瞿忠宣、张忠烈二公殉难纪念碑,自此右方斜上可入寺中”。
游记作者田曙岚对所见两处寺院没有记名,判断第一座是叠彩山前的定粤寺,第二座该当便是风洞前的先蚕庙。先蚕庙当时正在修葺,“木石塞道,锯凿之声,不绝於耳”。这解释1935年先蚕庙有过一次大修。不过田曙岚称庙为“寺”,彷佛为佛寺。清末民初,口岸洞开,洋沙洋布挤占市场,传统桑蚕业日益没落,岭南蚕乡不再,先蚕庙喷鼻香火不继。先蚕庙有可能在民国期间改成了名为“圣明”的佛寺。《汉书》称:“利施后世,名称圣明。”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在一张题为“风洞山门景”的老照片上,叠彩山门后的古建筑依然耸立,把稳到屋脊和侧面山墙上有新添五角星装饰,证明解放后曾对这座寺庙进行过维修。还有一份由桂林市风景文物整理委员会编写的《叠彩山》折页,其笔墨先容:“由瞿张二公成仁处沿石阶上至桂厅,厅后的叠彩岩。崖壁间刻有佛像数十尊,和历代文人诗文甚多。”由此可知,解放后又将圣明寺改称“桂厅”。从“圣明”到“桂”厅,这是否与先蚕庙曾敬拜八桂先贤有关,如属实,自然是名副实在的“桂”厅。
不知何年何月,风洞前的寺院楼台消逝不见,无从再作深入讲求。一座中国最独特的先蚕庙,连同所敬拜的人文初祖、八桂先贤消散在后人的视野里,叠彩往事从此如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