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地儿,肯定没地儿……”车还没到颐和园,张永和就开始头疼停车位。他对停车感到悲观,和妻子鲁力佳出门嬉戏,他总是担心会找不到车位。
不过,他还像年轻时一样,是一个连轴转的建筑师,七八个项目、好几个工地轮流跑,很难想象有哪一天会“安全然安”度过,他说这是一个建筑师的常态。他已经好几个周末没有安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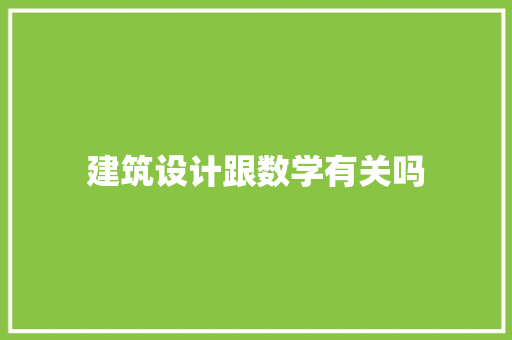
这个夏天的张永和彷佛格外劳碌。2022年8月16日,一场纪念他父亲伸开济的学术研讨会在线上召开。张永和与来自中美两国的专家在直播室里回顾同样作为建筑师的父亲,三千多的不雅观众量对付一场专业的建筑史学术研讨会来说,已经算是“爆棚”。
伸开济是继梁思成、杨廷宝、刘敦桢等人之后,中国第二代当代建筑师的代表人物之一。2022年是伸开济诞辰110周年,研讨会的主题为“中国当代建筑之空想——伸开济与1950年代的中国当代建筑”。“我们本日须要推进的事情,便是从他们那儿开始的。他们想要做的,是如何超越风格的当代建筑。我们本日还是面临这样的问题。”张永和在研讨会上说。
这确实是张永和多年来一贯在追寻的问题:“如何建造中国的当代建筑?”或者用法国建筑科学院院士伍江在研讨会上的话说:“他们那代人受到来自西方和苏联的影响,面临着极大的困惑,到底什么才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建筑?他们有着强大的探索动力,也有着很大的纠结。”
中国第一代建筑师们在新中国成立前紧张落脚于各个私人建筑事务所,到了1950年代,私人建筑事务所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国营设计院。伸开济便是从私人建筑事务所过渡到国营设计院的一代人。而他的儿子,又在1990年代成为了新的一批私人建筑事务所的创办人。
张永和的建筑事务所叫“非常建筑”,位于北京隆福寺附近。二十多人的小团队把不大的空间占得满满当当,走廊上堆满了历年设计的建筑模型。张永和的办公室里放满了他自己设计的小摆件。一张挂毯的设计图挂在办公室的墙上,设计图上是16个空房间,4×4排列,每个空房间的门窗关系、门窗和墙面的透视关系都不一样。“这一看便是建筑师会干的事儿。”鲁力佳说。
接管采访的时候,张永和的精神状态和正式场合完备不一样。饶是一位成名多年的建筑师,他还是无法适应正式的社交场合。“我特殊无所适从,但还得给你们摄影,我也没办法。”他说。
“如何建造中国的当代建筑?”面对这个问题,只管他看起来已经比他父辈的那一代人有了更多的实践,但他难有十足的把握。
回到建筑本身,他的回答就变得简洁、澄澈:“我对建筑学的认识,越是生手越随意马虎懂。就说建筑是干吗的?最大略的,不就盖屋子嘛。一个学生在学校,你到底学不学盖屋子?实在便是这两个问题。”
而他依然要面对大众、面对业主,以及通过媒体让人们意识到什么样的建筑是适宜自己的,这时候他悲观的一壁展露无遗,他说他特殊痛楚,“如果要我选择的话,我选择不说话,我是说话特少的一个人。”
“非常建筑”
1996年,张永和辞掉美国莱斯大学的教职,回中国当建筑师。那时候,市场上还是以大设计院为主,只有几个零散的独立建筑事务所,“独立的建筑实践的根本险些不存在”。他是新中国最早的独立建筑师之一。
张永和说自己是个特殊
萌发回国的动机还在更早的时候。1984年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拿到建筑学硕士学位后,张永和进了旧金山的一家建筑事务所。那是一家偏商业的事务所,他没有韶光做自己喜好的建筑,于是过了一年,他又回到了波尔州立大学(Ball State University)——他的母校任教,此后辗转于多所美国大学。
那是一段孤独却充足的光阴,白天上课,晚上有自己的韶光,画了自己喜好的东西,就拿出去参投一些建筑观点竞赛。他的建筑思想逐步在那段韶光成熟。“那时开始想回中国,奔着正在发生的当代文化去。”中国的当代建筑在改革开放后逐渐开始转型,未来的中国当代建筑是什么样子?张永和想要参与进这个正在发生的时期,“我以为中国的机会除了所谓创业挣钱,还面临当代中国文化的一个催生阶段,建筑师也能在里面做点事情。”
1993年秋日张永和入职莱斯大学,他和妻子鲁力佳两个人到了休斯敦,就想着注册一个公司,把盖屋子的事儿落到实处。鲁力佳站在休斯敦工商局的柜台上,要交7.5美金,注册须要名字,他们就临时编,“要不就叫‘非建筑’?”鲁力佳说。张永和心想,要叫“非建筑”,谁找咱们盖屋子呀……就加了个“常”字,叫“非常建筑”,用汉语拼音注册。现在想起来,张永和以为故意思:“非常不严明地干了一件严明的事。”
实在这个名字已经包含了张永和的建筑思想,“我以为中国当时的建筑过于强调造型,过于怪异了。我想,如果那些是‘正常建筑’,那么我们想建的可能便是‘非常建筑’了。”
后来,在“非常建筑”第一个真正建成的项目“席殊书屋”里,可以找到他的这种“以平常为非常”的建筑思想。当时,北京车公庄的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的楼里要建个书店,朋友先容给了张永和。那个地方原来是过车的通道,后来被堵了起来,他们顺着这个线索想到了书店与城市的关系,把车流人流等要素汇合在一起,用现成的自行车轮子做了“书车”——一个旋转的书架。
当时中国建筑界正受西方后当代主义影响,建筑师们都在评论辩论符号,“实际上便是往建筑上贴装饰”,那时候张永和已经意识到建筑学核心问题的缺失落,1998年他写文章《平常建筑》,开始强调材料的主要性。席殊书屋这个小小的书店室内设打算是他的一种批驳式回应。对张永和来说,建筑学的核心问题是材料、构造、建造与空间。
伸开济生平设计了很多大型的纪念性建筑,天安门不雅观礼台、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但在张永和看来,父亲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建筑,是新中国成立后为普通居民建造的民居。张永和说那些建筑没有明确的风格,“如果非要给它们贴个标签的话,可以叫它们‘基本建筑’。它们考虑的是空间、功能。”
“折衷主义”,这个听起来有点负面的词,被张永和拿来形容父亲的“基本建筑”,“不管是什么古典主义、当代主义,只要它是关于空间的,就可以在建筑里面被利用。当你放下风格与主义的时候,你的建筑也就走向了当代。”在这一点上,“非常建筑”的思想核心与伸开济的非常靠近。
1998年对张永和来说是一个主要的年份。这一年,晨兴数学中央和山语间两个项目落成。有了这两个项目,再加上席殊书屋,“大家以为我盖的屋子和其他人不一样”,业务就逐渐多了起来。2000年往后,“非常建筑”逐渐走出了窘境,张永和和鲁力佳也逐渐成为了连轴转的建筑师,“建筑师便是这样,不是找不到活焦虑,便是活太多搪塞不了。”张永和说。
约请人到户外来
张永和出生的那条胡同,现在叫灯市口西街,原来叫乃兹府,过去是管天子奶妈的地方。那儿离东华门近,夏天吃完晚饭,父母常常带着他和他哥到王府井遛弯儿。一起上碰到熟人,就站在街上说话。这样的城市体验,张永和良久没有碰着过了。
后来,他去了朋友蔡国强的老家泉州,街上还有这种传统,人和人都认得。他感到很倾慕。
张永和就读的波尔州立大学位于一个名叫蒙奇的小镇上,周围是一望无际的玉米地。范例的住在郊区的美国人,生活意味着三个停车位:家一个,办公的地方一个,购物中央一个。有这三个停车位,生活就转起来了。
但是不管是他曾经待过的蒙奇,还是现在生活的北京,都不是贰心目中空想的当代城市的样子容貌——他喜好步辇儿在城市里,如他们后来在纽约住的那个街区,10分钟步辇儿半径里,有五个不同的超市,三家电影院,还有理发店、修鞋店,他以为那才是真正的当代城市,有时候临用饭了,少一个什么蔬菜,立时就跑出去买了——他说这是他的一个“梦”。张永和把这个梦融入了他的建筑设计之中。
有一次,用友软件公司找他设计新的办公楼,他去公司不雅观察,跟员工交谈,他创造,员工们清晨到了公司,进了楼,一天就不出去了,中午就订一个盒饭吃。他以为这样的生活大概对付这些员工并不很空想,他希望设计一个户外空间,约请员工们到户外来。
张永和设计的这个软件园,有着高高低低的庭院和阳台,楼群之间有很随意马虎出入庭院的通道。园区交付之后,他又在不同的时令去不雅观察,他创造这家公司形成了新的“午休文化”。如果景象好,有些员工可以在表面溜达一个小时。“我们并没有能力改变北京的景象,但景象好的时候,实在大家是喜好户外的。”张永和说。
这个项目的成功,让张永和有勇气再往前走一步。在传统的房屋中,屋檐大多只有窄窄的几十厘米,但张永和把屋檐下的空间算作一种半室内半室外的空间。能不能让屋檐变长,让它所遮蔽的空间成为一种公共空间?
在温州医科大学的项目中,他把前后两幢楼的屋檐都延伸到了十米,两个屋檐险些都挨到一起,遮天蔽日,像两把大伞,中间只剩下五十厘米宽的“一线天”,“伞”遮蔽下的空间成为师生们的日常活动空间。一开始,张永和特殊害怕校长问他,假如下雨怎么办?结果校长主动对他说,如果雨水掉下来,那个时候该当特殊有诗意。“遇上运气了。”他在心里说。
张永和用“城市蔓延”来形容中国城市的现状——空间无序,不断成长,范例的特点便是汽车优先,不考虑行人;城市失落去了街巷构成的肌理,只有一栋栋伶仃的建筑,以及装饰在建筑周围的绿化,失落去了市民们活动、互换的公共空间。
1950年代,伸开济提出了他对未来中国住宅区的构想,他主见低楼层、高密度的住宅建筑,反对高层塔楼式住宅。这样的城市构想正渐行渐远。张永和不雅观察到,现在的一个小区,每每500×500米起步,而欧洲的街区大小为50×50米到100×100米之间,曼哈顿是60×120,长方形。
上海嘉定的创意家当基地项目,是他的一个小小乌托邦。他以40m×40m作为街区尺度,高密度地安排了十几幢办公小楼,街区间是10米宽的小街,同时建立了步辇儿系统和人的公共活动空间,创造了一个跟一样平常工业园不一样的“社区”。他不认为工业园是一个只有事情的地方,“人活着的每一小时,都属于生活的范畴。”人们来到这里事情八小时,也须要安歇、吸烟、喝茶、午饭,这都是他要考虑的问题。
大概中国当代建筑的大潮离他所期望的越来越远,但他还是希望有所作为,“我们做的事情更像一个约请,请你多去户外,你要不去,我也没辙。”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开放社区的空想彷佛变得更远了一些,面对南方周末的提问,他说:“不知道什么时候大家可以接管开放社区多一点,那真是一个好事儿。”
张永和是新中国最早的独立建筑师之一,图为他1987年的建筑设计图《水边宅-纵剖面》。 (资料图/图)
建筑中的口语文
年轻的时候,父亲考张永和:为什么一块砖这么大?这个问题他没想过,“就耍小聪明,说一块砖是要能用一只手拿的,其余一只手可以拿瓦刀,工人事情就很有节奏”。他居然猜对了。
这个大略的问题,实在蕴藏了人与建筑的互动:正由于是人在建造,以是砖头只能这么大;而砖头的尺寸一旦固定,反过来又建立起人和建筑的关系。
“以是这不仅是中国的传统,也是建筑的传统。”张永和逐渐意识到,险些任何建筑传统都同材料的体验有关,而建筑当代化运动的一部分内容就意味着材料的变更或消逝。
从这个逻辑推导,张永和以为做设计的出发点是材料和构造,而文化每每不是出发点。“比如北京红螺寺,”张永和脱口而出,“是中国竹子成长区域的北限。”那更北方的建筑不用竹子做材料,是文化的关系还是材料使然呢?他以为根据景象把建筑分为南北,比根据文化分为东方建筑或西方建筑,来得更加坚实、更为可靠。
以是他不喜好建筑中的文化叙事。“建筑的叙事学”曾经在世界各地盛行,“像西方过去几十年的理论,关注或崇尚的便是rhetoric,修辞学的,按北京土话便是‘说事儿’。比如,用某个材料,就说这材料是反响某地文化的,有民间建造的痕迹等等。”张永和以为这样的“修辞”并没有触及建筑的实质。
这样的想法,后来逐渐发展为对“建筑中的口语文”的追求。他到现在还在想,新文化运动推广口语文,而“现在的建筑设计实际上是文言文,由于有一种自我意识”。他认为建筑的当代化和措辞的当代化一样,要做出建筑中的口语文。口语文建筑也是他对“如何建造中国的当代建筑”的一个回应。
“我现在绕了一个圈,又回到建筑本体了。建筑设计要干什么?便是盖一个屋子,得把屋子最基本的部件都搭对了,从材料,到空间,到构造。”这是张永和现在的认知,可是张永和曾经以为,他在南京工学院所受的建筑学教诲,是一件坏事儿。
他是1977年规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的建筑学教诲只教人怎么盖屋子。老师们教得非常详细,一个雨棚不能超过60cm、窗台的坡度是多少,砖头怎么砌,是不是抹灰,要抹多厚。张永和学了三年,从来不谈什么形式、审美、理论,“一概没有”,“老师们怕和意识形态挂钩,不敢讲”。
曾经他也尝遍各种建筑理论、风格,但多年往后,他又把南工学的东西拾了回来,口语文建筑思想的萌发伴随着他的“回归”。
中国的古典建筑走向当代建筑的过程,有一个特定的方向,“这跟当初梁思成师长西席的选择有关系,当时由于某种我并不明了的缘故原由,他调查的、感兴趣的中国建筑是宫殿、寺庙、佛塔,很雄伟、很大,都是有纪念性的建筑。这个方向没有对错,历史便是这样。也可能是当时梁师长西席没有去南方。”张永和说。
梁思成的选择影响了后来中国建筑师,“那些建筑当然很主要,可是对我以及还有一批建筑师来说,江南各地的民居也是一样主要的中国建筑遗产。这些民居要到很晚才有建筑师去关注。有人认为民居而不是纪念性的官式建筑更适宜翻译成当代建筑。以是中国建筑当代化进程不是特殊均衡。”
就和口语文来自底层百姓的措辞一样,民居也是底层老百姓的寓所,它更大略、基本,更适应当代化。“南方的景象使得建筑更开放一些,可能性也多一点。北方的民居,厚厚的墙、小小的窗子,院落生活也不太可能,是有一些局限性。”
口语文建筑一贯是张永和在中国当代建筑中的实践方向,但这条路他还没有走顺。有时他会把设计故意做得直白,但在中国实践之后,他创造如果设计不明显或不张扬,业主会认为他没有设计。他一贯想为中国当代建筑做出有说服力的口语文建筑,“但没做到”。
把教诲体系落实到建筑里面
年轻时的张永和“野心”很大,想搞建筑,想教书,还想办学,传播自己的建筑理念,重新设计全体建筑学的教诲系统编制。
1999年北大找他去办一个新的建筑学研究中央。他那时候已经以为,光教一门课弗成,得建立起一个教诲体系,借由教诲授予建筑实践批驳性,“这样才能培养出有态度的建筑师”。他重实践,在北大的那几年里,带着一帮学生,在未名湖边的一个四合院里,像真正的建筑匠人那样造屋子。
后来他们回到美国——有一天,忽然传真机里来了一个传真:张老师,你愿不愿意来麻省理工当建筑系系主任?
美国建筑学界重理论,鼓吹从理论到实践,而张永和对此并不认同,“特殊反对美国东海岸普遍存在的自上而下的教诲体系,仿佛实践只是为了证明理论。”他以为这直接造成了美国建筑好屋子少的情形,也造成了建筑这行分开了社会。有一次,一个麻省理工的学生先容完自己的建筑设计方案,两个教授就开始辩论,各种大词乱飞,“结果我和那学生根本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
建筑教诲分开实践的问题,“美国和中首都挺严重”,张永和这么多年在教诲一线,“一个建筑学学生学了‘画’建筑已经算不错了,更多的是学会了‘说’建筑,可是对盖屋子很陌生。很多学生学了五年建筑,也没有去过一次工地,这很荒谬。然后大学毕业去设计单位画两年竞赛表现图,再读研究生看上两三年的理论书,这人可能十年八年下来也不知道盖屋子怎么回事,可是他也是一位建筑师。”张永和的讲述中带着过来人的感慨,当初他从建筑系毕业,也不懂详细怎么造屋子,也是步步摸索而来。
在麻省理工的那几年,正好是中国建筑业发展最火热的几年。“对事务所来说,肯定是失落去了一些机会”,但对张永和个人来说,他更进一步确认了自己的建筑思想,他最近的一个大型项目——中国美院良渚校区,完全表示了他多年来对建筑和教诲的思考。
当时美院的校长许江对他说,“你教过书,你来思考一下如何设计教诲体系。”对张永和来说,这是他一贯以来想做的事情,然后再把这个教诲体系落实到建筑里面去。
为了培养通才,张永和发起取消学院和系的划分,对过去的教诲系统编制进行改革。“学生从一个宿舍区一早走下来,食堂吃完饭,去上课,问题是像这种朝九晚五上班式的校园生活,对学生来说是不是一个最好的环境?”
学校部分采纳了他的建议,在良渚校区取消了分系,但保留了学院。和这样的教诲实践相合营,良渚校区被设计成了一个热热闹闹的大空间。
“美术作为一个教诲领域,它跟理工科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做建筑设计都是要动手的,画图是最最少的,还得做模型。”张永和想来想去,学生最好住在作图室的楼上,这样半夜12点钟有了灵感,就能下楼开工;白天假如困了,上去打个盹也可以。
“建筑的目的,本便是创造空间,组织空间。”伸开济在1961年的一篇文章里说。这里的空间没有教室的观点,都叫工坊。学生在工坊里面设计东西,制作东西,现场也可以展览,还可以在里面学习,也可以在里面上课。在这里当然也可以磋商理论,但实践和理论在同时、同一个空间里发生。“大概学生就在这里找到将来的互助者。这是一个更广泛的人际网络,为跨学科的互助打下了根本。”
只是让张永和没想到的是,由于他们这个设计,美院清晨第一堂课八点半,很多学生都八点一刻才起床,也不洗脸,跑到楼下就上课了。“让学生多睡
张永和主持设计中国美术学院良渚校区,学校采纳他的部分建议,取消分系,为学生们将来的跨学科互助打下根本。图为形断意连的校园空间。 (资料图/图)
所幸另一半建成了
张永和在美国教书的时候,建筑学是很能赢利的一个专业。最近两年,房地产遭受冲击。“过去大家都太急功近利了,投契的人多,以是也不太珍惜。该镇静镇静了,真不是什么坏事。”鲁力佳说。
建筑并不是纯挚的设计,它存在于社会之中,与每一个社会变量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一个建筑师,张永和无法肯定地见告业主“若何的设计一定会卖得好”,“由于我不懂经济、市场,也不懂消费生理,我只能从多年的实践履历出发,从人性的角度以及对宜居的考虑,为业主供应一个我们所知最好的建筑答案。”
“中国当代建筑的探索,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第一代外洋学成归来的建筑师开始,如今依然在摸索之中。”伍江在研讨会上说。
张永和险些不会谢绝任何类型的项目,别人找他做什么,他都会说“好”,但无论是什么类型的项目,他总是希望尽可能多地把真正的建筑学知识“塞”到每个项目能有的设计空间里,“虽然有时也做不到。”
“非常建筑”成立29年,未建成的项目约占了一半。而乐不雅观主义者大概会说,所幸另一半建成了。
建筑界的朋友常常批评张永和太理性。他说他基本上是一个善于剖析思维的人。像读文学,他的阅读范围很窄,诗歌他吃不消,激情澎湃的小说也读不下去,他喜好的都是很镇静的作品,像法国新小说中罗伯·格里耶的《妒忌》,这部小说完备是设计出来的,呆板,可是可以清晰地看到作者是怎么把小说搭起来的,“以是我也喜好侦查小说。”
他喜好待在一个很黑的地儿,有一个灯也可以,或者有一个窗,不是很大的窗。由于他最爱干的事之一便是看书,他只希望把他的书照亮,所谓的建筑空间就消逝了。“那是一个最温馨的场景,跟看电影比较像。”
晚年的伸开济彷佛无法理解同样作为建筑师的儿子。他没有办法和张永和对话,也无法理解儿子的建筑,险些每次谈天,父子俩都不欢而散,张永和记得伸开济有次自嘲说:“如果我能读懂他的建筑,可能他就不会获奖了。”
张永和承认他不长于和人沟通。特殊是刚返国那一阵儿,要想在中国当建筑师,必须建立一套中国式的做法,要面对各种寻衅。“比如速率、工艺以及一系列令人困惑的城市条件。”他说。
当时张永和没有在海内事情的履历,刚刚返国的时候,对海内的环境不适应。中国式的人际关系,他以为繁芜。中国商业领域里的话语,他也不是很明白。“如果他以为对方在欺骗他,或者在无理狡辩,他说不出话来的时候,他会急,一下子就会失落控。”鲁力佳说。
和他互助过的樊建川说张永和从不发脾气,爱看书,是个谦谦君子。但是鲁力佳说,他发脾气很厉害,而且没有预兆,溘然就大发一个火。“但他不敢和我发火。”鲁力佳补充了一句。
失落控之后是后悔。有时候他自己也不知道得罪了人。后来,为了不得罪更多的人,变成鲁力佳在前面冲锋陷阵,张永和在屋里做他的设计。
从返国到现在,张永和变革很大。“他确实在逐渐终年夜,但这个过程很长。”鲁力佳说。有一次,一个项目,已经做了一阵儿,业主忽然请来一个南派风水师,于是他这个建筑师也要随着南派大师学习一阵,“看看他到底在想什么,我也给他讲讲我的思想方法”。
他记得贝聿铭师长西席说过的一句话:妥协是一门艺术。“我后来理解这句话,你如果在业主、施工、政府部门那里溃败,你还有什么妥协可谈?每次妥协多少、怎么经商营业,真是一门艺术。如果你这个做好了,你不会离你想做的建筑差得太远,不至于全军溃败。”
张永和爱吃甜食,爱和小朋友玩,爱设计各种小玩意儿,“你不能想象一个没有生活兴趣的人会做好建筑。”鲁力佳说。
这些年来,他依旧喜好逛街,但依旧不喜好在北京逛街,那个关于开放社区的梦大概更加遥不可及。越来越多的人会问他:建筑是不是没有以前主要了?他说他从来也不认为这个问题问得对,但是他也没有能力回答得好。他只是想说,建筑如果做好了,它会冲动人。
南方周末 王华震 南方周末演习生 张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