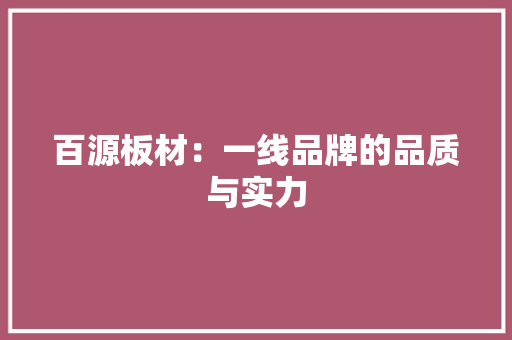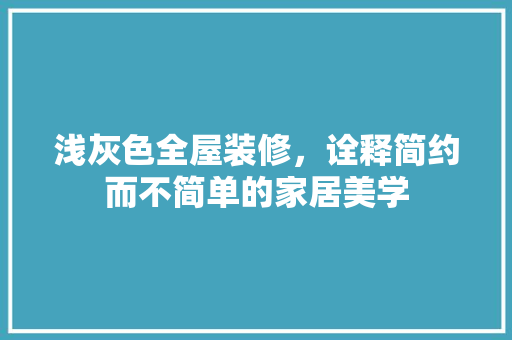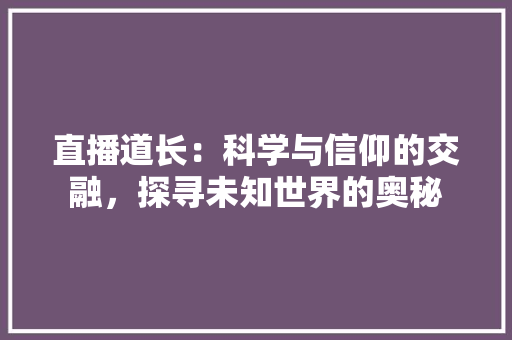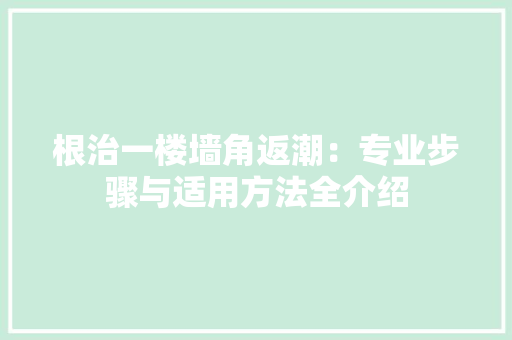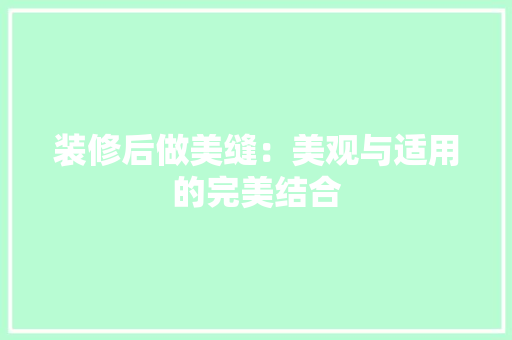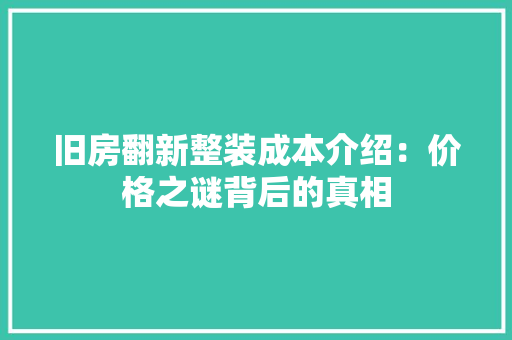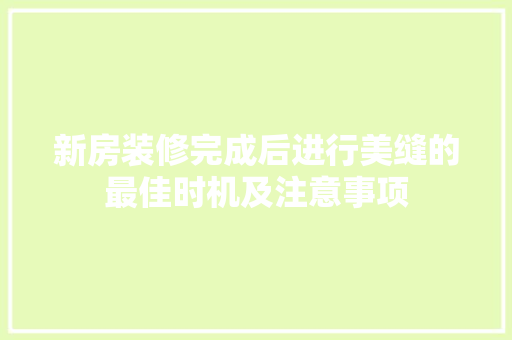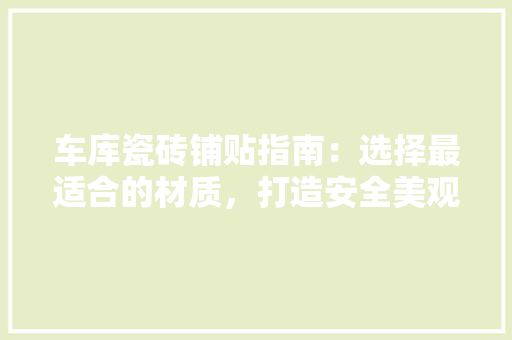《谎话守护人》
作者:(德)埃马努埃尔·伯格曼

译者:景丽平
版本:文景|上海公民出版社
2021年10月
旧天下和新天下
借助笔墨的魔术,伯格曼引领我们在两个看起来各自伶仃的天下间来回跳跃。那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欧洲,一个叫做莫舍的男孩出生在布拉格的犹太正统派家庭。他的出生源于一次不只彩的偷情,却被当整天主的祝福和基督降临般的奇迹。
此时,欧洲正从黄金时期走向分崩离析。“当代”的曙光依稀显现,冲水马桶、电灯和有轨电车的闪亮登场,成了文明降临的象征;但也正是“当代”,为种族隔离、大屠杀和历史上最残酷的战役拉开了序幕。莫舍从没意识到微小的自己正站在人类历史的十字路口。比起犹宁靖易近族立于危墙之下的处境,他更关心自己的命运。
一次马戏演出,让莫舍背井离乡,背弃了自己的出身和民族,从此,他接连卷着迷秘的奇遇和荒诞的遭际。伯格曼天马行空的奇不雅观叙事,将一幕幕波谲云诡的时期画卷垂垂铺陈:对“波斯公主”的一见钟情使令莫舍抛弃犹太身份,加入马戏团,又阴错阳差被警察奉为预言大师,穿梭于穷街陋巷和停尸房,探求凶手的蛛丝马迹;几经波折,他如愿成了“波斯公主”尤利娅的地下情人,引起醋海生波,导致了毁灭性的灾害;他亡命至阴云密布的柏林,化名扎巴提尼,靠着假冒的身份,竟然在党卫军高层中青云直上,乃至被希特勒算作精神导师;可当统统浮名散去,莫舍被打回了原形,成为犹宁靖易近族苦难的经历者和见证人……至善、至恶,至美、至丑,至尊、至贱,都浓缩在了莫舍前半生的奇遇当中。
与昨日天下的繁复丰饶形成光鲜比拟的,是小说中的另一个天下——二十一世纪初的美国加州,一个扁平而乏味的新天下。小男孩马克斯为了让感情分裂的父母重归于好,想找魔术师“伟大的扎巴提尼”来施展爱情魔咒。马克斯曾以为天下充满奇迹,真实的经历却让他失落望。他发觉生活的本色是浅薄和无聊,魔术师根本没有邪术,爱情仅出身于草率的一夜情,孩子的出生是一个无法纠正的缺点,每个人都不愿为自己的行为和举止卖力,就连食品都难吃得要命。伯格曼故意将新天下高度漫画化,令崇高和神圣在此无弹丸之地,我们乃至难以相信它与细腻、丰硕的旧天下之间存在关联。二十一世纪无疑孕育于二十世纪,新天下无疑孕育于旧天下,可两个天下就像希腊神话里的黄金时期和黑铁时期那样相去甚远。
两个时期的相遇
两颗看似相互隔绝的星球之间,总是存在着看不见的引力。这引力在小说中化身为两个连接新旧天下的老人,魔术师扎巴提尼和马克斯的奶奶罗塞尔。他们是来自昨日的幸存者,从大屠杀去世里逃生,他们的灵魂曾经立体而丰沛,却也在从旧天下到新天下的旅程中被残酷而且不可逆转地改变了:魔术师从刚毅、敏感的少年莫舍,堕落为昏聩、油腻的“色情狂”老头儿;罗塞尔由人见人爱的小姑娘、人性至善的活纪念碑,跌落成喋喋不休、大家嫌恶的老太太。在新天下里,他们被遗忘,被摈弃,变为一道无人乐意碰触的伤疤。人们只想埋葬他们在旧天下的遭遇,遗忘“犹太人大屠杀”“集中营”留下的黑洞。
埃马努埃尔·伯格曼。
对此,过去的少年莫舍、现在的老扎巴提尼有着复苏的认识,“他和他们不一样。他的经历,不论是战前的还是战时的,都让他变成了一个被流放者,人类的大家庭里已经没有他的位置了。”在活着的人当中,彷佛再没有人能够理解和收受接管他的经历。他人生中唯一一次吐露集中营的原形,是在吸食迷幻药之后,他对其他瘾君子讲起万人坑,讲起尸体和其散发的甜腻腐臭。在场的所有人,都自诩为试图打破人类精神和肉体极限的冒险者,可他们只听了一个开头,就呕吐不止,抱头鼠窜。莫舍的存在其实是刻在人类生活的幸福和确定性上的疮口,他那无人理会的痛楚、仇恨和绝望便是人类同胞给予他的惩罚。他只有保持缄默才能苟活。
罗塞尔奶奶却不肯沉默。她喋喋不休地讲述,仿佛她的生命永久困在了集中营。她对每一个人讲述自己被屠杀的亲人,讲述她如何从象征去世亡的“箱包工厂”找到通往自由的生路。人们以冷漠回馈她的讲述,家人躲着她,孙子马克斯认为她的经历比干涸拍浮池里的枯叶还没意思。
大屠杀仅仅过去了几十年,人们用了三代就抹除了历史上最腌臜、最残暴、最该当被铭刻的影象。种族灭绝、集中营、普遍性的恶,都从人类集体影象里消逝了。然而,《谎话守护人》通报给读者的一个真谛是:没有任何东西会凭空消逝,即便被人刻意粉饰、遗忘,也会一贯存在。一如谎话背后总有原形。
我们以为自己目睹了消逝的魔术,只是由于眼睛受到蒙蔽。
消逝魔术与人性的奇迹
在小说里,“消逝”既是莫舍善于的魔术,也是他的一种生存策略。初出茅庐时,他肃清了自己的犹太身份。陷入连环凶案和桃色轇轕时,他从马戏团逃遁。他善于消逝魔术,还找大师定做了一个行李箱,有了它,莫舍能让任何人隐形。
但这统统,实在都是障眼法,都是谎话。它能让人们对原形视而不见,却不能让原形彻底消逝。犹太男孩莫舍变成波斯王子扎巴提尼,他犹太人的身份却不会真的消逝。扎巴提尼继续了莫舍父亲、犹太拉比的布道手势,把犹太教义中的神秘主义抄袭进自己的预言演出。他的成功源于他的犹太根基,对此他毫无知觉,乃至以雅利安人自居。目睹犹太人遭受伤害,他袖手旁观;希特勒向他寻求帮助,他没有进行任何旋转民族命运的考试测验。他和无数成为纳粹帮凶的普通人一样,背负着平庸之恶,并因此一韶光青云直上。可是,他犯下的罪同样不会消逝。他姑息、纵容的恶终于将他反噬,拖入深渊。
所幸的是,身处地狱,莫舍的人性和蔼良没有消逝,反而从懵懂中觉醒。在集中营,他用演出魔术的箱子,变“没”了小女孩罗塞尔。当然,小女孩也不会真的消逝。靠着魔术创造的一线活气,她找到了通向自由之路,有机会享受漫漫人生。在她心里,莫舍施展的这场伟大的逃生魔术从未落幕,她穷尽生平一遍各处讲述这场魔术,即便没有听众,即便没人理解。她的影象因讲述而流传,她的讲述也抵达了终点——在莫舍生命的末了时候,他因她的讲述,才得知自己创造过无与伦比的奇迹。他的魔术演出骗过了去世神,在绝境里无中生有地首创了一条生路,让小女孩幸运地成为了全体家庭唯一的幸存者。而她的生命又生发了七个新生命,创造了七段完备不同的人活门程……
消逝魔术最精彩的部分不是某件东西消逝了,而是消逝之后,它又重新涌现。事实上,《谎话守护人》这部小说也可以看做一场消逝又重现的魔术。在故事里,原形被遮蔽了,又被再次发掘;影象蒙尘了,又被精心擦亮;过去被掩埋了,又被重新召唤。对付残酷的战役和灾害,人们可以选择视而不见,但究竟,每个人都不得不回溯生命的源头。就如小男孩马克斯,只有在奶奶罗塞尔“想当年”的讲述中,在魔术师扎巴提尼重现过去的魔术里,才能领悟到自己生命的代价。那是比漫画书和比萨饼、父母打嘴仗闹离婚、生日宴会大出风头更宏伟的东西。它伏线千里,从莫舍的生命、奶奶的生命绵延到马克斯的生命,从七十年前的集中营流转至本日的加州。它牵引着马克斯从自己的小天下走向自己的民族和其背后的历史,并且,在他面前展现连去世亡和最严厉的暴行也无法打垮的勇气与肃静。
马克斯称它为奇迹。
而我以为,那是天下在无尽的荒诞、残酷的间隙,展现出的一道仁慈的光。实在人的生命就像野草一样,无论经历过多少次火烧和践踏,只要这道光乍现,生命便能捉住稍纵即逝的机会,发达地成长。这便是生命的魔术——
“只要存在,只要活着,就已经是一种祷告。”伟大的扎巴提尼如是说。
撰文丨刘丹亭
编辑丨宫照华,肖舒妍
校正丨薛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