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百年前,林徽因和梁思成带领着中国营造学社团队开启了一段风尘仆仆的古建保护旅程。动荡的时局中,上千处历史遗构被重新创造,一本本风雅的测绘图,留下了历史沉重的身影。在本日,非遗传承、古建活化已不再是新话题。当每一个普通人都开始懂得欣赏那些曾经被掩埋在尘埃里的非遗之美时,专业的建筑师设计师们已然将“非遗和传统”作为一种设计本能。
他们“修旧如旧”,尽最大可能去保护古建原貌;他们“以旧传新”,将非遗技艺融入到当代设计中;他们“新旧相融”,试图探索出一种更适宜当代人的非遗生活办法。如今的建筑设计界,非遗不再是一时的流量元素,而是每一位设计师都在负责思考的文化创新力。只有当古建、非遗与当代共建出一种更闲适、适宜我们的生活办法,古建或许才是真正的复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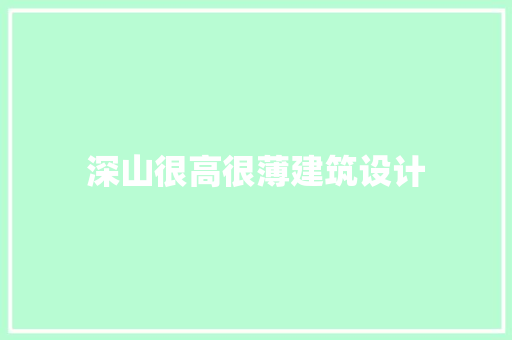
在万溶江畔的乾州古城中,原有一处当地木工世代传承实践的场所——“天工居”。在中国古代,真正为正史所记录的建筑营造技能实在很少。大多依赖历代匠师们以口授和钞本的形式代代相传。而在这座已有4200多年历史的吉首乾州古城里,人们世代信奉着天工鲁班,以口传技,以心营造。绵长的历史,以及优胜的地理位置,造就这座古城在湘西文化中主要的地位。
然而,时至今日“天工居”随着木工技艺渐微而早已变成荒废的老房。匍匐在杂草横生中的是曾经残酷的湘西文化,更有着当地人们复活文化的决心。
在当地文旅的支持下,看重传统与细节同时有着广泛国际视野的大不雅观建筑被约请来到古城,希望将原来荒废的老房建筑修缮更新,在植入具有活力的当代设计符号的同时,保留下这座浓缩了传统穿斗式木构造的“天工居”。
初初来到老房,年久失落修的一砖一瓦只管满是灰尘,但透过木墙、木地板、轻石砖、瓦面屋顶,设计团队依然感想熏染到当地浓郁的湘西民族建筑特色。
对付这些埋藏在历史长河中的古建来说,他们或许只是旧了,并非损失掉生命的“去世亡”。如果最大程度上保留原有历史痕迹,“修旧如旧”才是古建修缮更新的核心原则。在大不雅观建筑看来,这一原则是不可动摇的根本,只有在尊重古建的根本上,才能让那些蒙尘的古建真正复活。
以是更新之始,建筑团队最先做的便是以保护为主的修缮。从全体建筑院落的空间布局到一砖一木,建筑师只管即便保留下它们原有的样子容貌。
带着斑驳痕迹的古木,泛着油亮的光芒,纵然在暗夜中也能惊现出一种历史回眸的目光。庭院尽头的建筑损毁严重,门板夹层栏杆均已不存,夯土砖木多年来饱受雨水侵刷,早已涌现塌陷征象。只管如此,团队依然不想以新充旧,而是找到湘西当地熟习传统工艺的师傅匠人们对建筑进行精心修复,以此保留历史建筑的真实元素和历史风貌。
历史文化的代代相传并非只是守旧如旧。当越来越多古建开始清醒、复活,它们与当代人的间隔绝非只是隔着韶光长河的两岸遥遥而望。为古建置入更适宜当代生活办法的元素,才能授予它们时期的活力。
许多古建院落在翻修成民宿时,会看重保护建筑的根本木构造和每一处零构件,以老空间为容器,纳入一些既古朴但同时适宜当代人起居坐卧的家具。只管“天工居”并非因此民宿为目的的改造,但建筑团队依然在空间中融入符号属性非常光鲜的设计元素,以此极具张力的视觉性,强化了这座院落终极成为湘西非遗展陈活动空间的创新属性。
一抹极具象征意味的“红”,即是中国人独占的文化图腾和精神皈依,更代表了传承与创新,新旧共存。当一个为人所惊奇的赤色玻璃盒子被置入原有空间时,历史与当代的隔阂自此被冲破,古建复活也被授予了更多可能性。
几代人熟习的老厂房影象,在郁郁葱葱的林荫中再次复活。位于四川省成都邑成华东区东二环外侧的原老工业区,有一片凑集音乐、美术、戏剧、拍照等多种文化形态的东郊公共园地,高密度的山林覆盖度,让这里不仅仅是当地市民熟习的工业区,更是城市之中难得的自然疗愈地。
2020年,来清闲行建筑的主持建筑师温钦皓在这片工业旧址上新建“董小姐与马丁公共艺术空间”。少见的桶形单元,在东郊公园的东大门入口出自然围合出线性路径空间。不经意地溜达个中,穿过一个又一个象征老厂房的圆筒“烟囱”,历史的影象伴随着林荫与阳光,再次重现在人们面前。
对当地居民来说,这处少见的艺术空间形态,不仅是旧时期与新生活的结合,更浓缩了当地民间代代相传着的“竹编”非遗艺术。早在明清年间,盛产竹子的川渝地区在总结民间竹编技艺的根本上,将竹篾越划越薄、竹丝越劈越细,用具编织得越来越精细。逐渐地发展出清秀古朴,且风雅到令人惊叹的竹编艺术。
建筑师以“竹编”作为分外材质参与空间,使得建筑本身奥妙地融入到一片浓郁林木之中。当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精密的竹编表层时,散发出一种老川西坝子才有的独特生活技艺。同时科技膜材、净水陶砖、透明亚克力等材料的利用,也为建筑增加了一抹未来感的当代城市时尚活力。轻盈的竹,踏实的砖,在刚柔并济之间老城的文明开始复活。
傍百年步道而建,隐于林海之中。当一个人肯跋山涉水来到这片人烟尚稀的山岭之地时,他不仅与自然更近了一些,还在不经意间敲开了叩响了历史。
这座隐蔽在重庆市沙坪坝区曾家镇虎峰山村落的民宿,占地面积约有800平方米,遥遥望去像是被遗忘在山林中的一块瓦片,坐享万里的浓郁绿色。但在优胜的自然地理环境之外,民宿所在的虎峰山村落是当地名副实在的人文村落庄。
早在北宋乾德年间,虎峰寺便兴建于此,几百年间佛寺历经岁月现而今只剩下几座百年残佛,独身只身孤影地隐秘在山顶的荒草之中之间,但依然是当地人文精神的厚重缩影。伴随着周边大学城的发展,这处好山好水,吸引了许多来自川美、重庆大学等高校艺术家纷纭“落户”,事情室、画廊、美术馆、茶舍和民宿依山而建,可以说籍籍无名的虎峰山村落是一处集自然与人文的新式桃源村落。
建筑于古寺下的这所民宿名为“寺下山隐”,原基址是当地一座残破废弃的夯土老房围合而成的三合院。
建筑团队为了更好地传承西南地区特有的山村落村落庄的文脉与肌理,新建的建筑也通过掌握体量的尺度与围合,尽可能还原了基址过去的院落空间。同时,民宿与山区主道路的交通连接,仅靠一条一米多宽的陡峭石板步道作为连接,这种设计师和民宿主理人的共同坚持,是他们对原有历史园地的尊重。
只管爬山而行变得略显不易,但正是一步一行让人们能靠近历史。当人们踏着青石板,伴着清风掠过竹林的声响,途经一湖碧水后看见路边那片朴拙的夯土老墙,便晓得“寺下山隐”就在面前了。这像是一场自然和历史的精神洗礼,使得抵达的过程充满仪式感。
整座民宿完全继续了西南地区民居的传统夯土工艺,在保留老夯土墙的同时,融入经由新工艺改造后的夯土形式。同时极具当代感的钢构造和玻璃材质的融入,与朴实的夯土质感形成强烈的视觉比拟。恰到好处的一新一旧,无不表示着建造材料从传统向当代、从旧到新逐渐过渡的巧思。
当隐蔽在草丛中和屋顶上的灯光,逐一亮起,这座新老结合的建筑像是山林中的萤火虫,带着希望的光亮,在潜移默化中以人们最随意马虎接管的办法,通报着那些未曾逝去的老文化。在民宿的底层,设计师还专门搭建了非遗展厅,与无边池塘的乡间书屋相连接。他们希望每一位到访“寺下山隐”的客人,都能更自然地感想熏染非遗的文化魅力。对付这片上百年历史之久的山岭村落庄来说,自然是躯壳,文化是永久无法忘怀的灵魂。
编辑|Kiki
笔墨|KKC
设计与图片供应|以上设计事情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