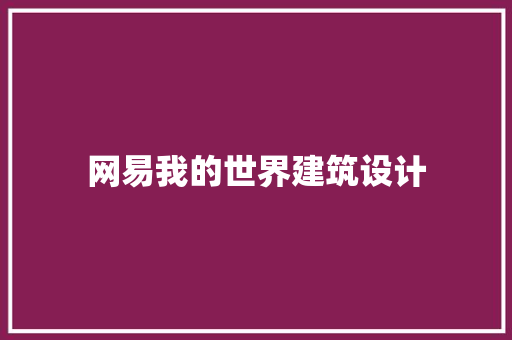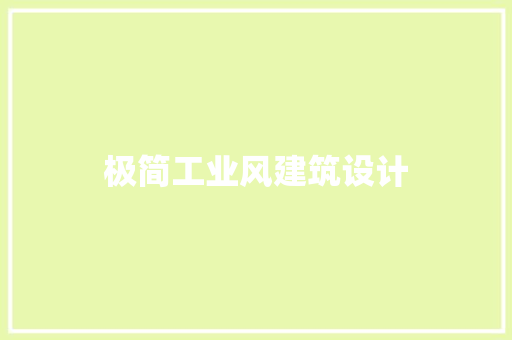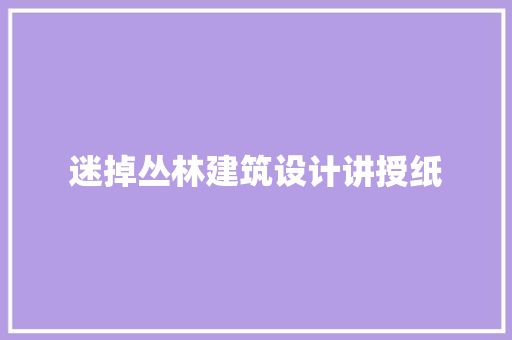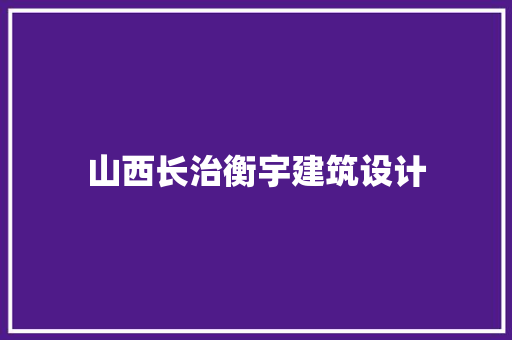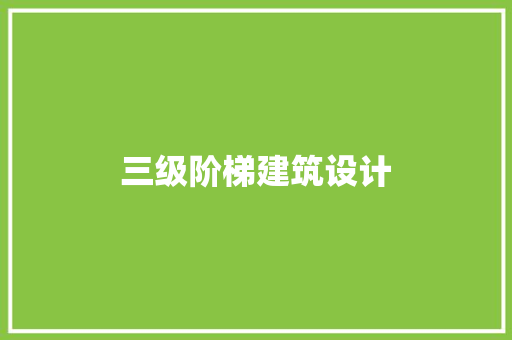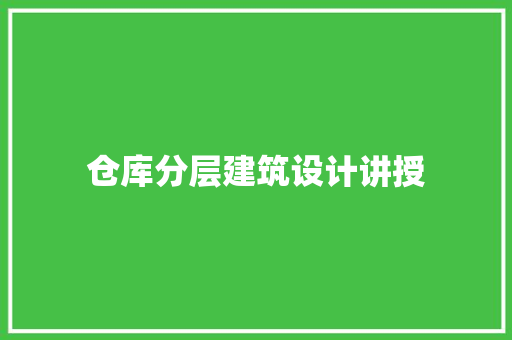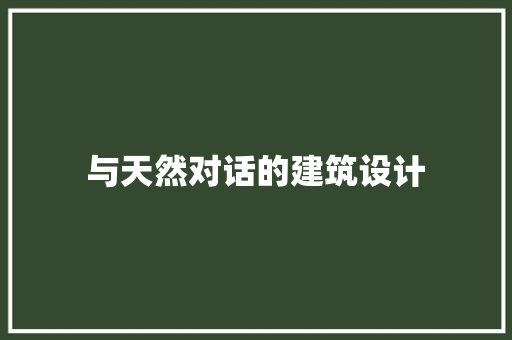章明(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方案培植建筑系副主任教授、同济原作设计事情室主持建筑师):
章明

从城市有机更新,到正在进展中的一江一河操持,可持续的主题对我们来说非常主要。“丘陵城市”是我们对高密度人议论况现状思考和未来发展方向的一个构想,我们将城市中的空间征象放回到人的意志和行为的语境当中,对城市空间在文化、生产以及管理层面逻辑进行一个重新的梳理,建立起与韶光、空间与人的行为相对应的所谓的回应性体系。我们在城市修复过程中思考,城市是不是可以像丘陵一样?丘陵有它的特点,坡度比较平缓,起伏连绵,气运通畅,水量丰沛,风景互异。这种状态能不能规复或者参与到高密度的城市当中呢?我们的城市是不是可以像丘陵地貌特色一样在形态上起伏平缓,以密度换高度?
“绿之丘”
以“绿之丘”这个项目为例,这个项目不仅是一个单体项目,它实际上融入到全体杨浦滨江建成环境的再生体系当中,我们在空间层面希望它能够衔接滨水公共空间与城市腹地,在建筑层面按照对非回应性技能体的自然化的过程,使它成为丘陵城市关于“微变、优柔、漫游”的一次践行。
我们称为“优柔之丘”,便是对园地脉络的回应。这个回应该中是各种资源与功能体进行复合和叠加,是各种机制的协同与互助,这种机制的协同与互助不是单方面建筑师的事情,一定是与业主方、政府同谋的结果。我们希望在城市中能够有更多的交界和更少的边界,包括根本举动步伐也不再成为城市的背面,而是走向公共空间、开放空间,让公共做事举动步伐变得触手可得。回到建筑本身,我们称这个建筑是被“减少”出来的建筑,是做减法出来的建筑。减少之前是30米高、40米宽、100米长的大体量建筑。这个体量与防汛墙之间的间隔不敷10米,对公共空间形成一个比较大的逼仄感。从功能上讲,它适应当年的功能的须要。可是在当下,当杨浦滨江的公共空间要还江于民,从“生产时期”走向“生活时期”的时候,它的功能开始发生变革,以是我们首先便是对体量进行讲明。体量的变革是对公共空间的回应,也是基于丘陵趋势平缓、微变状态的改变。
“减少”出来的建筑
我们提出“微变之丘”,是对韶光脉络的回应。就像丘陵地貌般经历的岁月的沉积和风雨的雕琢,缓慢地进行演化,以是它不是一推了之,不是一拆了之。城市空间特色一种类似韶光坡剖断面的办法和图式呈现出来,既有的与新建的,完成的与未完成的彼此交织,叠合成一个浑然的整体。
末了“漫游之丘”是对行为脉络的呼应,“丘陵”许可并鼓励人们自由穿行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像我们先人一样在连绵的丘陵间栖居与游牧,我们希望城市是一个促进身体移动的系统,地面拥有最大的延展性担保人的活动从地表一贯蔓延到屋顶,从河岸蔓延到桥梁,从公园蔓延到宅间,相互勾连的穿越性的场所形成弥漫式的立体的漫游路径。
“绿之丘”
我们所提出的是一个新与旧的原谅体系,是多种功能的原谅体系,是多种行为的原谅体系,它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所谓制度化的空间,而是不断发展的体系,是自然的行为,建造的行为,人的行为的和谐统一。我们鼓励这种互助关系不断发展。
童明(TM STUDIO建筑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方案学院教授):
童明
前面章明提到建筑该当以更加互动性的办法进行思考,必须对园地、文化、景象、材料等成分要做出相应的呼应。我想提出的是建筑师的社会任务,而且是“现在时”(architecture is responding to)。加了“现在时”后,它的很多含义变得不同,由于在很多的工程项目中实际上是相对断裂的,甲方、业主、设计方、做事的工具、利用的市民这几方都是相互分离的。“现在时”更多的是一个寻衅,对付学科、方法和思想都是一个寻衅。
2009年我和张斌参加过王澍的杭州中山中路改造项目。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小的屋子,这个小房子是比较早期的考试测验,用“现在时”来作为一个建筑设计。所有的建筑设计的方案都是来自于现场,乃至包括材料、做工方法都是取自于现场废墟的一些痕迹又复原到新的建筑形式上,现有留下来的历史片断形成再生的互动关系。
社会的含义指向的不是物,不是一种被动式的环境,而是指向“人”,是一群在不断变革的人。面对这一工具,如何能够跟它形成一个相应的互动并且来做建筑设计?我们在上海贵州路的更新中便是以这样一种办法思考。很多的项目或者思考都是针对环境、房屋。我们更多把聚焦点放在人上面,思考里面的居民如何能够从我们的项目中间能够得到更好的一种提升性的感想熏染。我们从政府资金里面把项目拆成12个很小的部位,把它分别嵌套到环境当中,比如说原来黑乎乎的门洞,通过大略的框架把内部空间通亮化;原来弄堂口的理发店保留下来,成为市民喜好活动交往的场所;原来居民用来倒马桶的厕所改造成画廊。更多的着眼点在于怎么通过一些建筑设计为现在的居民带来一种提升性的感想熏染和收益。
贵州路109号更新项目
我们在浦东曾经参与过小型的社区更新项目。在金桥镇,它在90年代形成了很多的居住区。这些居住区经由20多年往后变得比较迂腐,当时的城市方案留了很多的缺憾,比如小小的三角绿地本应成为居民活动的场所,但是由于方案的缘故原由被放到一个边角落,它的利用效率很低,成为了一个“去世角”,在日常生活中间没有太多的居民到达这里。我们做了一个事情,意图能够把这几个区域串联起来,由此做了一个非常“奇形怪状”的小建筑。这个小建筑能够使得原来碎片般的园地和举动步伐成为一个整体。它是全体园地中间最不起眼的地方,通过这样围墙或者边界的提升和改造,既起到领域分割的浸染,更多的是交汇性的场所。实际上它是为全体社区形成连接性的纽带,把这些花园和社区活动中央以及到表面的小广场和居民所活动的内容都给连接在一起。
这些反响出我们事情室近两年在磋商的问题,可能也是在做建筑设计中间所面临的最有寻衅性的问题,你的建筑如何能够跟一个社会能够发生互动,尤其是今年发生太多的事情,我们充分觉得到社会的变迁,原来环球大家庭的观点又要面临新的格局和新的寻衅。我们的建筑能否在这个环境局势下对全体人类,全体社会做出故意义的事情,我认为这是有可能性的。
刘宇扬(刘宇扬建筑事务创始人主持建筑师、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方案学院复合型创新人才实验班设计导师):
刘宇扬
我的背景比较繁芜,我在中国台湾出生,在美国学习建筑学,在中国喷鼻香港帮忙过RIBA的事情,绕了一圈末了在上海做建筑师。我的实践也很难被归类,很难一句话讲清楚,和我的背景一样,在很多的国家和城市留下过足迹。项目类型比较杂,过往十几年在上海实践的轨迹大概归为四大类:教诲办公、文化文旅,城市更新以及近几年景长的景不雅观根本举动步伐。
有一位建筑师的一句话特殊触动我。在20世纪上半叶一位非常著名的意大利建筑师Ernesto Rogers讲过“从汤匙到城市”(from spoon to city)。他描述米兰建筑师在当时的事情状态是可以在同一天设计一个调羹、一把椅子、一盏灯以及一座高层。某种意义上他实在表达了建筑师能够跨的领域重点不是它的类型或者尺度,而是思考的办法,这一点一贯影响着我们面对每个项目的方法和态度。
在海内各种各样的项目和机会很多,在自己事情室实践的过程中,我们梳理出大概四个类型:
一是历史文脉。我们从一种当代设计美学的办法看待历史建筑的改造以及背后必须要有的开拓的模式。不管是城市里的工业类型,创业文创空间的改造或者屯子里面,不管是私人开拓佳构酒店或者更有社会学意义、城市学意义的乡建,它归根到底都是在回应文脉的主题。
南京路步辇儿街的行人做事亭
二是社区营造。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事情创造出富有社会创新与民间活力的原谅性的社区。从前南京路步辇儿街的项目——12个行人做事亭一贯到现在仍旧被利用,这是最大的可持续的策略。
三是聪慧未来。2014年带领兰州大学建筑系在上海事情坊做了一个70万平米综合开拓的研究,在浦东做了一系列的聪慧办公楼区的项目。
四是开源协作。在个人实践中我最看中的一项是事情方法,开源协作。我们认为真正的好的创意不可能来自于一个人,初步的观点、设想、勾引可能来自个别,但是把一件事情完全从头到尾来很好的落地,它的创意一定是阶段性、过程性、积累性的,我们希望更多的借由同行,从我们干系的一些领域专家能够一起共同谋划更好的办理方案。在近几年我们参与到一些比较大型的项目都是用这种办法。
柳亦春(大舍建筑事情室联合创始人、首席建筑师;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方案学院、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客座教授):
柳亦春
本日我演讲的题目是“与废墟共同事情”,想借三个在上海黄浦江边煤码头的改造项目表达我对可持续的理解。少拆东西便是最大的可持续。少拆就意味着一种保留,这种保留也是文化的一种可持续。最近七八年我在全体黄浦江边上做了很多的工业建筑改造项目,在改造项目当中逐步意识到废墟、特殊是工业建筑作为城市曾经的构筑物,在损失它的功能往后仍旧具备的代价。
龙美术馆
龙美术馆在原来的北票码头的根本上,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把大部分厂房拆掉,只剩下一个运煤的煤漏斗。如何跟保留下来的煤漏斗共同事情,让新的建筑既有曾经历史上的工业的构筑物如何产生新的整体?如何去对话,如何让旧的构筑物成为新建筑的一部分?这是这个设计的一个重点。我们首先把保留下来的煤漏斗变成龙美术馆从城市到江边的城市空间的一部分,当人在穿越建筑的时候能够体会到这样一个被保留的构筑的代价。同时希望去学习工业建筑跟功能直接连接的设计办法,然后产生一种新的,在近年来说仍旧是一个非常直接的建造,它知足了空间的庇护,知足展览的需求。通过一个墙体散拱的构造,去完成功能和构造的一种整体性。新建筑里面所呈现的是一个特殊朴实本真的建筑的面貌,它实在也是一种工业建筑的措辞的延续。
艺仓美术馆
艺仓美术馆的旧址老白渡码头以前也是运煤的码头。2015年的时候。我们建议在这样一个空间里面结合当年上海城市公共空间艺术季,在里面办小型艺术展,选了上海八个比较好的工业建筑改造的案例,和艺术家、舞蹈家互助,做了八个影像的展览,让市民知道未来在这里面会转化为公共文化空间。临时性的展览结束往后,我们重新装载,一方面得到市民的理解,一方面也让业主张识到保存工业看上去废墟的东西,仍旧具备再被利用的代价。我们在设计中只管即便少地对原有的构造进行毁坏,把原来煤仓的空间包裹在新建筑的里面,在建筑的外部看上去彷佛是一个新的建筑,希望能够通过新的外部悬吊的构造来建立一个黄埔江边公共的空间。在美术馆关门的时候人们可以通过原来大的运煤通道或者户外的楼梯,在这个建筑的平台上自由走动,完成从工业建筑到日常利用的转换。同时工业建筑大多是封闭的空间,如果在黄埔江边如果建立新的文化空间要建立开放性和公共性,这样一种出挑景不雅观平台的办法,建立了一种开放性的办法,人们可以自由地在江边上走,通过公共廊道的空间可以看到远处的陆家嘴。经由公共步道透过玻璃可以看到室内的煤漏斗。不才面可以进行公共的讲座和展览,在二层很狭小的煤漏斗之间的缝隙里面,也可以办出非常故意思的当代艺术展。新的构造参与之后,原来的工业建筑变成了新的构造体,彷佛活过来的觉得,从废墟或者失落去生命的建筑又重新变成一个有生命的建筑,产生新的上海日常生活空间的活力。
杨浦东段的“边园”
末了是去年刚刚完成的杨浦东段滨江项目“边园”。这一部分原来是运煤的码头,上面有两个长长的混凝土墙,一堵拆掉就扔在码头和防汛墙缝隙里面,还有一堵墙保留在这里。第一次去现场看到长长混凝土墙还有缝隙里长出来的大树就特殊有城市边缘的荒野感,又带有一种园林的诗意在里面,我特殊想保持这样一个墙的觉得,能够重新梳理或者整理这样一个空间,让这样一些荒野能够以某种办法存在,同时又变成本日日常生活的一个空间的一部分。这是从鸟瞰的照片上,可以看到在防汛墙和码头之间缝隙里面,混凝土堆积的废墟之间所迸发新的生命力和回归。废墟从某种程度上是建筑向自然的回归,既保持住了建筑向自然的回归,同时也表达了人类的建造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人类的建造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中,蕴藏着我们真正不断刷新或者不断认知的一种可持续性的观点。
袁烽(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方案学院教授、上海创盟国际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创始人):
袁烽
本日我演讲的主题是“建造数字未来”。在这样一个分外的韶光,数字成为今年紧张的主题词。在这样一个时期,所有实践者、研究者都该当思考一下该当用什么样的办法来改变我们的实践,改变我们的社会运营和盈利模式,现在我们的模式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以及以人为本的设计办法是否存在问题。我们提出来“人文的未来”,不因此人为本,而是人与物的新领悟和折衷。
在这样一个后人文建构的思维根本上,在学界存在一批对数字设计工具、数字设计方法,以及建造实践具有独特工具研发和理论研发能力的学者和建筑师,大家在一起共同搭建了新的知识共同体。
在过去三年我们做了三个桥。第一年我们用可乐瓶的废弃塑料,试图通过机器人打印平台来重新构筑它的力学性能,从而建成一个桥。桥重量大约1吨,跨度11米,可以站五个人。第二年我们通过机器人3D机器打印技能对这个桥进行提升,轻了不少,比以前少了300公斤的分量,可以站七个人。第三年我们考试测验通过金属打印和碳纤维变质的工具和研发来提升效能。我们对可持续发展主要的认知便是,在后人文时期的经济发展该当是“熵减式”的方法,这个桥的案例验证了如何通过我们的实践办法来实现这样一个过程。
在我们的机器人工厂,所有走位都是精确掌握下的一个参数化设计的结果。而这种结果在以往可能只能勾留在纸面,我们是把它物质化把它变成建筑的内在形式,变成建筑的新美学来展示出来。
四川安仁OCT“水西东”林盘文化互换中央俯瞰图
这样一些工具方法对付建筑师未来可以做什么?通过我们在2018年的实践来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先容。四川竹艺村落有一大片林盘,林盘大概面积三四万平方公里,未来对全体屯子进行开拓。全体四川的特点:景象湿润,被云雾笼罩,林盘的核心,有林有盘,有竹林、溪水,水流的声音,还有当地的特有文化。在环球化的知识生产根本上,数字未来的核心还须要在地性,我们的实践包括如何拾取材料,如何通过一种新建构的办法来实现建筑空间和在地环境的关联。
我们将机器人运到现场,通过现场砌筑的办法来进行安装。墙面我们是通过废弃塑料的再生来表示我们对可持续的态度,所有的隔墙像流水一样,实在是塑料的。这是我们对未来自然性的一种新态度。在空间上,我们希望通过这种通透性,内部的院落感,外部的野外能重新唤起当地老百姓农人对付家乡的自满感。这种自满感建立在新知识根本上,我们将这种新知识称为后人文建构的核心,它是一种全新生产模式,全新设计模式,全新建造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