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WIIISH惟学空间
在奥地利西部,博登湖东岸,普芬德山山脚,有这样一座小城,布雷根兹。1946年,刚刚经历了二战的欧洲还惊魂未定,布雷根茨也损毁严重,人口锐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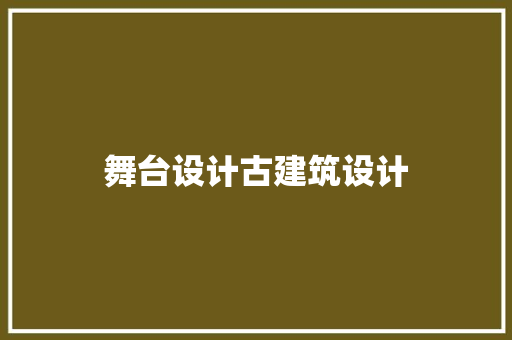
这样一座小城,在当时连剧院都没有,如今却发展成了欧洲艺术领域的明珠,“布雷根茨风格”更是成为了“大胆的视觉呈现”的代名词。
当然这并非本文的重点,本日我们想来聊聊的,是布雷根兹的艺术节,以及它的名片,舞台设计。
▲ 布雷根兹的艺术节,博登湖畔的水上舞台
布雷根兹艺术节是欧洲最著名的艺术节之一,从布雷根茨艺术节创办之日起,博登湖就成为艺术节展示的舞台。建筑大师卒姆托也凭着博登湖边的布雷根兹美术馆项目拿下了1998年的密斯·凡·德·罗欧洲当代建筑奖。
▲ 布雷根茨美术馆(图片来源:有方空间)
布雷根兹艺术节的标志——水上舞台,漂浮在奥地利、德国、瑞士交界的博登湖上,作为天下上最大的露天水上舞台,其距岸边足有25米远,预估可容纳近7000名不雅观众。
水上舞台的演出剧目根据特定的主题两年改换一次,博登湖的自然风景与超前的舞台设计结合,每年夏季都吸引着几十万人来到布雷根茨。
▲ 2015-2008年《托斯卡》
▲ 2017-2018年《卡门》
▲ 2019-2020年《弄臣》
▲ 2023-2024年《胡蝶夫人》
你有看过画作被丢到湖上吗?那同比例放大的舞美设计呢?上图宛如画卷一样平常漂浮在水面上的是刚刚落幕的22-23年布雷根兹艺术节水上舞台的现场。
回看2022-2023年的布景,主打歌剧是普契尼的《蝴蝶夫人》,剧情是女主人公巧巧桑与美国海军军官平克尔顿结婚后空守闺房末了自尽的故事。
▲ 《蝴蝶夫人》现场照
“你拿着这张代表日本之美的纸,然后你把它扔到湖上,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蝴蝶夫人》中所发生的事情的内在特色。”——Michael Levine
《蝴蝶夫人》水上舞台是由Andreas Homoki执导,Michael Levine设计的。在理解《蝴蝶夫人》的剧情之后,舞美设计师就想到这不便是将一幅俏丽的、古老的日本卷轴画扔在湖上,任其消亡的氛围吗?借此灵感,他们就设计了一个巨大的纸张舞台。
▲ 《蝴蝶夫人》现场照
在建造过程中,舞美设计师首先以1:50的比例模型创建了舞台,然后对表面进行了改进,使其具有纸张效果。再请专业团队对舞台进行数字化处理,并由带有虚拟现实眼镜的创意团队重新检讨,以检讨功能、运动和出口。
之后,又将全体舞台分割成117个不同的模块,用木材和聚苯乙烯制造,就像拼图的碎片一样,由起重机安装在完美结合的钢制底座上。
▲ 舞台施工现场
这个巨大的折纸舞台自21年秋日开始建造。布雷根茨音乐节的技能职员一贯在与33家企业互助创建该场景。他们的建筑完成了一项分外的寻衅:那便是让这张纸看起来很轻,轻到像是险些没有重量,但实际上“纸”舞台总面积为1,340平方米,重约300吨,它高达近25米,顶部和前面宽32米。
▲ 舞台全景
而现在,布雷根兹也在24年7-8月迎来了新一年的水上狂欢和新戏剧《自由射手》。
,时长01:19
▲ 2024年7-8月布雷根兹艺术节,展示影片
看到这里,大家大概惊叹于布雷根兹艺术节充满抱负与创意的舞台场景。那舞台设计究竟是干什么的?是装置设计的放大版吗?和建筑的差异呢?
就像是空间的一体两面
大略来说呢,舞台设计侧重于对空间和将发生事宜的想象,而建筑侧重于对空间实际功能的思考,也便是我所说的空间的一体两面。
从古至今,舞台与建筑一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早在古希腊与古罗马,人们便发挥聪明才智,建立起雄伟的圆形戏院,为斗兽或角斗等演出供应了空间。圆形戏院源远流长,至今已逐渐演化为主要的建筑原型。
▲ 古罗马戏院遗址改造
我们先来说建筑的视角,戏院,或者用建筑师的描述来说,不雅观演建筑。其历史大致是从圆形戏院开始,又在文艺复兴和巴洛克期间出身了镜框式舞台,大致类似于目前常见的室内舞台和电影院;之后进入当代,又衍生出了伸展式舞台和圆形舞台。
▲ 镜框式舞台
从这里可以看出,建筑的视角一贯聚焦于实际、理性、空间的构思,更多的是为了达到功能性和有效性。
而舞台设计呢?更多的是须要聚焦演员,更精确的说是聚焦演员的感情,并勾引某种心境,吸引或转移我们的把稳力,使沉重的、笨重的东西看起来轻盈,或是相反的轻盈变得沉重。
▲ 伸展式舞台
▲ 圆形舞台
“我们须要做的是将舞台上的所有视觉元素统合、剖析与编辑,而末了的成果已经不是一台布景,而是这个演出的视觉戏剧性。”
舞台设计是创造新的现实,故舞台上的空间并非真实的空间,并非我们一样平常熟知的空间利用与秩序。由于两者的目的并不相同,建筑空间是为了利用;舞台空间则是为了依着、呼应所欲表达的情绪。故主要的是是否让不雅观众感想熏染到感情而非是否符合真实。
舞台设计大师的空间邪术
建筑和舞台设计,都存在着操纵和转变空间以达到特定目的的共同特点,它们横跨在艺术和技能之间,试图达到审美和实际的结合,不少舞台设计大师都有着建筑干系的背景。
乔治·西平
出生于哈萨克斯坦的乔治·西平便是一位建筑出身的国际舞美大师。他17岁考入莫斯科建筑学院,却在1981年辞掉了建筑师事情,申请进入纽约大学蒂施艺术学院攻读舞台美术设计研究生。
80年代中期,西平正式开始了他的舞台设计生涯,其设计的《尼伯龙根的指环》《战役与和平》《俄狄浦斯王》《唐璜》等剧目,已经成为了当代歌剧舞台的经典作品。
▲The Ring Cycle (Saint Petersburg) 环(圣彼得堡)
乔治·西平的作品带有强烈的体积感,这无疑来自他的建筑学背景。他重视参考所有艺术表现手段与不同期间的历史元素,但他认为最主要的元素无疑还是演出空间。
随着新技能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舞台开始依赖投影及多媒体,但乔治·西平认为这是一条捷径,不用成为舞台的主导。“这些手段归根结底是一个平面的东西......戏院中,没有比空间更有力量的形式了,我们该当更好地去表现空间中真实的材质、真实的气味、真实的生命,让不雅观众在戏院中有真实的视听感官体验。”
▲Oedipus Rex 俄狄浦斯雷克斯
西平所理解的舞台设计是一门繁芜的、综合了各种文体于一身的、具有创造性的艺术形式。舞台上可被感知的三维立体空间环境,被即将发生的演出授予了神秘和意蕴的力量。他用建筑、雕塑、绘画、诗歌、音乐来塑造作品,但最主要的是,传达给不雅观众自由大胆的想象力。
安娜·维布罗克
安娜·维布罗克(Anna Viebrock)是德国戏剧界最具影响力的布景与服装设计师之一,是瑞士大导演Christoph Marthaler的“最佳拍档”。以1993年于柏林公民剧院创作的一部《杀去世那个欧洲人!
杀了他!
杀了他!
杀了他!
一定要杀了他!
》震撼欧陆剧坛,从此走上成名之路。
她的设计, 看重场景研究, 将布景设想为建筑,利用不同时期的建筑元素,将历史带入舞台,让生活和韶光在个中留下痕迹。你会创造她的作品有令人惊异的机制,与日常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背道而驰。她从车库、轮船、啤酒厂、教堂或飞机机舱等元素中解构建筑,并将它们重新组装在舞台上。
▲44 HARMONIES FROM APARTMENT HOUSE 1776
“解构”是一个具有时期性的文化特色,解构主义,后当代的一个分支,在词典里并没有明确的定义,其字面意思为将某个构筑物或建筑物冲破或拆除,个中既代表了却构成分,同时也代表了某种思潮。而 解构主义建筑作为一种后当代期间的建筑思潮, 以其独特办法对传统的建筑提出了质疑,利用扭曲的、不愿定的、混沌的形体重新诠释建筑。
▲44 HARMONIES FROM APARTMENT HOUSE 1776
而当解构主义建筑重逢戏剧舞台,也就造就了安娜·维布罗克的独特的舞台设计,从中不雅观众也能感想熏染到她带来的扭曲和失落控、焦虑与忧郁的情绪暴击。
▲44 HARMONIES FROM APARTMENT HOUSE 1776
更多跨界的舞台创作
近年来,传统的设计行业的专业界线正在模糊,“跨界”更是早就成为新世纪设计领域的热门话题和趋势之一。一些设计师渴望在跨界中打破思维定势,一些设计师则勇于体验真实跨界的乐趣。
跨界设计并不虞味着思维办法的颠覆,就像建筑师的跨界艺术作品,并没有抹灭建筑师个人的建筑素养与其建筑语汇。
不同行业的设计师们跨界参与舞台美术设计,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思考剧情构造与演出空间,更让经典抖擞新的异彩,对不雅观众产生新的启迪。
01
2002年在上海大剧院上演的比利时多媒表示代舞剧《变幻城市》,舞蹈团为了在舞蹈、多媒体与建筑之间建立起咬合的关联性,请了著名的英国建筑师扎哈·哈迪德来设计布景。
在整场舞蹈中,导演力争探索在钢筋水泥的现实城市,带来虚幻缥缈的生存状态,便让舞蹈演员、透视变形和光影效果奇妙地搭配在一起。
而扎哈设计了三个可分离组合,类似于水泥体块的建筑桥体。
当构造体平行放置时,即暗指虚幻城市剧情里,舞蹈演出展现出的人与人近在咫尺内心却冷漠迢遥;当三个水泥建筑体块交叉合并时,又暗含生活本是一个交叉的网络意向。
02
构造墨客圣地亚哥·卡拉特拉瓦曾说:构培养是建筑。在其作品中,运动的韵律美始终贯穿在构造形态中。
它不仅仅表示在全体构造构成上,并且深化在每个细节之中,同时他将雕塑、几何学、工程构造学,还有自然态和谐的领悟。从而形本钱身的构造美学,一套专属于他的独特建造语汇体系。
在他布景的舞剧《架构舞蹈》中,悬挂在舞台上方巨大的弧线缆索构造可以随着舞蹈的进行,变革空间造型。奥妙地合营芭蕾这门足尖上的优雅艺术,让不雅观看者有和谐的视觉享受。
对构造力学有分外嗜好的圣地亚哥·卡拉特拉哀求光芒完备贴合这个在舞台空间上方的弧线构造,以塑造其力学美感。纵然光芒变革多彩的时候 ,也能看出全体构造的上的光色过渡均衡 ,和谐并存 。
03
伊朗著名女性艺术家西丽 · 娜沙特紧张从事电影,录像和拍照等艺术领域,压迫、权力、性别、生活、去世亡和殉难等是她紧张关注的工具。
2017年在萨尔茨堡艺术节期间她跨界辅导完成了歌剧作品《Aida》。在西林· 娜沙特看来,歌剧《Aida》的舞台是一件整体化的雕塑。她利用两个镜像元素供应的可能性和视角变革,让作品在不同的阶段呈现截然不同的视觉效果。
利用两个镜像的一半,可以天生非常不同的空间配置。放置在旋转舞台上,这种构建的空间配置可以动态移动,从而实现额外的视角变革。
为了加深场景的氛围感,在建筑中添加新元素就显得十分主要。西林 · 娜沙特从排列成钟乳石的当代玻璃管中,创造了一个悬挂在舞台中间的枝形吊灯组件。吊灯发出的琥珀色光给寺庙添加了庄严又诡异的视觉效果。
04
奥拉维尔·埃利亚松,丹麦裔冰岛籍艺术家,以雕塑和大型装置艺术有名。他长于在作品中利用光、水等元素或调节空气温度以增强不雅观赏体验。
他曾和著名导演阿莱塔·柯林斯互助改编创作了《希波吕特与阿里西》。埃利亚松在个中卖力设计舞台布景、服装和灯光,于2018年11月25日在柏林国家运动场首演。
当设计的边界模糊,当任务书变成剧本,这便是想象力的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