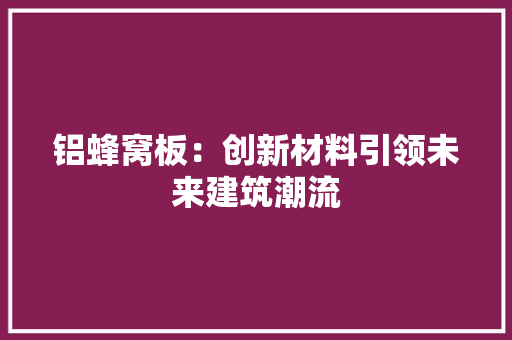于中宁 2024.08.26
拍文化和自然遗产系列影片的想法,在我从电影局回到科影之后就已经开始有了意向。

在按照规矩先拍了几部10分钟一集的短片后,就开始大量看建筑、艺术、风景名胜等等的书和文章。1986年完成了一个小时高下两集的《瑰丽的风景名胜》,虽然在国际上拿了个小奖,但自己觉得并不成熟。又用了三年韶光,不断看书和反复修正剧本,完成了《不朽的古代建筑》、《悠久的历史名城》两个剧本,以及《欧洲建筑》的剧本草稿。
1989年初,在乱糟糟的形势中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联系得到成功,6月7号我们登机赴欧洲,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供应的仅仅2万美元的经费,以及北京科影厂供应的仅有1:2的片比,我和拍照程受琦,以及翻译赵长兴,在欧洲拍了4个月。期间赵长兴的单位怕他跑了,把他叫返国。我们在法国雇佣了一位留学生,还要付给他事情用度。我们便是在这样艰巨的条件下完成的《欧洲建筑》。
为了节省经费也节省可怜的片比,在1990年做完《欧洲建筑》的后期,1991年我们将《不朽的古代建筑》和《悠久的文化名城》进行套拍。但这时候的条件已经好多了。首先是国家文物局非常重视,文物局的两位元老谢辰生和罗哲文,说服文物局从极其有限的经费中划拨了30万给我们,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天文数字了。同时发了文件给各文保单位,请他们全力支持我们的拍摄。培植部也全力支持,除了发出文件外,培植部的资深副部长储传亨亲自给各个城市乃至副省长写信,请他们给予帮忙。储部长的秘书陈海云一贯和我保持着联系,他还动员了培植部的各个部长秘书随时给我们办理问题,可以说全体培植部办公厅都为我所用。
1980年代和1990年代是思想解放和思想迷惘的时期。通过文革10年混乱,所有人都认识到过去的一套行不通了。但是许多人又陷入了新的迷信之中,这便是对西方思想体系的迷信。无论是文革还是新的对西方的迷信,在一点上是相通的,这便是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否定。从五四到文革,中国形成了一个对自己5000年文化缺少深刻剖析而通盘否定的传统,这种传统在几年前关于五四运动的电视剧中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而西方思想的传入,又给这种通盘否定供应了西方种族优胜、文化优胜、制度优胜的理论根据。
实际上在西方还存在一个非主流的思想流脉,这便是从伏尔泰的文化多元到萨特的存在主义。多元文化后来发展成了多元文明。多元文明讲的是事实上存在着多个文明,每个文明的产生和发展都有其地理和历史的依据,西方并非人类的唯一文明,更何况它的历史短得多。存在主义是讲任何有规模有历史的存在都有其合理性。否定一种存在的合理性,很可能是一种浅薄的狂妄。
《不朽的古代建筑》和《悠久的文化名城》,思想主脉便是想在与欧洲建筑的比拟中,磋商中国文化和中国建筑存在的合理性。希腊早期的建筑也是木构造的,希腊石构造建筑之所以是梁柱式的,由于它来源于木构造。实际上中国也早就创造了拱券构造。但为什么中国木构造建筑5000余年一气呵成?地理的缘故原由,材料的缘故原由,不雅观念的缘故原由,中国人将一种东西做到极致的那种精神状态,以及可能还有许多其他的缘故原由,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这些都在影片中做了大略的交代。
工业化的新材料改变了西方的建筑,也改变了中国的建筑,这是一定的历史趋势。新的材料须要新的美,任何对历史的抄袭都是可笑的,但这并不虞味着对当代潮流的抄袭不是可笑的。正像我在《欧洲建筑》末了所讲的,凡为人所创造,必为人所打破。一个建筑师如果没有在打破的根本上形成个人风格,那他就注定是平庸的。
可惜的是,平庸,正是我们这个时期的紧张特色。
我将另有文章来忆述那个过程的各个部分,并感谢那些帮助过我们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