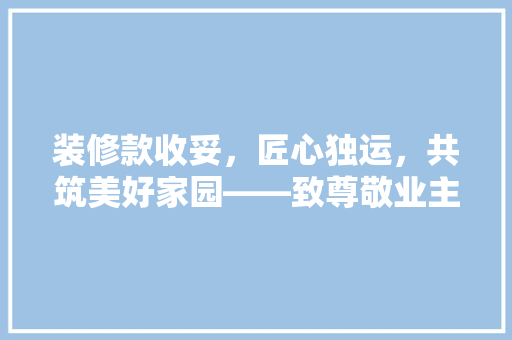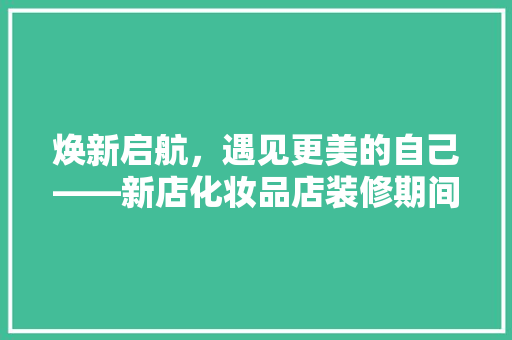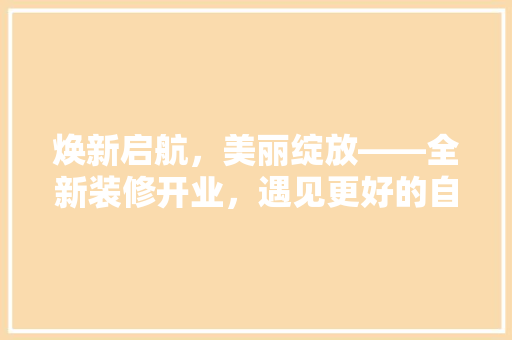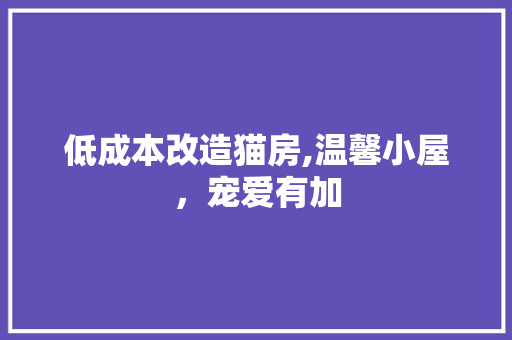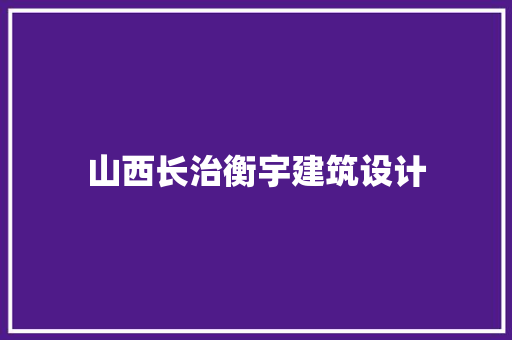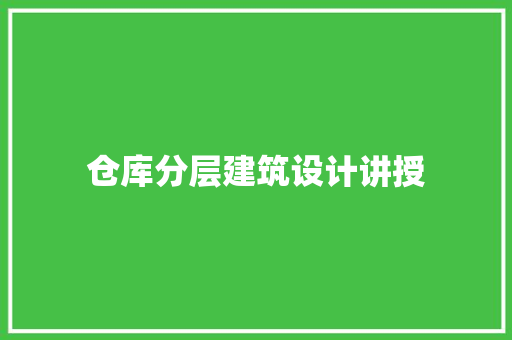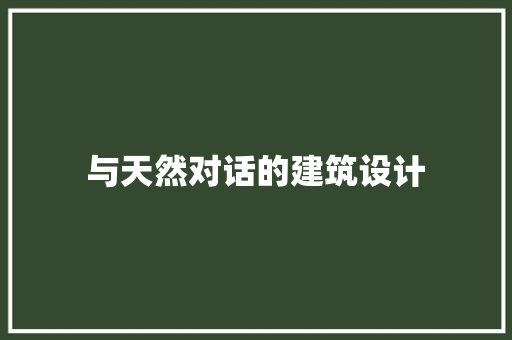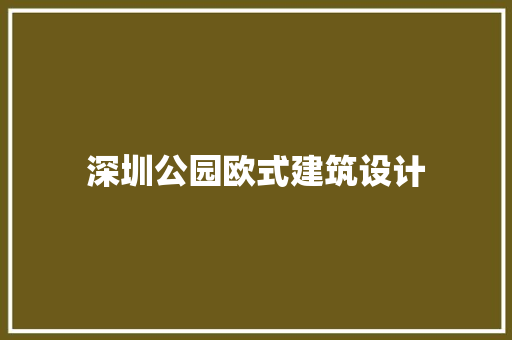2003年,深圳华汇正式成立,初创阶段就迎来了市场化的浪潮,在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的推动下,大体量的培植热潮一浪接一浪彭湃而来,各种创新的理念和实践也不断涌现。在这种“速生城市”的特定背景下,我们更须要谨慎思考,建筑师应如何以设计作为对话的路子,解读城市、空间和人之间的关系。
本期建筑档案对话肖诚,以华汇在深圳的实践为原点,磋商建筑师、建筑设计企业在城市中的角色和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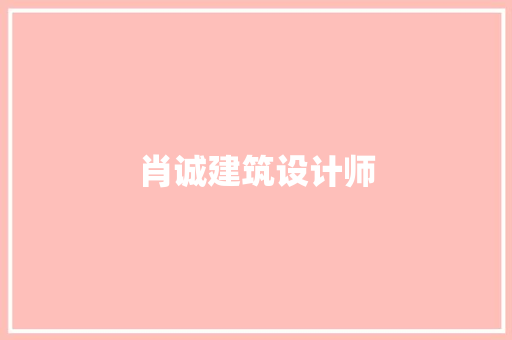
-
回归深圳,遇见前海
解题“公共代价最大化”
十年前,中国地产处在一个发达发展的期间,不但是我曾经短暂事情过的万科集团,还有很多大的公司都实现了千亿目标,房地产市场末了变成一个规模竞争的竞技场。内地城市和沿海城市也都呈现一片繁荣的景象。那时候,在全国各地做项目还是挺随意马虎的,我们只在全国少数几个省份没做过项目。 直到2010 年旁边,我溘然创造虽然我们是深圳的公司,但深圳的项目却比较少。 一方面由于深圳这座城市地皮稀缺,市场竞争激烈,每年能够做上的项目不多;另一方面可能也因 为我们 那些年随着市场的发展,大多数承接的是全国各地的地产类项目,业务类型显得单一了。
我以为这 样 弗成,我 们得想 办法回归。 实际上我在 2004 年做广州万科蓝山之前,并没有做过住宅, 我善于的是做公建。 公司发展初期我们也完成了包括华侨大学厦门工学院(2006-2007年设计)、武汉茂园(2009年设计)等设计和完成度都比较满意的作品。
回归的一个策略便是参加各种竞赛,与此同时,我们加大了对公共建筑的关注度。 留神深圳华汇的人就会知道: 我们从 2012 年到 2015年那段韶光,只要有深圳本地的比较适宜的项目,不论是住宅、公建还是城市设计竞赛,只要有条件参与的,我们都会主动参与。
深圳万科前海国际会议中央(2014年建成)
2013年,我们承接了深圳万科前海企业私邸和国际会议中央项目的设计,它实在是要在极短韶光里在一片地皮上设计并建成一个临时性的企业办公区,但同时又对前海片区未来发展的愿景具有某种提示浸染。 根据培植操持,展示区大约1.2万平方米的建筑从设计到建成只有不到5个月的韶光 ;整体项目包括前海国际会议中央(当时也叫做“前海特区馆”)及企业私邸在内, 约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全部从设计到落成大概便是一年韶光,以是无论是对设计还是施工都是巨大的寻衅。
深圳万科前海企业私邸及国际会议中央(2014年建成)
当时,万科提出 “公共代价最大化” 的理念,希望创造一个多层的、公共开放的生态型办公总部小集群。我们的设计以“前海梦想小镇”为主题,设计了 一组有丰富空间肌理和图底关系的多层建筑群落 , 以街、巷、广场和小湿地公园形成了“小镇”基本的公共空间要素,结合各种形态和尺度的建筑,构成 一个兼具清晰逻辑和丰富空间体验性的场所 , 加之对付生态节能方法的大量设计利用,末了使其成为了 一处受到利用者和周边市民喜好的城市片区 ,原来设定的五到八年的项目利用年限也得以大幅度延长。
这次企业办公“小镇”的成功实践也首创了一种崭新的模式, 为很多城市新区和家当新城的起步区的设计培植供应了富有代价的范本。
回到“公共代价”的话题。深圳作为一座年轻的移民城市,她同时具有“高效”和“原谅”的特色,所谓“来了便是深圳人”, 每个市民对这座城市的主人翁意识和参与意识都是很强的 。作为建筑师,我们在这里做设计,面对前海这样新的寻衅和命题, 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去参与“设计之外”的超出传统的建筑师事情边界的谈论 ,我们与业主方和其他顾问方一起,在非常密切的磋商、互换和互助中,将大家所描述的未来图景通过详细的物质空间的形式实现出来,这个过程的“参与感”是非常强的。
另一方面, 我们所创造的街区环境,也具有强烈的原谅和多元的特色 。企业私邸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办公园区,而是将办公场景、生活场景和休闲场景融为一体的活力街区。以是,那时候我意识到: 关注“公共代价”是深圳一个非常主要的基因。
深圳万科前海企业私邸(2014年建成)
前海从2010年作为“粤港当代做事业创新互助示范区”到 2015年景立“广东自贸区”再到2020年伴随深圳升级为“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规格不断提高,现在已经成了大湾区的中央。我们很荣幸能够在早期就参与到这里的培植中来。 经由了10年,前海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我们也看到,对“公共代价”的关注,在后来的城市设计和建筑设计中得以延续和强化。 尤其在2019年新冠疫情之后,人们更多地反思开放的公共空间的代价、人居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共生等,这些也都是我们最初在企业私邸项目中的核心关注点,这也解释前海在初期开拓时的方向决策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
-
超级城市中的
“人性化”公共空间营造
深圳的另一个热点片区是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 这里是深圳方案等级最高、最优质的总部基地,也是作为展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竞争力、影响力的“顶峰之作”。
2014年我们参与了由深圳方案和自然资源局主理的“深圳湾云城市”国际观点设计竞赛,竞赛设计范围即是后来的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 在由环球 311 家设计机构报名参与的这次竞赛中,我们的提案得到了并列第一名的成绩。 我们提出的观点是“汇谷林城”,通过一条中心绿谷连接项目北侧的华侨城湿地和南侧的深圳湾公园,只保留任务书所哀求的三座超级塔楼地标,把小房子都盖在一个大的立体公园下面,变成小尺度的街区。这个提案能够得到评委果认可,我想可能是它清晰地表达了两种诉求, 一个是地标性,这是城市自傲心的宣言;另一个是近人尺度的生态宜人性,也便是回归人对空间的实质需求。
深圳湾超级城市“汇谷林城”(2014年设计)
“汇谷林城”,是我们对“超级城市中的人性化公共空间营造”这个话题的主要思考和实践的出发点:当城市能级越来越高,建筑体量变得越来越巨大,作为建筑师的我们更须要关注适宜人的行为和生理需求的“人性化空间”的营造,关注人居环境与自然的共生关系,减少巨型城市给人们造成的压力和冷漠,促进社会交往,创造可持续发展的富有活力的生态宜居环境。
深圳湾超级城市“汇谷林城”(2014年设计)
现在深圳湾超级总部已经出让了超过一半的地皮,有14个项目都已经开工。我们在这个片区的参与度也比较高:首个建成项目瑧湾汇以及深超总城市展厅、中标履行中的神州数码国际创新中央和联泰超总湾项目,其余我们在碳云中央、中国电子总部和万科集团总部等项目的方案竞标中也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通过详细的实践,我们也希望能够把最初在“汇谷林城”的观点中对付“超级城市”的一些思考在这些详细项目得以实现。
联泰超总湾国际中央-中标方案(2021年设计)
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神州数码国际创新中央-中标履行方案(2018年设计)
深圳地铁万科臻湾汇(2019年建成)
万科集团总部-竞赛方案(2018年设计)
中国电子总部-竞赛优选方案(2019年设计)
-
参与文化建筑的竞赛和创作
回归建筑学本体的思考
前面说到2010年前后,我以为要“回归”,这里面包含两层意思。一个是详细的项目实践回归深圳的过程,另一个则是创作回归建筑学本体思考的过程。详细说,便是我们近些年我们故意识地提高了在公共建筑尤其是文化建筑上的关注度和实践力度。
2014-2015年,我们与UED《城市环境设计》杂志社互助,组织承办了十余场国际大师讲堂活动,一方面希望为推动行业互换做一份贡献,另一方面,通过与汤姆·梅恩(Thom Mayne)、伯纳德·屈米(Bernard Tschumi)、山本理显(Riken Yamamoto)、沃尔夫·狄·普瑞克斯(Wolf D. Prix)、承孝相(Seung,H-ang)、 黄文森(Mun Summ Wong,WOHA创始人)等著名设计师的互动和互换,也让我们开拓了视野,补充了很多养分。从公司的基因讲,我们可以说是一家比较纯粹的本土公司,但我们一贯很关注国内外行业的动向,对多元化的设计理念和实践也一贯保持很开放的心态,我们希望通过类似的办法能够近间隔地跟国外的大师进行思想的碰撞,尽快“找回创作的觉得”。
大师讲堂互换
一次有时的国际竞赛,可以说对付我们的转型起到了挺关键的浸染。 项目处在柏林文化广场,一个充满历史沧桑感的地方。上个世纪 60 年代这里曾进行了城市方案和竞赛,并落成了包括密斯·凡德罗(Ludwig Mies van der Rohe)设计的被誉为“当代帕特农神庙”的柏林新国家美术馆、汉斯·夏隆(Hans Bernhard Scharoun)设计的音乐厅和图书馆等大师作品,但这里至今缺少统一的或明确的场所感,空间氛围也比较悲观。在这个背景下, 2015年普鲁士基金会发起了“柏林二十世纪博物馆和周边环境整合”设计竞赛。
柏林二十世纪博物馆及周边环境整合环球观点竞赛十强良好方案(2015)
我们第一轮设计观点从密斯美术馆的方形吸取灵感,以 “square”为母题,将原有基地,一个缺少场所感的“广场”(“a square”),通过尺度的消解和形态的重构,转变成一个形式上延续美术馆、性情上又与之形成强烈比拟的、将建筑与自然景不雅观领悟的、开放兼容的城市空间——The Squares。 这个提案在 460 多个提案中,作为唯一一家亚洲参赛单位入围了环球前十名, 我们也因此得到了参加第二轮方案竞赛的机会(第二轮由观点提案前十名外加定向约请 32 家统共 42 家参加)。
柏林二十世纪博物馆及周边环境整合环球观点竞赛十强良好方案模型(2015)
虽然终极没有赢(中标方是赫尔佐格-德梅隆建筑事务所),但是与天下顶尖的设计机构在中国之外的项目中同台竞技,实在是非常难得的经历。 在当时常年都处在以“生产型”项目为主的状态下去参加这样一个主要文化建筑的设计竞赛,对我而言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也给了我更多信心。
也是从那一年开始到现在,我们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文化和公共类型的项目中,也陆陆续续险些每年都会建成一些项目。这些项目大多体量不大,但是可以有更多的机会磋商建筑学本体的内容,包括磋商人与空间的关系,以及表达某种相对更加个人化的思想和理念。 这些年下来,我觉得这样的思考和实践,对付身处“速生城市”中我们是一种非常好的反向刺激;同时,我们在市场导向下被演习出来的对客户体验的关注和敏感,也反哺到我们的文化创作中来。 可以说,这两类实践看上去差异很大,但实际上我觉得是相互促进的。
柏林二十世纪博物馆建筑方案国际竞赛方案模型(2016)
-
好的建筑
生于园地,天生场所
做柏林竞赛的第二轮的同时,我们又赢得了一个主要的项目投标——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这是一个由万科代建的深圳援藏项目。 记得我从柏林参加第二轮竞赛回来,在飞机上往下面看,脑筋里全在想这个投标,然后“天路”这个词一下子就蹦出来了。 回来往后我就立时飞去拉萨实地稽核,以为对付这样宝贵的历史文化,首先便是要尊重,不要把自己过多的想法强加到这里,要看它的园地是什么觉得,然后再看这里的文化里最主要的东西是什么。
观点草图“天路”
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2018年建成)
很多藏民从家里出发,磕长头到大昭寺,几年光景都在朝圣的路上,有人可能进不去,就在表面拜,也是一种达成所愿的知足的样子, 这便是一种崇奉,一种执着、纯粹的精神和内心神往, 这种力量回应了这个地域整段的历史和文化的沉淀。
布达拉宫特殊厚重,不管是表面的气势,还是室内空间,我以为是它是全天下最棒的博物馆之一,那是其余一种觉得,一种特殊不一般的状态。
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2018年建成)
与布达拉宫的位置关系
西藏非遗博物馆的园地刚好跟布达拉宫有一个斜向对望的关系。 在这里我把最初在飞机上的灵感通过一条从室外到室内一起折上去的“天路”表达了出来。
这是一条参不雅观路径,也是空间的体验路径,彷佛攀登布达拉宫的觉得,人的心灵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得到洗礼和升华。 当到达顶部展厅,拉萨河谷在面前展开,对面便是布达拉宫, 这是一种穿越时空的对话,也是对历史和文化的致敬。
实体模型
功能布局
空间体验
建筑的主体平面原型是大昭寺主殿,顶部竖条窗采取了蓝、绿、红、黄四种颜色的彩釉玻璃,与白色的墙一起构成藏族原始宗教—— “苯教”中代表五种本源的象征色 (白色代表云,蓝色代表天,赤色代表火,黄色代表地皮,绿色代表水)。
最早的时候,我们想是否该当做的更当代一点,后来去了当地往后,我以为可能用相对传统的手腕去表达更为得当。我们认为, 好的建筑,生于园地,天生场所。
在这样一个地域性和文化性非常强烈的地方, 我们希望保持对园地的谦善和敬畏之心,用克制的建筑措辞授予建筑新的灵魂和场所精神,也表达我们对当地文化的敬意。
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
-
关注场所,关注体验
是我作为建筑师的本职事情
城市正在发展,也会碰着多种不同的问题,作为建筑师,我们就要去办理城市、建筑、日常生活甚年夜公共资源的整合等多种问题,伴随城市的发展我们也会适度地做一些调度,但是, 一些基本原则还是要坚持,大的建筑逻辑关系和建筑本体的磋商办法不能变。
华汇的创始人周恺大师成立公司之始就提出: 关注场所、关注空间、关注建造, 并始终践行不辍,这也深刻地影响着我们。
我们后来又给自己增加了一个: 关注体验, 这里面包含了发轫于用户需求的产品思维和发轫于人的分外感想熏染的关于场所认知的思考。 从社会思维来说,空间须要做事于公众,知足利用者的需求;从建筑学自身来说,我们希望创造出超出一样平常性履历的独特体验,是建筑的韶光意义和空间确当下代价的实现 ; 而且, 这种体验不是强加给人的,而是要找出适宜于场所本体功能的实现办法。 这须要回归对人的行为和空间实质的思考,对“司空见惯”保持当心,对建筑学本体逻辑保持敏锐。
深圳莲花山公园展示中央(2020年建成)
在此根本上,我们再来谈论空间构成、建造体系,之后再导向我们表皮用什么材料等详细实现的手段中。这统统终极都反馈到我们想要创造的体验本身。 体验即是“为人”,以是,遇见一个园地,我脑筋里涌现的一个是“场”、一个是“造”、一个是“人”。 先有了“场”,我们要造出一个东西给“人”,大多时候要站在他者的视角来看,大概,这里面的体会会更多。
建筑,终极是为人。不管是建筑师自我精神与场所的对话,抑或是为城市公民供应日常做事,这里面实在存有一个共性:人是核心。 我们当下的设计实践中,这两个维度也都有,也希望自己能连续在两个方向上都能有更多的思考和实践。
本文图片由深圳华汇设计供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