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何胜景?胜景几何?建筑档案更加侧重这个问句。问时期,问当下,问建筑,问自己,胜景的临摹,像是一个建筑师终极目的,问,则是作为建筑的常态性动作。 当建筑不仅仅是建筑,建筑要传达的”胜景“所要给予的该当是一种什么状态,重新对建筑和自己进行发问的同时,建筑,也会给于自己更多的指引,当下的建筑也就成为了未来的韶光,我们同在个中,同问,却不须要趋同,作为建筑师的存在,也是为了通过建筑,让人们由于建筑而得到美好的生活感想熏染。
不去随随便便地做设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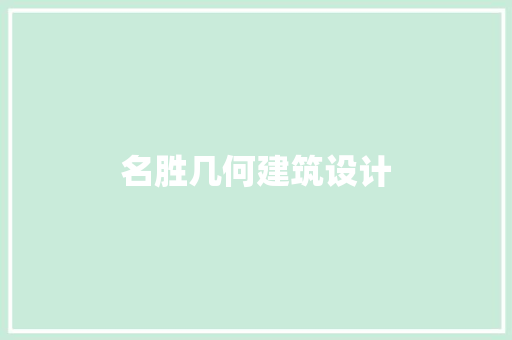
建筑须要主动探索,也须要更有深度的思考
、
有一点特殊有趣,我觉得自己一贯没有太过长远的操持,也从来不做五年以上的操持,事情和人生操持都没有,便是把这两三年手头上的事情做好就行,对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我会很专注。
这些年,那种“文的浪漫”彷佛都藏在了心里,给大家觉得更多是严谨、理性的状态。
我并不把兴涛社区这一组项目当成常规项目对待,从这个项目开始,我就加入了更多自己的思考,通过深度的思考——这个“深度”可以打引号,由于,当时看着是深的,大概并没有那么深——也便是说:我开始意识到要“经由深度的思考之后再去做设计”。
冬奥会延庆赛区全区前期草图与延庆冬奥村落及国家雪车雪橇中央模型
延庆冬奥村落(上)与国家高山滑雪中央(下)
“不去随随便便地做设计”是我做项目时候的一个思路,这跟我在大学里的学习和受到的一些触动是有关系的,要做“有思考的设计”。
那时候,我做的项目并不多,也没有那么多好项目的机会,都是市场上很平常的一些项目,是很多人大概看不太上的项目,我以为大量的年轻建筑师可能都会是这样的情形,比如那时候的我也接不到一个真正的学校项目,由于学校是公共建筑范畴,但我能够掌握的是在兴涛小区的配套里做这么一个学校,并把它当成一个公共项目来做,而且要做出我独特的思考来。以是,北京兴涛学校对我很主要。末了这个学校作为一个建筑作品案例,在《北京青年报》有过一个整版的宣布。我记得那标题的大概意思是说:学校还可以设计成这样?
在这个过程中,有坚持,但并不会特殊固执,我会考试测验找到一些实现自我的路子与办法,在建筑里,须要这种“主动性的探索”。2000年开始担当我们院的副院总,我31岁,成立事情室是在2003年。那时候的事情方法已经跟后来事情室的整体状态有些相似了。
李兴钢事情室百口福(2003年-2011年-2020年)
行政方面的事务并不太会影响我做设计,那时候管的人要好比今多一些,还要参加院里的一些技能管理层面和带有公益性的事情。但做设计紧张还是依托于所里的团队来做,那时候团队是不固定的,做一个项目可能是这拨人,做其余一个项目可能是其余一拨人,2003年的时候,院里进行机制层面的改革,应对来自国外建筑师的竞争,建立了这种“大院里的独立建筑师事务所”的专家(院总)事情室模式。
第二个事情室(上)与第三个事情室(下)
李兴钢个人办公室
事情室的成立改变了我的事情条件,也有了自己相对稳定的一个事情团队,刚开始事情室只有5个人,恰好也遇上2002年底开始的“鸟巢”项目与赫尔佐格·德梅隆公司的竞赛互助和中标,又要建立一个专门的设计团队,在这个项目上跟他们进行项目履行的全过程互助,以是,就相称于事情室成立的时候,两个团队、两部分事情要同时进行。“鸟巢”项目一贯持续到08年,我自己的事情室,也同时做一些零散的小项目。
中国自有其“胜景”
建筑要谈论的则是“胜景几何?”
“胜景几何”这个词提出来,是在2013年,通过一次展览开始的,但在此之前,我也已经一定韶光类似“几何与胜景”这样思考性的东西,从2013年开始,开始正式在媒体上揭橥。
2013北京方家胡同微展
2000年是挺主要的一年,那时我正在做兴涛社区的展示接待中央,也便是兴涛小区的售楼处,在这个带有商业属性的小建筑中我开始用引入 “园林”为线索的当代设计方法, 即“园林的关联性思考在当代建筑设计中的考试测验与利用”,那是一个出发点。
“八人展”现场事情室留影,北京(2004年)
从1991年到2000年的这十年里,从在部院演习到在部院有了自己的事情室。之前的一次经历对我影响很大,那便是我讲过多次的“爬景山,瞰故宫”,那种强烈的感想熏染对我特殊有触动,开始对“中国传统城市和建筑的同构性”感兴趣,那种传统城市和建筑营造聪慧中的城市感和文化感,让人乐不思蜀,这是最初的一个“触动”。由于这样的一次触发,开始看一些这方面的书,比如像李允禾师长西席的《中原艺匠》这样标志性的研究著作,还有台湾王镇华师长西席的《中国建筑备忘录》,大体都是从空间剖析的角度对中国传统城市和建筑进行的研究。
万春亭俯瞰故宫手绘
佛光寺手绘
草图三则之蔚县水涧子
园林稽核,苏州(2006年)
从本科毕业设计我就开始做这方面的考试测验,便是把传统中国城市和建筑的营造聪慧,融汇到当代建筑的设计中,便是这么一个欲望。当时想到设计院来盖屋子,有点小小自傲和想要考试测验的冲动,也跟这些东西有关系。
出国,我当时以为不须要,是由于相信我们自己的内在就有很好的东西,想读研究生也是希望请聂兰生和王其亨两位老师一起做我的导师:王其亨师长西席是在中国建筑历史研究方面非常有造诣的大家,聂兰生师长西席对付当代建筑设计有自己的研讨和思考,同时她也是一线的建筑师和研究日本建筑的专家。通过读研究生进行更深度的思考和研究,再去盖屋子自然是好,但我并没有读成研究生,而是直接在盖屋子的过程中研究和学习、思考。
北京大院胡同28号改造
北京大兴的兴涛小区里,还有其余一个没有实现的小建筑叫兴涛会馆,也是一个配套公共建筑,实在是我关于传统城市营造办法在当代建筑设计中利用的考试测验和磋商,也便是说,我努力在实践中探求机会,做了很多类似的事情。在2000年研究兴趣转移到园林方向之前,兴涛学校和兴涛会馆是两个代表我对城市和建筑方向兴趣的主要项目。
应有的“韶光”与“贯通”
不变的是“聪慧的存留”
后来,我对中国的村落或者聚落也产生很大的兴趣,有类似”爬景山瞰故宫”的冲动,中国园林对我的触动也是类似的,这些都是一种“带有中国底色的思想交互”。
这样在韶光上我个人思想先后关系的进程,也伴随其实践中不同路径层面的考试测验。实际上,我一贯在探求,乃至,有时候会刻意回避“传统”这个词,并考试测验在中国的传统城市、建筑、园林、聚落中,找到那种“当代性”。
所谓“当代性”,它不是用“传统”这个词能够形容的,“当代”跟“传统”对应,实际上,它代表了一种韶光的延续,或者说它是不以韶光条件而变革的“一种聪慧的延续和留存”,它是可以超越韶光的——在以前的时期它可以“发生浸染”,在当代它也可以“发生浸染”,这种“浸染力”可以被借用过来或者说我们是可以从中吸取养分的。
唐山第三空间
这样一种“与聪慧有关的存在”,古人实在早就创造了,真正的聪慧,是不受材料、技能、韶光等成分旁边的,我们也希望能找到的或者正在找的,或是我以为自已已经找到了的那一点点,你可以理解为是一种“韶光的影象”,或者是一种“存在状态”。
而这种存在状态,我创造它在城市、建筑、园林、聚落平分歧形态中是同等而贯通的,虽然经由大概30年的韶光,让我对每一种形态逐个产生了兴趣,然后,不断去研究、考试测验、继而做到理解。让这统统能够“贯通”在一起的是一种哲学、一种对天下的意见,也是一种代价不雅观与生活态度,这种“生活哲学”是让它们能够贯通起来的根本。
天津大学新校区综合体育馆
选择很主要,可以向外看,但依然要明白自己坚持的工具。我也并不是说不向外看,实在,“向外”给了我一种选择,这条路也已经摆在那了,是“当代主义”或者是别的一个什么东西,但这个东西也仅仅是表征和措辞,可以给我营养,但或许不是我的方向。有时候我们在选择开始或者根源的时候,实在已经选择了未来,找到属于个人的“根源性的探索方向”决定了“自我”的呈现形式。
向外,也是为了向内
你只有到了罗马,才能更好的认识巴黎
“向外看”后来对我来讲也很主要,1998年有机会出国,可以去欧洲看看那些“经典的城市”和“经典的建筑”,在这些建筑的古代和“当代”之中体验它们、理解它们,这个很主要。
这段履历对我来讲起到了两个浸染:
一是跟我在中国所感想熏染到的和看到的“中国聪慧的存在”起到一个“对照”的浸染。在法国巴黎学习演习的那段韶光,我常常出去旅行,每次旅行会请个假,管演习的老师对我很不满意。有一次我走得比较远,目的地是意大利和希腊,要请个长一些的假,然后他说:你旅行可以,在你的卒业报告要写出来这一段。后来我的报告中就干脆写了这么一章:只有到了罗马,才能更好地认识巴黎。
绩溪博物馆
当你到了其余一种文明或者不同的文化环境、城市和建筑环境里面,你才能够更清楚地认识我们中国的城市、建筑和空间环境的特点,它“聪慧的独特性”在什么地方,它对付人这个物种意味着什么。两者之间有对照,就意味着既有差异的地方,又有相似的地方,“相似”是意味着一种人类文化的共通性,只不过大家用不同的办法来表达和创作。
威尼斯纸砖房(40㎡)
璧园(40㎡)
二是“出去看看”,还让我深刻认识到城市和建筑真正的“当代性”在什么地方,这是我在中国不可能认识到的。由于,“当代”和“当代” 的根源在西方,在欧洲,真的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城市和建筑的当代性:你或许以为你在做一种很当代的事情,或者你认识到了这便是中国传统中的当代性,而这种当代性究竟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当代性?这须要亲自去真正当代的环境中去体验才能认识到。
-
“鸟巢”的产出过程,给了我“当代性”的深度体验
也是两种不同语境的深度对照
“内在”的那部分也很主要,内在里的“文化部分”会是一种勾引,文明或者文化迹象里的贯通性让我有兴趣,从而要出去,追根究底地问,考试测验找到或者佐证根源的存在,再去推敲该用若何的表征把它表达出来,这件事才有了意义。要不然既没有快感,也没故意义。我探求这个东西,带有一点自我精神的向外,又带着一种当代精神向外的一种状态。我们渴望互换,但是,我们也希望找到属于我们的“根源”。
鸟巢
“鸟巢”项目这种跟国外建筑师的互助,一样平常人会以为我这是给老外打工,我乃至都没有把“鸟巢”列入到我最近出的作品集里,但我以为它对我来讲,依然非常主要,我也越来越认识到这个经历的主要性,而且,我永久也不会忘却这段互助的经历:一次文化层面上的真实碰撞,不同的建筑师,来自不同的文化语境,在共同关心同一件事情的时候,态度和做法上都是如何的不一样。
这种文化的碰撞,是一种特殊的深度对照,在全体过程中能更深刻、细微地认识到这种文化的对照,这里的差异性和共通性,通过一个项目的办法,事无年夜小、详细而微地表示了这种碰撞的状态,同时也加深了我对建筑当代性的真正理解。
鸟巢
赫佐格与德默隆绝对是西方当代建筑师的代表人物,他们怎么做项目、对艺术的意见、怎么研究材料、材料是怎么在西方语境中把当代性呈现出来的等等,这些于我而言,是特殊详细而又真实的一种认识,从2002年底到2008年,我们一起为同一个项目事情了将近六年的韶光。
“鸟巢”,在中国是一个当时有争议的项目,本日看来这种争议越来越少了。由于它成了一个奥运会的焦点,它不仅仅是一个体育场,也是举国高下集体精神的一种知足,国家开放性、自傲心的表现,又创造了一种新的城市文化景不雅观,同时它又代表着当代中国,也是对新北京的解读和象征,这都是项目难度和履历的一部分。但社会关注度上带来的这种压力与寻衅以及详细构造技能上的寻衅,包括我们设计工具和设计方法的重大变革等等,有了见证和体验的这么一个过程,也可以说是一种职业与人生的体验,以是,这个对我来讲是特殊宝贵的一段履历,很主要的一次高难度的自我打破和寻衅。
鸟巢
做完“鸟巢”之后,我以为没有任何项目可以在我面前构成寻衅性了,就像一个登山家爬过珠穆朗玛峰之后,他会以为所有其他的山峰不再能再对他构成难度一样。但对我来讲,更主要的是一种深度的体验,这与作为一个察看犹豫者不雅观察的深度是不一样的,完备超出预想的一种建筑文化碰撞和应对,通过这样一种办法,我更能够深刻认识前面我提到和感想熏染到的那些有历久魅力的营造聪慧,我也更能深刻觉察到那种贯通的哲学和文化,它的主要性或者详细的力量在什么地方。
-
参与“鸟巢”的出身,并非幸运
我记得2003年那时候特殊想出国:我从2000年开始当院总,2002年的时候跟法国建筑师做过另一个互助的项目,我以为可能事情到了一个“瓶颈”期间,不知道专业上该当往哪些方向提升。大概是潜意识里意识到在我们的文化语境里面,我彷佛看不到更多的深刻性在里面,或者是基于当时的眼界,无法从这个路子上去提升了。我还想请赫佐格和德默隆两位师长西席做我的推举人。
与赫佐格与德默隆事务所建筑师一起制作“鸟巢”竞赛方案模型(2003年)
他们当时都在哈佛大学GSD任教,我在瑞士巴塞尔事情的时候就跟他们提过推举信的事,他们当时也答应了。直到2003年“鸟巢”项目中标,我跟别人也说过:既然这个项目已经有了却果,算是告一段落,我要准备出去了。但这个时候德默隆师长西席说服了我,给了我一个不能谢绝的情由,终极还是没出成国,而是在“鸟巢”这个项目上留了下来。
他说:咱们一起互助便是你最好的学习机会,即便是你去再顶尖的设计院校,哈佛也好,耶鲁也罢,紧张也只不过是随着老师们做课程设计studio。这两位建筑师自然是最好的老师,“鸟巢”又是一个顶级的项目,个中的体验和实战履历是别的项目所不能比的。以是,我相称于读了六年的“研究生”。这次履历,对付我该当是一次“身心深度的加强”,也是一次可以对建筑进行深度阅读的关键经历。
这是一个迁移转变点,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决策和选择,就犹如毕业时没出国直接到设计院事情,做“鸟巢”也是一次很主要的选择。
有人会说:我是幸运儿,我并不认同。在做“鸟巢”之前,我已经是部院的院副总,虽然很年轻,但是我也已经有很多的事情经历了,也已经得到过建筑专业层面主要奖项切实其实定,算是有点小名气了,比如,当时跟齐欣等建筑师一起在《北京青年报》的整版系列宣布,也参加一些重大的竞赛,包括:中心电视台、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博物馆、西直门交通枢纽等。以是,“鸟巢”的互助,对我来讲是一个迎刃而解的事。
与J.赫佐格和P.德默隆“鸟巢”现场谈论(2007年)
赫佐格与德默隆是第一次跟中国建筑师互助,开始做竞赛的时候大家也并不知道“鸟巢”能不能有后面的成功,他们以前做的大都是一些小项目、小房子,在中国的官方语境里看着轻微有点“特异”。但我以为还是有一些一定性,也有院里崔总等领导对我的提携和大胆利用。我去瑞士互助竞赛和之前法国学习到后来跟法国建筑师一起做项目,实在都是被崔总发起引荐的。
当然,竞赛能赢,既有建筑师自身作品的独特性,这里也有幸运的身分,可以说是一个幸运的结果;而且遇上2003年那个时候的中国具有亘古未有的国际视野和开放状态,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时期背景是有关联的,以是,怎么能说不是幸运呢?
胜景几何,是创造“自然而然”的建筑
2008年之后,我有了真正比较独立的事情习气和状态。事情室2003年就成立了,中间只能因此“鸟巢”的事情为主,占用了大部分的韶光和精力,以是,也只能做一些零散的小项目,以是,我想2008年往后得把韶光赶回来。不过现在我对那段韶光又有了新的认识,这次合为难刁难我的独立事情有着重要的浸染,也须要进行一次思想层面的聚焦与重构。
从2008年到2020年,这十几年间的韶光是一种过渡与沉淀,准确地说:“胜景几何”理念是这十几年一贯在思考的工具,也是一种状态。
瞬时桃花源
2010年之后,又看了很多的村落庄。我开始有一种“贯通”的意识,可以把这么多年来对传统城市、建筑、园林、聚落的不雅观察和研究,通过实践中的不断考试测验进行更有深度的认知,然后,逐渐贯通起来,也便是把对事物实质的认识从文化理念上把它们贯通起来。这时候,我也有机会做了一次总结,整理一下自己瞥见过的和考试测验过的,也就很自然地涌现了“几何”与“胜景”这么两个关键词,它们代表了多年来我的全体认知系统。
楼纳露营基地做事中央
2013年,以方家胡同的“微展”为契机,将我所“贯通”的认知系统浓缩到“胜景几何”这个词上。今年这个展览的主题还叫“胜景几何”,还有一套书的出版,也是一次对自己多年以来的事情更为系统化的总结。非常大略的一句话:胜景几何,是设计或创作建筑与自然之间的交互,设计或创作的结果即是可与自然交互的建筑。
胜景几何展(2013年)
这个“自然”有两层含义:一层是对“自然”本身观点的扩展,它既是荒野自然,也是人工自然;既是原生自然,也是文来日诰日然,这样就可以把当代人的生活环境涵盖起来——当代人,并非生活在纯粹原生自然的环境中,而是更多生活在人工自然的环境——无论城市和村落庄都是比较人工化的环境。如何对待这些不同的“自然”环境,或者建筑如何跟这些不同的“自然”环境相交互——它们之间要发生互动和更为密切的关联,这是“胜景几何”要回答的问题。
“胜景城市”图 李兴钢绘 - 旁边滑动查看更多
其余一层含义便是“自然而然”,这是我希望自己能够达到的一种境界,也便是事情意图、事情状态和事情成果的自然顺应与接壤,从而造诣一种“自然而然的建筑”。以是,一个是与自然交互的建筑,一个是自然而然的建筑,末了,我称之为“自然的建筑”。
沉浸式体验区现场(2020年)
“自然”关键词现场(2020年)
“胜景几何”,意味着一种“自然的建筑”。《行者图语》那本书里的总结性语汇、草图以及一系列片段性的感悟,大都来自于对城市、建筑、园林、聚落的“野外稽核”,这样深度的场景性的“渗透”与“不雅观察”,既延伸到中西方的现当代建筑,也延伸到我自己的日常事情之中。
“胜景几何”导览图 - 旁边滑动查看更多
聚焦到《胜景几何论稿》这本书,那些片段性的感悟就变成了相对系统化的思考,我做了一些凝炼,比如:“风水形势、人作天工、构造场域、叙事空间、胜景情境”这样的一个系列,它们构成“现实空想空间营造范式”的五个有机构成要素,实际上是对 “与自然交互的建筑”或者“自然而然的建筑”在设计方法论层面的延伸和详细化,以此构成了“胜景几何”这个理念的核心内容。
“自然”的建筑,实在,是在西方经典建筑体系中“坚固、适用、愉悦”的维特鲁威建筑三原则的根本上加入了第四个原则,叫作“自然”。“坚固、适用、愉悦”之间是有关联性的,只有坚固,才能够达到人类庇护所的目标;适用,是要适宜人的利用以及人在个中的生活;适用的含义里,再作出一个层面的提升便是愉悦,不仅是物质层面的舒适,还假如一种精神层面的愉悦。如果我们的建筑还有一种“自然”的原则,自然而然又与自然交互,那么,带给人愉悦的层次就可以提高,以是,“坚固、适用、自然、愉悦”,是我们事情中的建筑四原则。
“不雅观、想、做”三本书 ©不雅观点
以上所说,便是“胜景几何”这四个字所包含的紧张内容。当然,胜景几何?它也是一个问句,“几何”在中国汉语里又是 “多少”、 “若何”、“如何”的意思。这于我而言也是一个自问。便是说,我所追求的“与自然交互的建筑”或者“自然而然的建筑”,是不是真的做到了?做到了多少?做得怎么样?这是一个开放性的命题,也是一个须要努力达到的目标。这里的“自然”,既包含了空间,也包含了韶光。
胜景几何展览现场(2020年)
或许这个命题用笔墨表达出来的时候,也造成大家的误读,会有太多的不愿定感,但正好是这种“误读”,也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我们或许真的须要造就一种更加开放的状态,太明确的东西也就没有什么生命力了,它反而是一种失落去,以是,为什么我喜好“胜景几何”,这个词它不论是作为名词的陈述状态呈现,或是作为一个问句的迷惑状态呈现,都是一种相对模糊的状态,我以为这便是最自然的一种状态。
月野亭下(2020年)
不给定论或许才是对的,就彷佛每一个跟你聊起这个事的人,都成了一个同语者,他也自然参与了你的发声场,或者有一种“共同觉醒”的履历,策展是一个视角,或者说是一种“偏见”和“侧写”,有趣的是可以“同语或者不同语”,但却可以“同问?而不趋同”,这可能也是建筑里一贯都在发生着的状态。
李兴钢在国家雪车雪撬中央屋顶(希望自己能保持一颗少年奔跑之心,永一直歇)
本文图片由李兴钢事情室供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