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豪中(通讯作者),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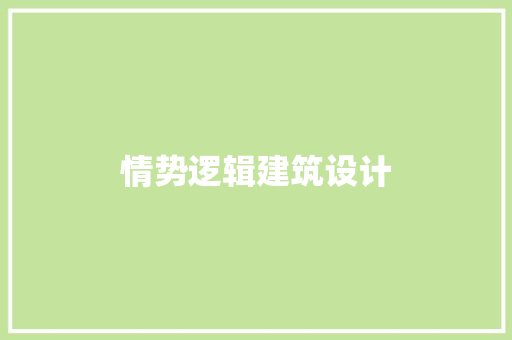
本文摘自《机器与社会空想:莫西·金兹堡的构成主义功能性设计方法逻辑探析》,原文刊登于《建筑师》杂志2024年2月刊,总第227期P86-92。头条版已略去文中所有注释、图片来源、参考文献等信息,正式版本以原文为准。
本刊所有文章均已在中国知网、国家哲学社科文献中央、超星、万方、维普等数据库上线,用户可自行下载阅读。引用格式:吴寒,杨豪中. 机器与社会空想:莫西·金兹堡的构成主义功能性设计方法逻辑探析[J]. 建筑师,2024(01):86-92.
20世纪20年代,金兹堡面对新旧风格之交替、艺术与技能的争辩提出了一种集社会空想与机器性为一体的建筑设计方法——“功能性设计方法”,其成为各先锋思潮在建筑本体域的一次聚合与主要接驳点。然而鉴于政治成分之参与,功能方法一度在建筑历史理论研究中处于失落语状态。文章将从功能方法之历史时期特色出发,探究其思想之源并着重探析其以社会空想为目标、内化于机器生产逻辑的机器范式,揭示其对构成主义建筑理论与当代主义理性设计方法的主要奠基浸染。
目录概览
一、弁言二、回溯历史三、功能性设计方法的思想之源四、机器范式——从机器到社会凝聚器的必要路径五、结语
一、弁言
20世纪初期是当代建筑前的主要摸索期间,关于当代风格始于“艺术还是技能”的辩论始终哓哓不休。先锋派对新风格之探索亦辗转于机器化与形式美学之间,无法达成二元之统一。苏联建筑师金兹堡则另辟路子,率先从思想上解脱了形式之桎梏,从“物质与社会双重修构”的时期特色出发,首创了一种全新的一元性建筑思维新方法,为新风格的探索开辟了一条新思路。
金兹堡(Moisei Yakovlevich Ginzburg,1892—1946)是20世纪初期苏联当代主义理论家兼建筑师,其于20世纪20年代陆续在《当代建筑》杂志揭橥了一系列关于功能性设计方法的文章(表1)。这一方法一经面世便备受推崇,成为构成主义的创作纲领。该方法根植于金兹堡早期关于建筑风格的思考,领悟了时期特色,并发展为一种以社会空想为目标、内化于机器生产逻辑的机器范式。虽然其存续韶光较短,但其直接启示了列奥尼多夫、汉斯·曼耶等建筑师,并成为构成主义理论与当代主义理性设计方法的主要基石,对包豪斯乃至全体当代主义产生了主要影响。
二、回溯历史
1.时期背景:一个双重构建的时期
“构成主义建筑,或者说功能性设计方法出身于我们的时期——一个双重构建的时期。”十月革命后,苏联在社会革命与工业发展的双重刺激下,引发了新的社会经济关系并试图将新的文化生活不雅观念引入公民日常生活,开展物质生产与日常生活的双重培植。苏联此种社会空想同样使令早期构成主义艺术向生产主义转化,罗申科、阿列克谢·甘等生产主义者从早期以加博、佩夫斯纳为核心的“抽象”构成主义中剥离,试图建立真正与社会秩序符合的“实用”构成主义。
作为社会革命后的第一代青年建筑师,金兹堡于1923年与A·维斯宁结识,并从构成主义生产化潮流与马克思主义美学中汲取了养分。他敏锐地洞察到建筑之社会职能,主见将培植新生活(zhiznestroenie)作为当代建筑的目标,并呼吁建筑不应成为“生活的装饰者”,而是“生活的组织者”。在他看来,建筑师之职责在于合理组织日常生活并尊重设计逻辑之自主性,以达成建筑形式、功能、技能、构造与社会需求的同等。
2.学术背景:一个多元聚合的时期
20世纪初期,战役爆发时局动荡,欧洲各国思想激荡开启了钻营变革的艺术先锋探索。诸多先锋思想在接管传统学院派教诲的金兹堡心中掀起了波澜。当金兹堡在米兰艺术学院求学时,正值未来主义在意大利盛放,彼时他已开始逐渐背离传统学院派触及先锋思想,将未来主义的“运动”、“速率”、“机器化”观点融入自己的建筑理论体系。完成学业后,金兹堡前往克里米亚,在设计实践中深入思考“究竟是传统还是当代”的命题。1921年,金兹堡回到艺术先锋思想争辩激烈的莫斯科,开展传授教化和学术研究事情,开启关于当代建筑的新旧风格之思。1923年金兹堡与构成主义艺术家维斯宁兄弟相识,从此金兹堡在构成主义中寻得了理论共鸣,并致力于在建筑本域发展构成主义理论。
次年,金兹堡揭橥了《风格与时期》,其立足于历史蜕变理论指明唯有触及时代之实质,方可通向建筑新风格。在工业生产发达发展之际,金兹堡与德意志制造同盟、未来派一同将希冀的目光投向机器与工业建筑,然而其规避了机器形式与生产的出发点,反而以机器之自然逻辑为原型,首创性地提出应该构建一种“清楚条例的组织方法”以“战胜并改造迂腐的建筑思维系统”。事实上,金兹堡的某些不雅观点并非首创性的,他的贡献在于,其吸纳了多元先锋理论中的旧不雅观点并将之综合到一个新的建筑组织方法模型中。这一方法终极构成了贯串衔接先锋派理论宣言和当代主义建筑实践的桥梁,并成为各先锋思潮在建筑本体域的一次聚合与主要接驳点。
三、功能性设计方法的思想之源
1.从历史出发:理论根本
针对20世纪20年代苏联普遍存在的“混乱主义”,金兹堡提出了一种既不盲目崇拜古典建筑亦不武断摒弃历史的辩证唯物主义路径,其从德国古典艺术史学家沃尔夫林和弗兰克尔的论著中寻求风格研究的方法与模型,建立了风格蜕变理论,并揭示了其内在动因与外在推动力,即“延续性”(continuity)与“独立性”(independent)。金兹堡认为,风格之发展是连续的、迭代的,螺旋向前的,其间定然存在某种延续性,而“独立性”则作为一种诱发生发火风之变的外部推动力与探究时期精神的依据。
从历史中寻求启示并非金兹堡之独创,无论何时从历史样式中寻求灵感的建筑师均非少有,但鲜有建筑师可兼具艺术史学理论之思与建筑实践之行,金兹堡思想之独特性便在于此。金兹堡立足于史学理论,以艺术风格史学研究为方法,探寻蜕变之规律与动因,并终极据此确定了新风格的详细方向。金兹堡坚信,当前时期的建筑新风格应该源于时期之标志——机器、机器化生产以及劳动,此类标志性元素将构成新风格的主要决定成分。
2.从机器出发:逻辑根本
19、20世纪之交,机器与工厂如雨后春笋般蔓延欧洲大陆,快速行进的列车以及工业文明的发展给欧洲社会带来了冲击。意大利未来主义者清晰而准确地捕获了这些变革,并授予其积极美好的未来愿景。马里内蒂与圣·以利亚揭橥了未来主义建筑宣言并开启了一个狂热的机器象征与技能崇拜时期。同样从机器化中探求时期之声的还有德意志制造同盟,其匆匆使建筑师与生产性企业之间建立了联系,呼吁“标准化美德”。只管未来派与德意志制造同盟均受启示于机器,但两者各自着眼于机器形式与机器生产,并未构建真正基于机器逻辑的建筑理论框架。
然而金兹堡不仅深刻意识到了机器对付人类生活办法的空前改变,而且深入阐发了机器内在逻辑,并将之类比于建筑设计过程。金兹堡将建筑创作视为一个目标明确的整体性活动,从建筑任务存在伊始,建筑的基本物质要素及其干系的社会文化要素均呈现为整表示象的不同表现方面,而建筑师的任务便是类比学习机器的有机和谐组织,将建筑创作分解为多个相互浸染的部分,并根据目标所约束的必要性原则将之合理组织,以确保其各部分与目标的有机统一。金兹堡对建筑创作实质的认识条件决定了其由机器逻辑出发的机器范式,而并非“机器形式的狂热风格化”或单一标准化模式的建立。
四、机器范式——从机器到社会凝聚器的必要路径
1.功能方法的目标——社会凝聚器
在十月革命后的前十年中,金兹堡深刻意识到当代建筑师的目标:开拓新的建筑类型,创造当前时期的“社会凝聚器”(social condenser)。此目标表示了非传统类型学意义上的建筑设计思维,其预先设定某种基于时期社会任务的建筑类型,根据实际需求对建筑系统的各个部分进行理性剖析,从而构建建筑形态,即“形式是一个未知数X”。
金兹堡从不承认形式的固定化,其思想与阿列克谢·甘(Alexey Gan)之“形式必须回应或适应社会进化”异曲同工,他强调建筑师应通过功能方法顺畅地回应社会需求,遵照设计方案的逻辑演化,以达成形式与时期精神的同等。而“社会凝聚器”这一观点则表示了金兹堡授予建筑的乌托邦空想,他将建筑类比为一个容纳人们集体生活文化的容器,并借助这一详细物质形式影响人类的感官和生理认知,勾引行为,匆匆成一种集体主义的生活办法与劳动生产模式,期望以建筑为介质重组日常生活,重塑社会关系。
功能方法匆匆使建筑成为一种与社会日常生活机制相契合的工具,其将建筑目的与社会目标相领悟,并基于此种目的性建立了一种从功能需求导向形式的逆向类型化。这种基于社会意识形态的新型类型化思维启示了后当代主义关于空间文化的理论转向。20世纪60年代,列斐伏尔通过法国建筑师库普(Anatole Kopp)重新发掘了这一观点,并在“建筑空间勾引生活办法”的根本上指嫡常生活对空间的反浸染,提出了三元辩证的“空间生产”理论,进一步重构了社会、建筑、利用主体之间的空间关系。
2.功能方法的内在逻辑——机器范式
穷究金兹堡思想之内核,机器范式无疑成为实在现建筑社会职能的不二基石。金兹堡借阿尔贝蒂之话语表达了机器之时期性“机器匆匆使我们清晰和精确地表达创新性想法”。在金兹堡的理论构架中,其将机器整体与局部间的有机和谐原则类比于建筑,将建筑过程分解为有机而独立的多少进程,其间各进程环环相扣,共同参与并构建了建筑设计全过程。
自此,建筑设计将不再是基于潜意识与直觉的结果或是对先入为主的形式模拟,建筑师将成为问题的办理者,对付某些既定成分与未知成分对应的问题提出明确的空间办理方案,使建筑适应利用者的特定社会需求。这种依次推导的过程将平面组织视为实现空间有效用场的主要方法,其次合理考虑实现空间组织的施工方法与材料构造,迫使建筑师思维模式转变为由内而外的办理过程。同时,建筑师不仅要办理建筑内部的空间问题,还应该向外延伸,将建筑的体量作为城市空间办理方案的核心,理论上该方法的工具适用性匹配于全尺度的设计方案。
与旧有设计过程常日导向功能与形式的抵牾或疏离不同,功能方法使建筑设计过程从一个问题自然流转于另一问题的思考,此中并无任一元向来自主不雅观臆想,统统结果均遵照逻辑链条之理性推导而成。金兹堡利用功能方法主导了由其卖力的两次社会主义住房探索。
在始于1926年社会主义住房探索中,金兹堡利用问卷调查的科学方法探索苏联新型工人住宅,他分别针对民众与行业专家开展社会主义住宅的调查,评估集体化在塑造新型生活模式的潜力,基于民众需求与社会主义培植需求开展住宅探索(图1、图2)。而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工业化发展导致工业建筑与住房培植资源分配失落衡,面对住房危急与建材短缺,金兹堡与苏联国家经济操持委员会基于功能方法重新提出一种以当地建筑材料预制而成的廉价住宅方案(图3)。鉴于该方案可针对居民的隐私需求与个人生活能力的变革灵巧装置(图4),便于适应详细的社会主义生活模式,该方案被视为有效改进苏联社会问题的详细手段。
图1:1926年工人住宅竞赛金兹堡方案
图2:1926年工人住宅竞赛金兹堡方案住宅单元剖析
图3:巴什基尔的社会主义住宅(模型),1929年
图4:建筑单元的装置式图解,巴什基尔的社会主义住宅
相较而言,只管两者年代靠近,但鉴于其时代经济特性与社会需求的差异,两种住房实践在平面组合、建造办法、形式材料等均表现不同(表2)。此中差异揭示了功能方法的事情路径:以社会目标为主导,基于不同背景条件展开理性剖析,匆匆使建筑实践回合时期需求并合理组织建筑各要素形成理性对策。由此路径可嗅探至功能方法“以问题为导向”的实质特色,且其反响了“功能性”中的某种“客不雅观性”。艺术史学家阿道夫·贝恩在其著作《当代功能建筑》中曾将“客不雅观性”(Sachlichkeit)诠释为“问题的大略、实用、直接的办理方案”,显然该释义与金兹堡之路径实质不谋而合,但应指明金兹堡并非持机器化不雅观点的功能主义者,其“功能性”思想并非继承于狭义的功能主义,而是一种根植于历史唯物不雅观的设计思维范式。
金兹堡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主要阐释者普列汉诺夫处寻得了启示。普列汉诺夫是第一位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利用于文学和艺术批评的俄国政论家,在金茨堡的时期,他成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主要来源。普列汉诺夫的艺术功利论主见艺术应该促进社会的繁荣发展,即“为社会而艺术”。
金兹堡则进一步发展了此不雅观点,在他看来,构成主义建筑的美学特色超越了主不雅观的视觉形式而导向一种社会学层面的客不雅观性。一方面,其表示在建筑终极态形成过程中的理性推导逻辑链中,即“问题导向”中;另一方面,其建立在利用主体对建筑空间的感知根本之上,即金兹堡所谓的“建构性与审美性的有机统一”。详细而言,金兹堡认为,建筑师凭借知觉履历“将构造力量与人的内在天下履历相联合创造了一个有机的形式天下”,从此构造系统不再是置身事外的独立构造,其因人自身的生理生理机制特点而与人类建立繁芜的联系,由此产生了一个形式天下的审美系统,个中同一建筑要素同时具备了却构与审美的双重特性。
此种美学特色在构成主义建筑实践的领头人维斯宁兄弟与列奥尼多夫的作品中得以阐释与延续。作为构成主义第一代建筑师,维斯宁兄弟长于从“问题导向”出发,在办理功能问题之条件下,构建符合社会生产需求的物质环境,并通过考虑建筑要素的社会意义实现“功能与造型的统一”。其早期竞赛项目劳动人民文化宫被金兹堡称为“构成主义建筑的里程碑”(图5),“它第一次在建筑作品中表示了建筑新方法的有机原则,且其并非模拟于某种固有模板,而是源自关于实际问题的办理。”
随后,维斯宁兄弟之诸多改造性的创作实践,如:在水平连续凸窗知足采光功能与视线互换之双重需求的第伯聂水电站项目中(图6),匆匆使功能方法被广泛利用并成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建筑师加入构成主义阵营。被称为“构成主义的墨客”的列奥尼多夫便深受A·维斯宁与金兹堡之影响,其在技能至上的形式元素根本上架构了理性思维之桁架,与前一代建筑师对内在逻辑的关注比较,列奥尼多夫更关注理性化的形式要素。在当代建筑师协会第一次会议上,列奥尼多夫在功能方法根本上提出了一种“新型工人俱乐部”(图7)。
其将科学、展览、体育竞技、政治组织事情等功能置于由玻璃、混凝土构造组成的外壳中。在他看来,以往的工人俱乐部并未真正实现工人文化生活的重组(图8),其主见通过当代科学手段赞助建立工人阶级新文化,并以一种超越现实的技能空想授予多元功能以新兴的表现形式,由此实现了超技能下“建构与审美的统一”。
图5:维斯宁兄弟劳动人民文化宫方案,1923年
图6:第伯聂水电站水平长窗,1927—1932年
图7:列奥尼多夫的新型工人俱乐部方案立面图及平面图,1929年
图8:奥尼多夫对原有俱乐部的否定
3.机器范式的空间表现——功能空间组织
于金兹堡而言,建筑之实质源于其庇护之基本用场,建筑师借由物质要素的围合产生空间划分,由此构成建筑形式。由此可见,金兹堡将建造目标与建造手段视为空间组织的优先层级。在其组织过程中,金兹堡基于机器生产流程与生活生产过程的类比,提出了功能空间组织办法。
机器被金兹堡视为一种布局逻辑明确,目标清晰的有机体,其创造者通过生产流程图解、机器装置图示等渗透工业生产活动的变革。受到美国实业家亨利·福特当代汽车工厂模式的启示,金兹堡将研究视野转向人类生产生活的运动轨迹,将工业生产的组织原则运用于设计过程。透过赖特与布鲁诺陶特的平面组织,金兹堡确信了有效功能在建筑整体中的可整合性,并提出“功能流程图解”与“设备方案”两种基本空间图示。
工业建筑中生产或劳动过程是动态连续的,其由多少独立的运动定向组成,因而生产系统可借“功能流程图解”表达生产过程的从属环节。与之对应,这些详细劳动操作干系的机器和设备系统则通过功能流程图解供应的信息组织这些机器的位置,形成了金兹堡所谓的“设备方案”。工厂的生产过程本色上是一个生产与日常生活办法(byt)相结合的过程,人的行为被划分为诸多节奏片段,动态流程被凝固在空间中,建筑师将此静态节点与建筑环境建立理性联系,这项事情越精确完全,末了的办理方案便越贴合社会需求。
只管生产过程每每发生于工业建筑中,但日常生活中的必要活动与基本生产流程具有根本性关联,因此,金兹堡将这类“功能流程图解”利用范围扩大至其他类型建筑中,如公共住宅、俱乐部、剧院、电影院等,他们均可类比于工业综合体将其实际用场进行阐明、分类、阐明并归入功能流程系统中。以电影院所应具备的多少实际用场为例,其基本空间图示如图9,从入口大厅到终极不雅观影结束,这一个过程通过各举动步伐确立运动的目标,将动态流程分解为独立的静态时候,功能方法通过举动步伐的排列组合抽象了平面空间的组织逻辑,定义了电影院的空间形态基本构成(图10)。
图9:电影院功能流程图
图10:由功能流程图天生的电影院平面图
这种“功能流程”与“设备方案”双重叠加的办法不仅有效描述并预设了建筑中的利用目的分布,而且以科学方法提高了空间利用效率——通过对利用者运动轨迹的研究,秉持经济原则将设备家具分布在运动轨迹的封闭链条中,使得利用者以最小位移实现最大的空间利用。至此,建筑师已借由物理空间组织回应了社会需求,其后将设计方向转为以知觉感知、形式转换为必要规则的构成形式逻辑演化,从而匆匆成整体建筑的天生(图11、图12)。
图11:纳康芬大楼户型F功能流程图,比例图解
图12:纳康芬大楼户型F平面图
值得把稳的是,功能方法在发展过程中涌现了定量化趋势——主体行为与平面组织的定性关系被建筑师克拉西尔希科夫(Nikolai Krasil'nikov)发展为一种基于数学剖析与科学效率的定量方法。其指出建筑师应该“以最大限度的精确性和量化渗透全体设计进程”,他企图以大量关于建筑形式与生产过程的数学公式与图表阐明其思想的合理性。只管此举有助于发展一种数字化仿照的设计方法,但是从当时的技能发展水平而言,其分开了现实并将功能方法导向一种极度功能主义。
与之相似,我们同样可以在20世纪30年代汉斯·曼耶的建筑设计思想中窥见这种类似的“极度”。曼耶在任职包豪斯校长期间,秉持一种“以科学知识为根本”的理性设计方法,主见通过“功能流程图解”明确平面组织的理性推导。1928年,其提出了“功能乘以经济”之论断,认为设计应从实际需求出发,并以经严格推导而得的空间生产效率为依据。曼耶对功能方法的片面性继续与发展匆匆使功能方法被拆解并融为当代主义的主要组成部分,构成了当代建筑设计过程中平面流线推导之雏形。
不幸的是,功能方法在苏联的发展随着政治场合排场的变动以及关于对其的各种误读逐渐结束,该方法被诬陷为成本主义的工具,被视为受困于空间经济效益桎梏的产物。在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之间,这一方法被汉斯·曼耶等新客不雅观派建筑师片面发展为当代主义的理性设计方法,并且在苏联建筑天下一度失落语沉寂。直至20世纪60年代学界对东欧建筑历史的重新发掘才催生了对功能方法社会生产层面的研究。
五、结语
作为20世纪20年代的先锋建筑师,金兹堡从建筑历史本体出发洞察时期特色,立足于双重构建的时期背景,以“集体凝聚”的社会空想为紧张推动力,构建了以机器范式为特色的功能性设计方法。这一方法冲破了艺术与技能对立的二元不雅观点,建立了以马克思主义美学为核心的“建构性与审美性的有机统一”。同时,该方法是金兹堡十余年对当代建筑新风格探索的结晶,其领悟了以机器化、艺术形式为出发点的先锋思想,成为弥合“先锋”与“当代”之鸿沟的主要媒介。
纵不雅观历史,功能方法之后续影响紧张存在两种趋向:其一,基于功能流程的理性设计思维;其二,导向社会职能的空间生产趋势。这两种趋向源自时期之“双重修构”,并在功能方法中得以聚合,然而在被后人解读与研究之进程中,其集机器性与社会性为一体的一元整体性常常被忽略,导致其对后世学界之启示被一分为二。本文对功能方法的还原性研究有助于从根源性阐明功能方法之一元性,避免单一趋向化的理解。究其根本,功能方法并不拘泥于从单一问题层面办理繁芜任务,而致力于构建一个符合时期发展的“社会凝聚器”。在建筑符号化愈盛之当下,这一方法将启示建筑师思考如何以目标为导向关怀新时期的日常生活,定义新风格的建筑程序模型,实现社会组织的空间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