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大众知·美术馆\公众建筑完成,我该当是第一批慕名前往的不雅观众。却由于建筑内部还没有开放,对付美术馆只留下了外不雅观的根本印象,当然没有资格写下什么。有幸的是建筑写作于我而言并非职业,大多时候便是个人的事情,当一个建筑自己还看不清时,选择等待是最大略的办法。
没曾想到这一次等待竟然靠近五年。直到知美术馆经由多年的调度和预备,以\"大众开\"大众为名的艺术群睁开幕,美术馆迎来了正式开放的一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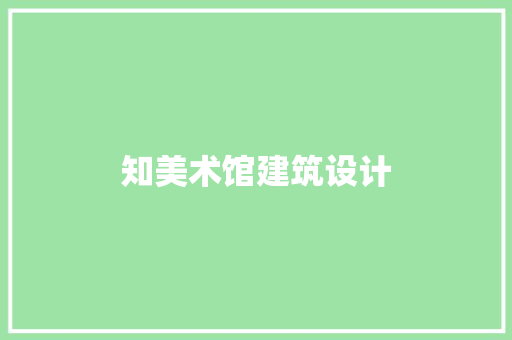
\公众开\"大众展确当天,微微颠簸的水面将阳光反射到美术馆建筑上,在大块玻璃和外挂的中国瓦之间映出摇荡而不愿定的光斑——成都难得的骄阳将建筑润色出最完美的身形,这是我五年中三次来访也没有看到过的场景。
当参加开幕展的一个个俏丽的身影穿梭在不愿定的空间里,当走廊的光影与人影交织在一起,当来自水面的波光荡漾在室内的玄色石材墙面上,羞涩多年的知美术馆终于轻轻地撩开薄纱,向众人露出它最动人的一壁。我心中关于建筑的那根琴弦也随之颤动,有了打开这篇文章的勇气。
建筑师隈研吾
作为日本最具有影响力的建筑师之一,隈研吾有很多让人着迷的作品:根津美术馆、广重美术馆、木桥博物馆,都是我不远千里也要去一探究竟的建筑。同时他也是出色的建筑作家,32岁在哥伦比亚大学做研究员期间就出版了著名的《十宅论》,之后则一发不可整顿:《负建筑》《联系的建筑》《自然的建筑》《场所原论》《我所在的地方》……建筑专著一本接着一本。
他一贯在探索建筑的实质,谈论建筑该当担负的功能和任务,探求新的材料(或许是过去的材料),去实现他对付建筑的思考。他总是用最浅近的笔墨去传播他的建筑理论,他的演议和书本对付包括我在内的建筑从业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直到现在,我对付建筑的基本感知模式都依托于他的理论,而这些感知对付我而言弥足宝贵。
以是当我站在他所设计的知美术馆面前,虽然担心自己没有能力足够理解建筑的意图,却更怕由于我对建筑师个人的喜好而过度理解他的设计。
但有一点却是肯定的,他从来便是一个最重视场所精神的建筑师,总是追求他所设计的作品具备足够的\"大众在地\公众属性。然而,作为一名建筑师,隈研吾却把当代建筑视作一件\"大众恶\"大众的东西。建筑的体积弘大、对物资的花费和建好之后的不可逆转,这是在他的著作《负建筑》中提出建筑令人讨厌的三个起因。一个建筑一旦完成,不但改变全体环境的视觉,乃至改变全体人的生活轨迹和模式。要想一个建筑不成为生活中的\公众恶\"大众,那么建筑师就必须负责地感想熏染建筑所在的场所:
\"大众与'场所'取得联系的建筑,无论其外不雅观如何寒酸、薄弱,都会具有难以置信的顽强力量……'场所'对我而言不是数据,而是肉体的影象。是深入骨髓的空气感、颜色、味道和质感……\"大众
隈研吾对付建筑的感知和肉体的影象,大多来自于他的发展经历。知美术馆坐落在成都南郊新津县老君山下,我不知道这个地方会不会让隈研吾想起他发展的\公众里山\"大众,于我而言这里也是游离在城市和屯子的边界。
而美术馆就在静水中自然地成长出来,在成长中不断地向上倾斜,与背后的山势和所在的园地高差相呼应,形成灵动的、看似随意的围合,当代和不可捉摸的造型和表皮\公众漂浮着\"大众最传统的中国瓦,仿佛建筑师洒脱的一笔划出了城市和屯子、平地和山、未来和过去的边界。
中国瓦如\公众风\"大众
那些漂浮着,如同一匹巨大的布一样平常包裹着建筑的中国瓦,险些已经是知美术馆的最大辨识形象,哪怕你没有来过现场,只是看到美术馆的照片,也一定会对他分外的\公众表皮\"大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隈研吾是重视\"大众表皮\公众的建筑师。\"大众由表皮覆盖'虚空'的部分,随即便成了洞穴。\"大众\"大众用表皮覆盖下的建筑物就会变成生物一样平常自然、开放和优柔。\"大众这是他对付建筑表皮的描述。他的大多数建筑作品,都被表皮覆盖,这些覆盖的画面感也来自于他对日本传统装饰\公众千鸟\"大众的研究。
\"大众千鸟\"大众从字面上来说,是指无数只鸟的意思。鸟与鸟之间保持着间隙,在空中飞行。\"大众我所要追求的正是这般无数的鸟凑集成一群飞行在空中的状态,那些眇小的碎片凑集起来,构成了建筑物一样平常大的整体。\"大众隈研吾着迷于千鸟形式中的间隙力量,光、风和气味从构成建筑的眇小粒子的间隙进入。间隙成为隈研吾为建筑留下的呼吸空间——没有间隙,建筑就会窒息。
而知美术馆的表皮是由数量弘大的中国瓦组成,这些瓦片全部是民间烧制——听说是隈研吾第一次拜访新津时,被周围屯子屋顶铺满老瓦片的美震荡所致。美术馆这些瓦通过一根根不锈钢丝拉吊起来,一片片悬浮在空中,用仿佛被风抚动的状态洒脱地包裹在建筑四周。
在这些形式感上,可以感想熏染到日本\"大众千鸟\公众空中飞行的觉得。但我自己第一次见到这个建筑的这一形式,就以为这些本来作为承载和归流雨水的瓦片,仿佛便是雨水洒落的瞬间或者便是风的状态,被隈研吾固定住了,从而让全体建筑仿佛没有了绝对的顶和侧,给人轻盈乃至失落重的神奇不雅观感。
只有中国瓦,特殊是民间烧制的青瓦给予了建筑独特的个性。这些瓦片颜色不屈均,大小也不一,而颜色和形态的差异给予建筑更大的不愿定性,乃至带一些土气。想起了在日本看到的那些厚重、呆板、大小颜色都同等的日本瓦,虽然它们是抵抗日本常见的大雪和海风的绝佳建筑材料,可是你无法想象把这些瓦片悬挂起来将是若何一种笨重的组合。
隈研吾该当是在知美术馆项目中发觉到了中国瓦的魅力,在之后中国美术学院民俗艺术博物馆建筑设计中,将瓦片这个元素从顶到墙再到地面延续了全体建筑体。只不过在知美术馆,这统统如\"大众风\"大众;而在民俗艺术博物馆,隈研吾表现的更像是一座\公众山\"大众。
\公众洞穴\"大众建筑
站在美术馆主入口,一个包围在建筑、表皮和水系之间的半围合空间,我第一次清晰地感知到隈研吾常常提到的洞穴建筑。\公众洞穴\公众一贯是隈研吾建筑设计的一大主题:
\公众有时我会觉得到自己实在并不是在做一个建筑,而是在思考一个洞穴般的东西……认为'建筑是塔型'的人着重光柱建筑的纪念碑性;相反的,认为'建筑是洞穴'的人则主见建筑中那些连续的体验。\公众
在表皮建筑中间的开放式空间,将全体建筑一层分成美术馆部分和咖啡厅部分。从开放式的洞口向左进入豁然开朗的大堂,沿着建筑成长的形式,盘旋向上或者向下。建筑通过本来的形态约束了人的参不雅观动线,也让空间内显得灵动,充满变革。所有的通道都在建筑外侧,人在空间中相互对视,相互成为被看的作品,所有参不雅观的觉得都是丰富而轻松的。隈研吾再次在建筑中呈现他所推崇的\"大众虚拟透明性\公众,人的行动与外界的光和瓦片的影模糊到了一起,空间本身有了灵性。
隈研吾曾经提过,关于建筑实质的谈论中,最让他有所感触的是马丁·海德格尔在一次演讲中的定义——\"大众建筑是作为桥而存在的\公众,\公众我在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原来令人困惑的一些疑问都顿时迎刃而解了。\"大众洞和桥这样两个实质的不雅观点,看似抵牾,其实在隈研吾的手中得到了和谐的统一,\"大众洞穴\"大众除了作为体验的场所,也和桥一样起到了连接某些事物的浸染。
\"大众洞穴是连接旁边两侧事物的媒介,使得旁边两侧的空间发生对话。在物体间任何人之间以及社会之间就通过这种办法在洞穴的环境中稳定地牵连着。它不像洞穴那样封闭,而是在唤起公共性的同时,光明正大地展示出来。\"大众
就在知美术馆,我见证了一个建筑如何按照隈研吾的设定成为连接事物的媒介。外部的光影,展示的墙体,游走的人群,展示的艺术品,都被\公众洞穴\"大众牵引到一起,建筑在这里变得柔和、温暖,成为了一种将人与艺术品、人与人牵连起来的场所。
老君山的道与自然虽然并不知道隈研吾在新津勘察项目时,曾经去过哪些地方,却笃信他一定会登上老君山,这个玄门主流教派全真龙门派圣地。而就算老君山没有这样的背景,隈研吾也一定会固执地拾级而上,登上这几百级的阶梯,看看这里与他家乡的山是否有几分的相似。当然再高的阶梯也不能阻挡我沿梯而上跟随大师的脚步,抱负在某一个频率和大师有所交集,感知建筑设计源头的精神力量。
老君山的丰富大大超出了我的生理预期。全体道不雅观建筑群沿着山势自然铺开,台阶、道路、建筑都没有那么多严格的规制,依存着山势的发展仿佛自然成长出来——天经地义地避让着山里的树木、大石,山势平缓则平缓,山势陡峭则长出70度的笔直楼梯,到了平台或山壁则长出建筑;有些建筑威严明穆独立平台中心,有些建筑小巧精细与岩穴石雕融为一体。
这险些是道家精神的典范案例。\公众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大众这是远早于西方的\公众有机建筑\"大众体系。不知隈研吾走上老君山的时候到底收成了什么,但在他的设计中,我们看到了关于\公众道法自然\"大众的当代诠释,看到了向重视自然与平衡的道家思想的致敬。
隈研吾是我所见过将自己的建筑学思考和建筑实践结合的最好的建筑师之一。他成长于\公众里山\"大众,虽然身份已经阔别那片故土,但\公众里山\"大众的统统都已经成为了他的肉体影象,朴实而悠长,他的身上可以看到一位建筑师对社会任务的自我哀求。
这些肉体影象和任务,终极造就了知美术馆和一系列的精良建筑,终极也将潜移默化地冲动无数走进这些精良建筑的人。
老君山中的洞穴神龛作为连接神和人类的空间,而知美术馆被隈研吾轻轻地放在老君山下,成为了联系城镇与山之间的装置。由此,老君山从一个快被众人遗忘的角落,拉回到众人面前。
攀上老君山末了一段70度陡峭台阶的大半,小心翼翼地转身,被身后的场景惊艳了——如果只是山头远眺的景致恐怕不会产生这样精细的效果,而老房的瓦顶和树影围合而成的自然窗景让人留下难忘的影象聚焦。这恐怕是人类力量和自然最默契的合营,是建筑最该当有的状态。
一贯在乎建筑与自然的关系,反对建筑改变全体\公众在地\"大众场所,一贯追求\"大众让建筑消逝\公众的隈研吾,一定也在这个危险的台阶上转过身看到了这一幕吧。
总 编 | 邓雪松
主 编丨林育程
实行主编丨程喷鼻香
资料来源 | 《中国古典家具》2018年10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