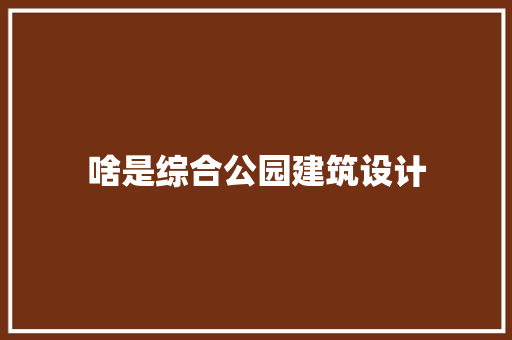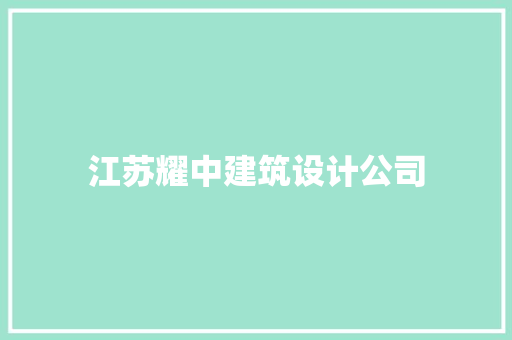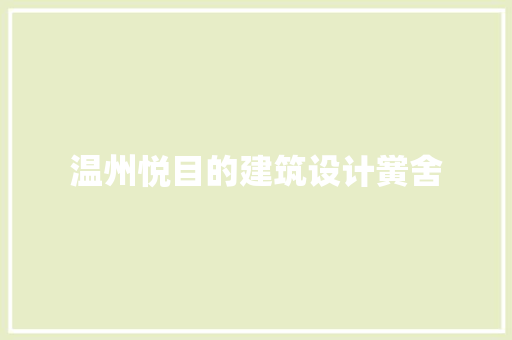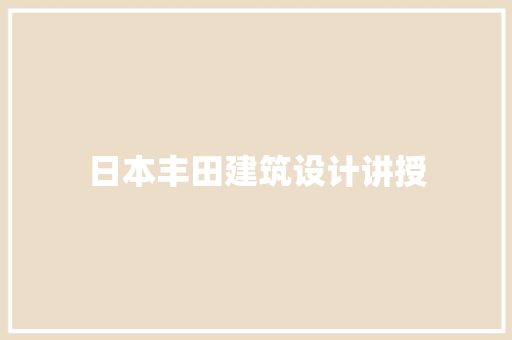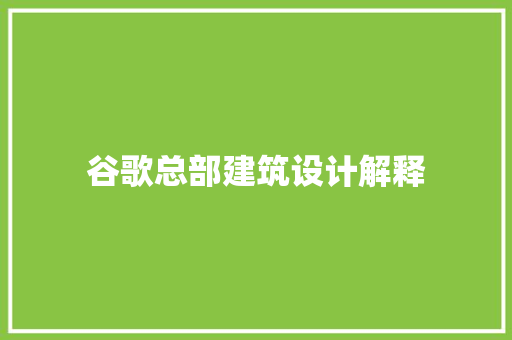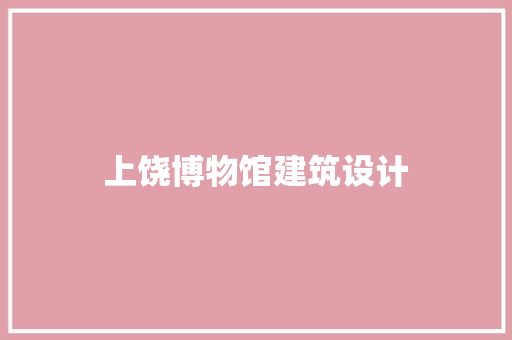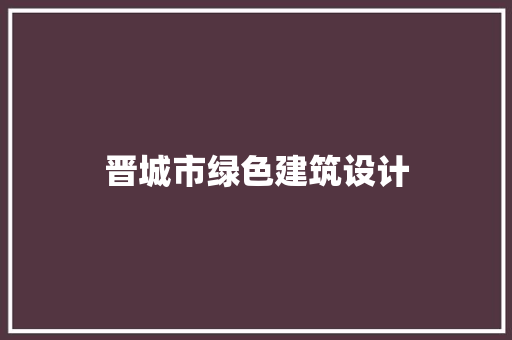1994年,哈佛大学教授苏珊·费恩斯坦写下城市方案领域的经典名作《造城者》,磋商了城市的公正、民主以及多元性理论。今年,《造城者》第二版的中译本首次出版,5月26日,苏珊·费恩斯坦来到上海城市方案馆,与译者、同济大学教授侯丽,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教授王林,中信泰富地产设计总监汤黎明,万科上海区域万晟产品能力中央联合创始人张海涛,上海欧美同学会哈佛校友会理事长曹钟勇展开对谈,畅聊城市发展和对美好城市的方案与设想。
活动现场

城市公道渐行渐远
侯丽先容,苏珊·费恩斯坦本科就读于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文理学院,后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取得政治科学博士学位,如今已是城市方案领域的著名学者。她执教后编纂的历版《方案理论读本》和《城市理论读本》一贯是天下各地方案学生的入门读物。在长期的学术生涯中,她始终关注社会不平等征象,深刻鞭笞城市对特定人群的偏见和压迫。
《造城者》共分十一章,书中包含大量实证案例,例如纽约时期广场和伦敦国王十字火车站中央区项目中公私互助的角力、斯皮塔菲尔兹和布鲁克林中央区的方案方案的效果,以及奥林匹亚与约克公司在纽约炮台公园城和伦敦码头区的开拓进程及兴衰等等。在费恩斯坦看来,西方天下的其他城市从未像伦敦和纽约一样,在1980年代取得如此迅猛的开拓速率,并对环境产生显著影响。在这两座城市中,不仅新的大型办公楼取代了原来中央区较小尺度的建筑,而且在原来空置或废弃的地皮上,不断呈现能干的巨型综合体。
伦敦的码头区和纽约的炮台公园城是1980年代这两座城市经济和社会转型的范例代表,培植定位为金融和高端做事业,它们所拥有的巨大财富更进一步宣示了这两个家当及其从业职员对大都邑经济的主导地位。
“开拓商的决策塑造了伦敦和纽约的物质形态,我的研究目的是理解匆匆使他们作出这些决策背后的经济、政治、技能和文化成分。”费恩斯坦说,她试图通过剖析房地产开拓中关键角色决策的缘由,以及策略、彼此之间的博弈,来探究城市发展的动态过程,聚焦纽约和伦敦,她选择不雅观察那些风险最大地区的房地产开拓活动,同时强调这两座“天下城市”的地位对城市形态和选址造成的影响。
侯丽表示,从1990年代开始,西方城市学者们欣喜地看到在经历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郊区化和内城衰落之后,城市开拓与再开拓重新回到了天下舞台,中央性增强了,城市变得更加聚拢。然而,这种再中央化与传统呼吁的空想模式大相径庭,城市成为投契性培植和空间需求双重压力下的产品。人们期待的生活便利、城市多样、福利均等、城市公道等,正在渐行渐远。
“房地产市场具有周期性,公共部门明显在市场高峰期具有更大的话语权,该当如何在此时利用政策工具保障公共利益和社区福祉?如果房地产过度供应可能会促进房价进一步平稳,该当如何设计政策,使得社会利益得到最大化?”侯丽表示,书中所提到的,利用暂时的经济危急,实现相对的社会公正,设计更加渐进、原谅的城市发展政策,是方案师们值得考试测验和努力的方向。
当公共部门遇见私人企业
在公共政策不可避免地产生负面结果时,费恩斯坦认为,引入私人企业互助,通过企业精神应对市场寻衅,有助于平缓城市发展中的抵牾。但是,私人企业每每关注的是利润,他们所培植的项目每每是割裂的,如何将这些单独的项目融入城市整体方案,成为一个棘手难题。
“追逐利润是开拓商的实质。在公私互助的框架下,如何通过这种逐利的行为实现公共福利的最大化,让大众得到普遍的利益,这成为巨大的寻衅。”费恩斯坦表示。
王林表示,政府追求的是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开拓商是追求经济社会发展的利益最大化,社区组织是追求社区居民自身的利益最大化,每一个主体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不断有私人企业和政府公共的参与,如何能够培植美好城市的同时,实现利益的共赢,值得每一个主体的思考。
在她看来,城市更新是永恒的主题。当国人大多拥有稳定的住所后,对城市的诉求又到了新的阶段:须要良好的社区氛围与做事,这样推动着中国的城市发展不断向前。
讲座中,开拓商代表也表达了自己阅读后的体会。“现在的城市方案与市民需求是部分脱节的。”汤黎明表示,“开拓商虽然流淌着逐利的血液,但是所设计的产品经由完全的市场调研,符合市民的须要,而宏不雅观的方案有时对此欠缺考量,两者结合,更能填补毛病。”
张海涛认为,在城市培植中过度遭受成本裹挟会带来负面的效果。在早期的项目里,开拓者热衷于评论辩论公共参与,但是最近几年,城市发展中的成本力量愈发放大,越来越多的开拓者选择“把屋子切成豆腐块卖掉”,只考虑财务指标而非城市的长远福祉,这是否会带来成本的霸权和公共福利的退缩?关于成本和社会利益的关系,仍需城市方案者长期不懈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