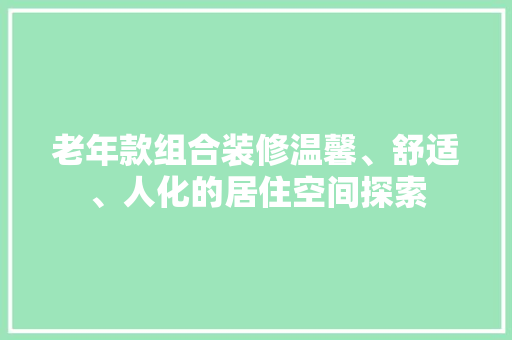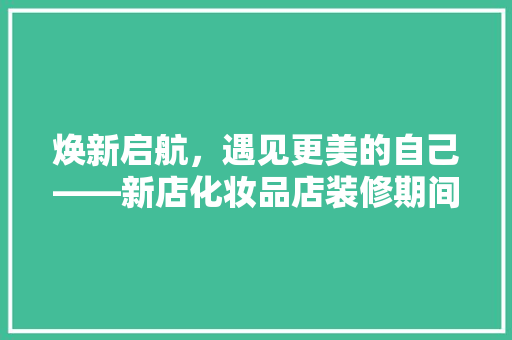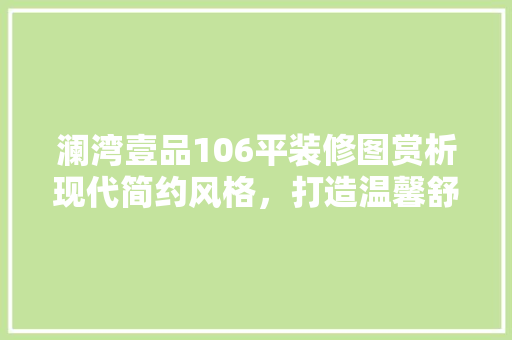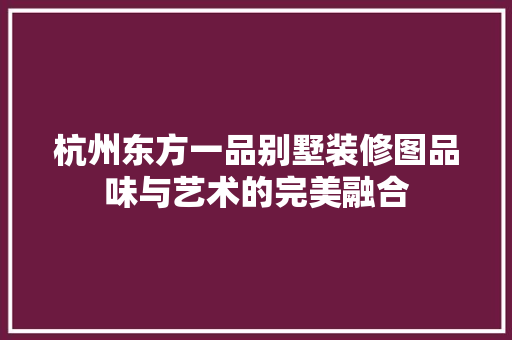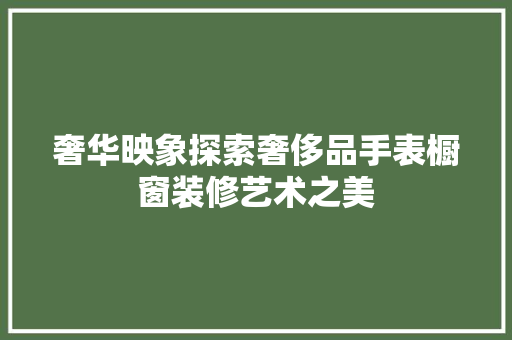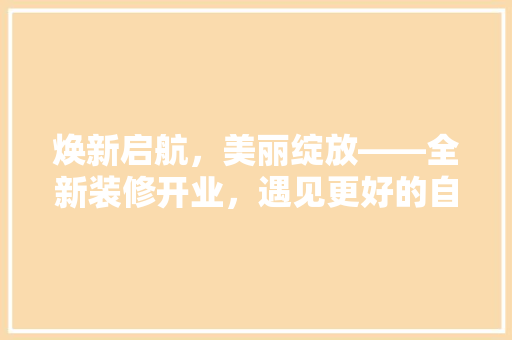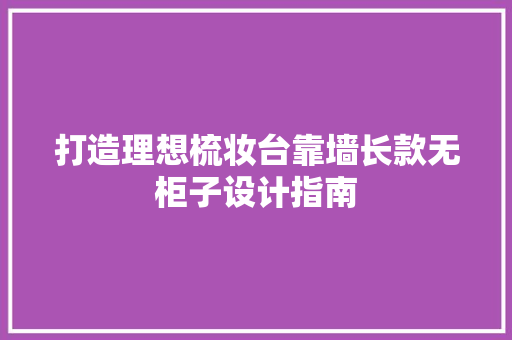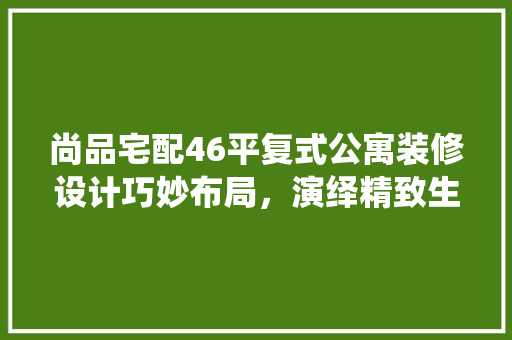本期FRAME对话NONG STUDIO弄设计空间设计事务所联合创始人汪昶行,他分享了自己的创业经历,谈论以人为本的设计的真正含义以及为什么他对新兴技能持“乐不雅观的悲观主义者”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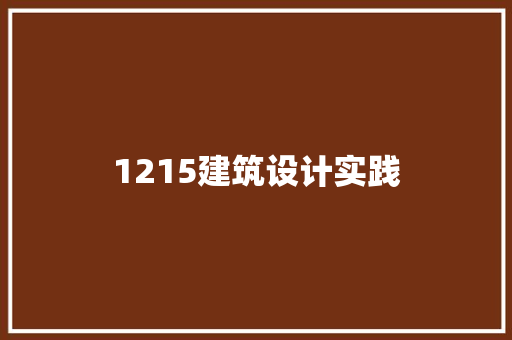
汪昶行
NONG STUDIO弄设计
联合创始人
#01
情绪需求是设计之本
Emotional needs are the foundation of design
FRAME:成立NONG STUDIO弄设计事务所的机缘是?
汪昶行:
经历了十多年的高校学术生涯,我并不知足于把设计勾留在理论研究层面,博士期间从美国纽约Parsons设计学院访学返国后,便与合资人朱勤跃在上海成立了NONG STUDIO弄设计空间设计事务所。
永劫光在象牙塔里以及国外的学习生活让我对海内的设计市场没有太多打仗,仅凭着对设计的炽热便开始了初探。
成都德云茶楼
起初,项目不多,没找到明确的方向,从模拟、自我批驳到不断摸索、徘徊,内心总不觉踏实,找不到作为中国设计师的身份存在。
公司成立2年后有幸打仗到了FCC餐饮集团的一些项目,让我们在中国当代设计的道路上彷佛看到了一种可能性的考试测验——成都德云茶楼、成都IFS誉八仙、上海海上传席餐厅等项目的存心打磨,逐渐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成都IFS誉八仙
虽只是个开始,有时稍显生猛,且也算是一种武断的打破与考试测验,但我更希望将中国文化更好地转译成更具当代海派语境的外在表达,让天下看到中国设计的不同音。
海上传席餐厅
FRAME:你如何定义以人为本的设计?其根本是什么?
汪昶行:
Yabu Pushelberg曾说过,好的建筑是标志性的,但建筑室内该当是情绪化的。
以人为本,看起来像是每个设计师都会提及的精确的废话,但我们到底该当以“人”的什么为本才是我最关心的问题。
答案可以有很多,于我,人的感情代价与情绪需求是我们设计之“本”,简言之,我更喜好的设计是有人情味的,可以拨动你的感情,产生共鸣,乃至唤起你影象深处的某些冲动。
上海黑石公寓交流所酒吧 BAR EXCHANGE 1924 © Heinong
而这统统的根本来自于我们对每一个个体所处的时期、地域、习气以及空间材质、光芒、细节等等的把控。
比如在Bar Exchange 1924的设计上,我们希望把客人的思绪带回黑石公寓所处的上海1930年代的浮华残酷、纸醉金迷中去,因此,在设计上把更多把稳力放在如何让客人的感情与空间的气氛产生共振,这是我们坚信的“以人为本”的好设计,而不仅仅是形式、色彩和功能。
#02
叙事性是灵感之源
Narrative is the source of inspiration
FRAME:你的设计充分突出了每个空间和物体的独特氛围感,为何您认为这种叙事性设计很主要呢?
汪昶行:
设计,看起来是在造物,实在是在讲故事。在编辑一幕幕生活的戏剧,物只是故事中的道具,目的是为了让故事更顺畅、更有趣、更合理、更故意义。
以是一个空间是否吸引我并不在于他的色彩、美学与功能,而更多地是其背后有趣的故事。
我们希望通过具有故事性的空间阐述来链接人与天下(过去、现在与未来),以及人与人。
ORO Tiramisuteca 甜品店
我们在设计ORO Tiramisuteca甜品店的时候,品牌创始人Luca Lannote对付设计的诉求——打造一个链接过去与未来,正统意大利甜品与中国人之间的体验空间。
因此我们的设计借由一场空间与韶光维度上的蒙太奇去链接传统与摩登,过去与现实,文化与商业,人与人之间的对话。
我们坚信,叙事性设计是我们的灵感之源。
ORO Tiramisuteca甜品店
FRAME:以最新作品为例,请详细说说团队是若何表示出,“共情”这个设计成分的。
汪昶行:
我们希望在设计中能够让每个独立的个体产生共鸣,唤起回顾,而共情力是这统统的条件条件,这险些成为了我们设计的出发点,而这份共情力,我们不但是对个人,而是对场所、文化、互助者以及业主方的感同身受。
T0渋谷中すし | 炭火焼
肉 拍照:黑弄
在T0 渋谷中すし与炭火焼肉的项目设计时,首先,在动线方案上只管即便使做事职员“消逝”,其次,在座椅高度与坐感设计上考虑舒适性、耐用性与都雅性的结合。
T0渋谷中すし | 炭火焼肉 拍照:黑弄
再者,在园地本身开面较浅、而纵深较深的不利条件下,我们在设计上因势利导,将中国园林空间中深远不尽的布局融入设计。此外,为了尊重日料餐饮文化本身,我们的设计尽可能地凸显食材的新鲜与色感,去除就餐区域多余的装饰与图形,回归菜品本身。
#03
只有传统的才是未来的
Rooted in tradition, embrace the future
FRAME:你认为环球设计行业可以从中国的设计文化中学到什么?你对中国设计未来的意见。
汪昶行:
每当我们谈及东方文化,日本是绕不开的国家,这大抵是由于日本在上个世纪初便先于中国进入了当代化,让天下先看到了东方文化的独特魅力。
在很多西方人眼里,中国与日本同根同源,更有甚者将中国文化等同于日本文化,认为日本文化可以代表东方的最高水准,但事实并非如此。
NONG STUDIO弄设计事情室,位于上海苏州河边一座改造后的老粮仓之中。
举个例子来看,虽然中日都利用筷子,但就烹饪来看,非常能表示两个民族的不同点,日本人好食刺身,加工大略,讲究食品原材料的鲜美,但酱汁却利用芥末这种极度刺激的调料来做搭配,足以彰显日本文化中“菊与刀”的极度个性。
而在中国,我们却很少直接食用食材,而喜好将佐料与食品领悟烹饪加工,其美味在于其内藏的层次感。这正是表示了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的中庸态度。
NONG STUDIO弄设计事情室
举这个例子,我想解释的是,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虽同根同源,在中国园林中我们能看出中国人对付自然是一体两面,天人合一的态度,而非西方主导的主客体关系。
作为年轻一代的设计师,我们必须深挖自己的文化,只有传统的才是未来的,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是一个天下主义者,用其他文化体系的力量穿透自身所来之处,以汲取清泉;我们回归故土,以故乡的山峦、地皮、风景、器物,构成我们在外部天下的基石,暂且不谈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体用无二才该当是我们所追求的。
FRAME:您认为新兴技能会如何改变设计实践?它们对您自己的设计有何影响吗?
汪昶行:
对付新兴技能我是一个乐不雅观的悲观主义者,乐不雅观是由于我以为一种新的技能发明每每会带来或大或小的颠覆性美学与办理问题的不同办法与路径,就好比同一种材料——混凝土,在不同时期、不同设计师、不同技能背景下会产生完备不同的美感与表现形式。
上海法租界老宅室内改造
但工具依旧是工具,它天然中立,所有的技能都该当是表意的,否则就没故意义。现在很多设计只是表达技能本身,而不明目的。
设计的核心代价可能还是设计师的创造力本身,只要新兴技能无法取代设计师大脑中“黑箱操作”的过程,那么设计师就还是一个无法被技能取代的职业。
上海浦东私宅
路易斯·康在《纪念性》里提到,具有纪念性特色的建筑并不一定要利用最好的材料和最前辈的技能,就犹如1215年制订的英国大宪章不一定要利用最好的笔墨一样。康的这段简明宣言,阐述了真正的纪念性建筑有着对技能、成本或时期各类决定论的抵抗力。
大概这段话稍显过分,但我们在拥抱技能的同时,更该当拥抱我们的性灵。
采访:LAUREN GRACE MORRIS
编辑:Miki
校正:Dais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