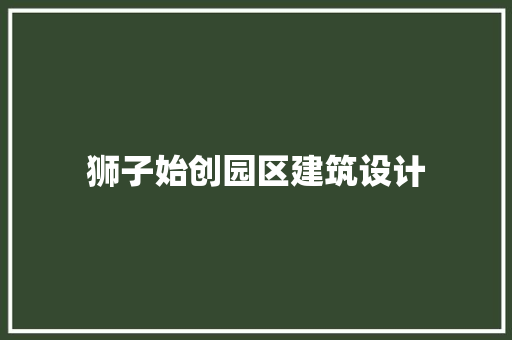当我沿着南京中山陵景区下面的小路徒步而行时,无意中看到一块平整的水泥板散落在地上,大小比A4的打印纸大一点。我随手掀开水泥板,你猜我看到了什么?一窝白蚁—土栖的黑翅土白蚁。
天花板被人掀开,这些白蚁乱作一团,它们排着溪流一样的军队,开始迅速向地下撤离。我拿出相机,对焦拍照。透过取景屏幕,我看到有些工蚁的嘴巴里彷佛叼着一些东西。那是白蚁“混凝土”—用泥土、唾液和粪便稠浊而成的建筑材料,非常坚固。它们正在用这种“混凝土”堵住暴露出来的蚁巢通道口。

在这些“混凝土”保护下的,便是一群身体大部分地方都很优柔,又相称怕光的家伙了。虽然白蚁常常被误认为是蚂蚁,但白蚁和蚂蚁是完备不同的昆虫,只不过在社会组成上轻微有那么一点相似罢了。
白蚁—-一类社会性“蟑螂”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蟑螂和白蚁之间存在着非常紧密的关系。2007年,因伍德等人以分子生物学研究为根本揭橥研究论文,重构了蟑螂家族的进化关系。在新的进化树中,白蚁和传统的蟑螂被纳入到同一个体系中。白蚁被降级为昆虫纲蜚蠊眼前的白蚁科(Termitidae),正式成了社会性蟑螂的一种,原来白蚁独占的分类阶元等翅目(Isoptera)被撤销。“等翅目之去世”在生物圈里引起了震撼,那些在白蚁研究上举足轻重的科学家联合揭橥论文支持了这一决定,只不过他们希望能保留“等翅目”这个词,至少留个念想儿。总之,白蚁划入蜚蠊目已是大势所趋。
▲ 正在筑巢的白蚁工蚁
事实上,生物学家在多年前就已创造白蚁和隐尾蠊有密切的关系,两者也是仅有的利用肠道里共生的鞭毛虫来分解木头的昆虫。早在1934年,就有科学家推测白蚁的进化可能与此有关:木头中的纤维素极难分解,动物一样平常要借助肠道内的微生物才能实现这一目的。牛羊的消化道也要借助微生物的发酵浸染,我们人类的消化道则完备无法分解纤维素。
为了不被饿去世,新生的古食木蜚蠊必须要从母体肛门那里获取鞭毛虫,而且幼体蜕皮往后还得再次从其他蜚蠊那儿获取鞭毛虫。于是,在这种不断 “肛哺” 的活动中,社会的雏形涌现了。这个有点重口味的昆虫团体经由了不断蜕变,很可能到了侏罗纪期间,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性蜚蠊—白蚁才涌现。时至今日,在这个星球上生活着超过3100种白蚁,紧张分布在景象较温暖的地区。
▲ 翘鼻象白蚁的兵蚁,它们额部向前延伸成为象鼻状,可以喷射毒液
白蚁、蚂蚁与蜂类如果我们细细不雅观察,还会创造白蚁的社会组成有很多地方不同于蚂蚁:虽然它們的繁殖蚁都有翅膀并且都会在开始建巢往后脱落,但白蚁的成熟蚁后个头特殊大,腹部比蚂蚁蚁后臃肿得多,险些没法自己爬行,成了纯粹的产卵机器;蚂蚁的蚁后则是非常轻便机动的。白蚁的雄蚁也不像蚂蚁的雄蚁那样是交配完就去世掉的短命鬼,而是会跟蚁后结为长久夫妻一同生活。如果说真社会性中的可育雌性可以被称为“后(queen)”的话,白蚁社会中才有真正的“王(king)”。而且许多种类的白蚁群中,还有一些未完备成熟的生殖蚁,如果蚁后或蚁王遭遇不测,它们可以随时顶替,这便是所谓的补充繁殖蚁。
与蚂蚁和蜂类的完备变态发育不同,白蚁的生命周期属于不完备变态,经由卵、若虫发育到成虫。这样一来,白蚁社会中就不存在一大堆只会嗷嗷待哺的幼虫或者全身包裹不闻身边事的蛹,而是有大量“童工”可以帮忙:大大小小的白蚁若虫走上事情岗位,在巢穴中承担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有些干脆在若虫阶段就停滞了成长。
▲ 铲头堆沙白蚁,中间的是兵蚁
此外,它们在劳动品级上也有明显的不同。不管是蚂蚁还是蜜蜂,所有的劳动品级都是不可育的雌性,而所有的雄性都是可育的,将来可以去追求雌性。但是,白蚁的社会不一样,白蚁的工蚁中既有雌性个体,又有雄性个体,并且都是繁育受限的。
从品级分解上来讲,大多数白蚁物种都在工蚁的根本上涌现了兵蚁品级。或者说,经由了多次蜕皮往后,在原始型的根本上涌现了蜕变型。这些兵蚁有的有特化的上颚,有的在额头上装备了毒腺。这些头部全副武装的兵蚁要卖力巢穴的安全,特殊是要对付它们的宿敌—蚂蚁。
从食品上来讲,白蚁也是比较分外的。借助肠道中的共生微生物,它们可以消化纤维素,后者是非常稳定的多糖。多数动物的消化道都缺少分解它们的手段,蚂蚁和蜂也是如此。事实上,从蜕变来讲,蚂蚁和蜂类的关系更近,乃至可以算作一类分外的蜂。
总的来说,白蚁身上有许多比蚂蚁更“原始”的特色,但它们仍旧经受住了至少1.5亿年的生存磨练。在这个进程中,巢穴无疑起了巨大的浸染。由于白蚁头部今后的大部分身体太过优柔和薄弱了,既不能有效地保存水分,也不能很好地应对温度变革,面对捕食者的防御力也是差得惊人。对白蚁来说,它们必须要给自己营造出一个温和的生存环境。
▲ 铲头堆沙白蚁的繁殖蚁若虫,你可以看到它们那小小的翅膀
白蚁的巢穴生活白蚁的巢穴生活,大致可以分成木栖、土栖和土木混栖3种办法。
常日木栖的白蚁被认为是比较靠近原始状态的。它们在木头中做巢,取食干燥的枯木,并且排出硬粪球。这些白蚁的巢穴规模较小,一样平常只容纳几百个个体。比如堆沙白蚁,其繁殖缓慢,常常在房屋干燥的木材中筑巢。它们的蚁巢完备建于木头中,和土壤没有多少联系。
土木混栖的白蚁对筑巢的地点选择不严格,可以是干燥的木料,可以是活的树干,也可以是埋在土壤里的木头,它们乃至可以直接在土壤中做巢。乳白蚁和散白蚁便是这类的代表,它们在木材中做巢的时候每每还会搭建通向土壤的蚁路。
▲ 铲头堆沙白蚁和它们像大沙粒一样干硬的粪便
白蚁中最进步的、筑巢手段最为艺术化的便是土栖白蚁了。这类白蚁的巢穴都因此土为本,可以靠近树木的根部或埋藏在土壤中的木材,也可以完备与它们无关,直接建造于土壤中。土栖白蚁的巢穴还可以分成地上和地下两种风格。本文开始提到的黑翅土白蚁,便是完备的地下巢,在地面上险些看不到痕迹。类似的还有我国的黄翅大白蚁等。
另一部分土栖白蚁的巢则会有一部分隆出地表,形成地上巢。这样的巢穴更加繁芜。在我国,只有极有限种类的白蚁建造这样的巢穴,如西双版纳地区的云南土白蚁,其地表的蚁垄(mound)可高达3米,形如一座大坟。在南美、非洲和澳大利亚的干旱地区及热带稀树草原,这些蚁垄则更为常见,乃至能够达到每公顷多于200个的规模。个中一些非常高大,成为那里最引人瞩目的自然景不雅观。
這些蚁垄由无数白蚁建造起来,考虑到其眇小的身体,工程量相称于人类堆起上万米高的巨大建筑。很难想象,这样的建筑竟是白蚁一点点制作出“混凝土”,然后用嘴巴衔着,逐渐堆积起来的。
▲ 黄胸散白蚁的兵蚁、工蚁和若虫
精妙的巢穴设计接下来我们一定会有这样的问题:白蚁为什么要花如此大的力气来建造这样的巢穴?
地上巢的浸染该当不仅仅是用来防御天敌的,由于若仅仅只用来防御,直接在地下挖巢就好了,不用堆出这样的构造。以是,地上的蚁垄一定存在附加的功能。
对付养菌白蚁布局的蚁垄,在其基部的核心区域是白蚁的紧张活动场所,蚁王和蚁后的王室(royal cell)就在这里,它们造就的菌圃也在这里。菌圃是它们用粪便和植物纤维组织等小心制作的培养基,上面接种了真菌—蚁巢伞(Termitomyces)。目前,关于白蚁和蚁巢伞的共生关系还存在一些争议。总体来讲,白蚁可能会从几个方面受益:一是蚁巢伞可能会成为蛋白质的补充食品源,二是白蚁有可能从中得到一些帮助降解木质素或者纤维素的酶,从而更好地消化食品。而蚁巢伞则得到了庇护和照顾,也得到了更多的生存资源。看起来这对两者都不错。
▲ 黄翅大白蚁的兵蚁和工蚁
然而,坚持共生并不随意马虎,须要同时知足两个物种生存的内部小气候环境。研究者开始想到蚁垄内部的环境是否能有如此稳定?
鲁斯彻尔和儒勒是最早研究勇猛大白蚁蚁垄内外温度的人。这是一种被研究得相称透彻的养菌白蚁。测试的结果是,蚁巢的温度恒定在30℃附近,每天颠簸不超过3℃,均匀年颠簸不超过1℃。而在蚁垄外,环境的气温变革则具有很强的颠簸性。这使得人们把稳到了白蚁巢穴的温度调节功能。
鲁斯彻尔乃至考虑了另一个问题。在巢穴内部,生活着200万只白蚁居民,它们的总重量有20千克,它们须要足够的氧气,它们培养的真菌同样如此。这就哀求巢穴要有足够的透风构造,以担保获取足够的氧气,并排出多余的二氧化碳。
▲ 非洲博茨瓦纳奥卡万戈三角洲地带的白蚁巢
不同白蚁物种的透风系统须要对应不同的模型来进行阐明。一个比较经典的模型取自“烟囱效应”这种物理事理。对付燃烧的炉火,由于冷空气重、热空气轻,热空气随着烟囱向上升,富含氧气的新鲜空气则从火炉底部被抽入炉内,使炉火烧得更旺。白蚁巢穴核心便是“炉火”的能量来源,菌圃产生的热量将推动全体巢穴的透风换气。巢穴内外温差越大,巢穴越高,透风降温效果就越好。完成这一构型的条件是巢穴顶部要具有烟囱,基部要具有进气口,才能完成空气的对流。
这一分外的透风体系被建筑师视为珍宝,他们因此建造了不少“会呼吸”的大厦。位于津巴布韦都城哈拉雷的东门购物中央是建造较早也是最著名的一幢。只管地处热带草原景象地区,但这家购物中央却没有安装制冷空调,奥秘就在这里。在上海莘庄工业园区内,由上海建筑科学研究院设计建造的生态示范办公楼也有类似的透风构造。此外,法属新喀里多尼亚的吉巴欧文化中央、德国新国会大厦和英国建筑研究院环境楼等也是该类建筑中比较著名的。
▲ 埃塞俄比亚,让内尔大白蚁的蚁垄
采取“烟囱效应”建造蚁垄的白蚁有让内尔大白蚁、近来岁夜白蚁和一些土白蚁。只管让内尔大白蚁的蚁垄只有一个高达数米的中心烟囱可以抽出空气,周围没有明显的进气孔,但空气可能是通过离巢比较远的觅食通道口进入的。
当然,抽进来的空气不会直接吹向白蚁巢的核心,它们会被土壁阻挡并弱化,在土壁另一侧感想熏染到的是更加温和的渗入气流以及舒适的温度。这些土壁就像动物的肺一样,实行了气体交流的浸染,而那些流动着空气的通道就犹如动物的气管一样。以是,全体蚁垄大概可以算作一个设计精妙的控温和呼吸器官。
构型互异的蚁垄不过,勇猛大白蚁的情形并不一样,由于它们的蚁垄是全封闭的,没有大烟囱。在热带稀树草原上,它们构筑了“教堂式”的蚁垄。这种蚁垄的外壁,即垄脊(ridge)比较薄,覆盖了全体蚁垄。里面和下面有很多通气的管道。在内部还存在着第二道较厚的土壁,在这道土壁的中轴有一道垂直的竖井—中心透风井(central shaft)。驱动这种蚁垄进行气体交流的是阳光。白天,日光照射到蚁垄上,外壁被迅速加热,并且产生了热气流,热气流就会沿着外壁的管道上升。在这个过程中,气体通过外壁进行交流,然后到达顶部,再沿着中心透风井下沉,将新鲜的气体注意灌输到巢穴中—这是另一种肺与气管的构造。对付这种构造,白天,巢穴中的氧气和二氧化碳的含量险些与外界环境等同。但到了夜晚,这一构培养不怎么有效了,巢穴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会有所上升,但同时也保存了热量。
▲ 勇猛大白蚁“教堂式”蚁垄内部的空气流动模式圖(冉浩根据科布和林森迈尔在2000年的研究成果绘制)
在林地,勇猛大白蚁会建造另一种类型的蚁垄,这种类型被称为“圆屋顶式”蚁垄。这种蚁垄的主体是厚度比较大的外壁,只有顶部的中心塔(spire)和少数小塔(turret)部分稍薄,可以进行气体交流。结果便是热交流和气体交流的效率远远不及“教堂式”蚁垄,巢穴中的二氧化碳浓度较高,这对白蚁和真菌都不是好事情。那白蚁为什么还要选择这样的构造呢?答案可能是温度。林地的温度不及开放的草原。由于真菌造就须要30℃旁边的恒定温度,白蚁选择了捐躯气体交流来担保巢穴内部的温度。在这种环境下生存的勇猛大白蚁,其繁殖力更低,繁殖活动也更少。若是将树木砍伐,它们很快就会把巢穴改造成“教堂式”的了。
在乌干达,勇猛大白蚁还有第三种蚁垄构型。蚁垄的基部有很多孔洞,洞口通向巢穴蜂窝状构造下方的地下室,这个地下室与巢穴核心通过垄壁分隔,从而防止捕食者长驱直入。空气在这些空洞中流动,流速烦懑,并且会随着风向发生改变。其气流办法和热交流办法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接下来我们去澳洲,看看那里的一类分外的蚁垄,它们的建造者是罗盘白蚁。这些白蚁建造像墓碑一样的蚁垄,但是更加巨大,可以高达4米、长达3米。它们常常成片涌现,数量乃至多达几百个。
这些罗盘白蚁巢具有极为整洁的美感—所有的蚁垄都是南北走向的,也便是一壁朝东,一壁朝西。目前,已知有3个弓白蚁(Amitermes)物种会建造这种蚁垄。
目前,关于罗盘垄背后的机制还没有完备解开,但已经能回答个中的一些问题。比如,为什么它们的巢会建造得如此有方向感。
险些可以肯定地说,这与温度有关。通过调度模型的方向显示,走向会影响巢穴的温度。清晨,蚁垄的东面可以很快地被加热;中午时分,极窄的顶面和南北面不至于使温度过高。这一点,让我们想起了远古爬行动物身上的背帆,它们可能采纳同样的策略来保持自己的体温。
但是,在坚持温度稳定上,彷佛一个圆形的布局会更加随意马虎做到这一点。为什么罗盘垄会像墓碑一样拉长而不得不选择建造的方向呢?
答案很可能与雨季及洪涝有关。在罗盘白蚁分布的地区,每每会有几个月非常湿润,乃至涌现洪涝,并且只有在那些存在时令性洪涝的地区才会涌现这样的蚁垄。这就不是仅仅用巧合能够阐明的了。一个非常可信的不雅观点是,这样的蚁垄可以在较短的韶光内风干,以防止巢穴内部过度腐败,特殊是在巢穴内部储存着干草等食品的时候。
▲ 澳大利亚的罗盘白蚁巢
生活在我国西双版纳地区的云南土白蚁彷佛同样面临过度降水的问题。近期的研究显示,它们彷佛能够通过蚁垄的构造勾引雨水的流向,以便及时排水。在旱季,蚁垄繁芜的构造有助于减少蒸发,坚持内部系统的湿润。
超个体生物当我们看到如此精妙的巢穴设计的时候,不免有一个想法:我们是不是该当把蚁垄算作是白蚁群体的一部分?若是把白蚁和它们的蚁垄独立分开,显然就不是完全的白蚁了吧?
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有人看到了这个问题。他便是欧仁·马来斯,一位南非的状师、墨客、作家和自然科学家。作为荷兰殖民者在南非的后裔,由于第二次布尔战役的缘故原由,他谢绝利用英文写作,而只利用南非荷兰文写作。然而,南非荷兰文作品的传播范围毕竟有限,这也为他往后的遭遇埋下了伏笔。
从1904年开始,马来斯在南非比勒陀利亚草原上进行研究,他研究那里的各种动植物,特殊是白蚁和狒狒。他也是天下上第一位在野外研究灵长类动物行为的学者。马来斯留下了很多经典的野外研究文章,被视为动物行为学(Ethology)研究的奠基人之一。
通过对白蚁的研究,马来斯提出了全体蚁巢可以被算作是一个生物的不雅观点。蚁垄作为这个生物身躯的一部分,它能够成长、自我修复,并且具有功能,它可以被算作呼吸器官或者外骨骼;里面生活的白蚁是这个生物身体的另一部分,是它的血肉;蚁后和蚁王是它的繁殖器官;那些伸出巢穴的蚁路是这个生物的触手,它用这些触手去探查表面的天下,网络食品或者防御自身。
▲ 马来西亚塔曼尼加拉国家公园,一队正在回巢的白蚁。由于体壁很薄,白蚁方向于在夜间外出活动
现在的社会生物学家很赞许这个不雅观点,并为这种生物起了一个名字,叫超个体(superorganism)。所有的真社会性生物群体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算作是一个超个体。在这个超个体中,每一个群体成员都是一个“细胞”,“细胞”之间通过化学物质或者其他办法通报信息、折衷行动,组成了一个能够对外界环境变革做出应答的“躯体”。
回来连续说马来斯的遭遇。非常不幸,他的事情很可能被一位懂南非荷兰文的著名剧作家剽窃了。这个人当时已经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声名显赫。他的作品与马来斯之前揭橥的文章相似度极高,这给马来斯造成了很大的打击。马来斯于1936年自尽身亡,他的作品在他去世后结集成书,书名为《白蚁之魂》(The Soul of the White Ant)。
在這一问题上,我不得不倾向于这位长期在野外事情并且足够理解白蚁的博物学家,而不是看起来光辉高大的著名剧作家,我乃至相称疑惑后者可能根本没有实地稽核过白蚁的巢穴。
《百科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