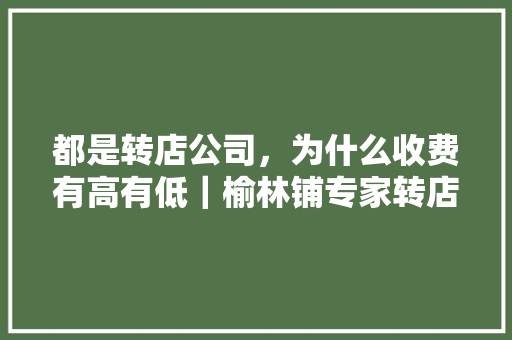山林深处访古村落,楼宇殿前话红军
下曹村落位于宁化县南部,迄今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是我国古代精良建筑艺术的展示地,目前还保留不少明清古建筑,拥有“中国历史文化名村落”“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两块国家级金字招牌的名誉,还获评为省级“爱国主义教诲基地”、市级“中心红军村落”。红十二军、红一军团、红九军团、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等红军部队都曾在此开展革命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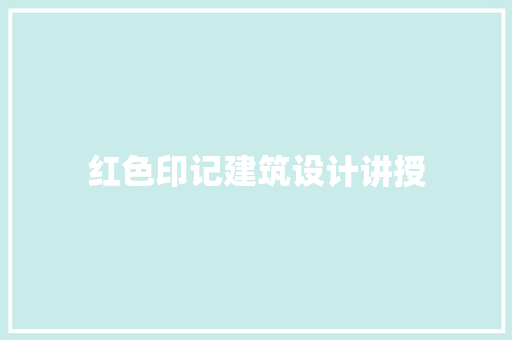
九龙桥。海峡网 李牧晨 摄
下曹村落第一布告、红军后代曹春福先容九龙寺。海峡网 李牧晨 摄
穿过村落口的雅南楼,跨过九龙桥,一起上古木葱茏、溪水潺潺。“我们村落始建于南宋德祐元年,据村落里族谱记载,当年先人是先种树后建村落,以是现在村落周围的这些古树都有七百多年树龄了。”下曹村落第一布告、红军后代曹春福先容说。
沿着村落道,一起上古木葱茏、溪水潺潺。海峡网 李牧晨 摄
松子坝和红三十四师将士林。海峡网 李牧晨 摄
站在据传为清代村落内武秀才练武的松子坝旁,曹春福指着一片青翠的小树林见告,2019年12月,福建籍湘江战役红三十四师义士后代集结在这个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和其先辈们共同战斗过的下曹村落,一起种下34棵松柏树,将它取名为“红三十四师将士林”。
采访调研团穿过满塘荷花。海峡网 李牧晨 摄
敬湖公祠。海峡网 李牧晨 摄
上曹村落苏区干部后代曹祥增分享其父亲的回顾录。海峡网 李牧晨 摄
顺着村落中古道一起前行,在那满塘荷花之后,便来到青砖灰瓦的敬湖公祠。这里也是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宿营地旧址。在门前,曹坊镇上曹村落苏区干部后代曹祥增讲述了红九军团后方机关在曹坊镇“万人军民大联欢”“鸡爪梨树下集结出发长征”等革命故事,“这些故事都记录在我父亲曹发伙的回顾录里,他从68岁开始写回顾录,就怕自己去世后没有人知道当年的事了。老人家说‘要让后人知道我们曹坊有这段历史’。”
曹祥增展示其父亲曹发伙的部分回顾录照片。海峡网 李牧晨 摄
青砖黛瓦品沧桑,赤色故事永相传
下曹村落革命旧址群内,古巷通幽。海峡网 李牧晨 摄
采访调研团一行溜达在高墙窄道间。海峡网 李牧晨 摄
溜达不才曹村落革命旧址群,巷弄弯曲,四向通达,高墙窄道错落其间,历史的沧桑感油然而生。据曹春福先容,下曹村落登记在册的“六古”建筑(古民居、古巷、古宗祠、古桥、古井、古寺庙)达51处,个中七处被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八字形门楼、马头墙、高墙深宅,这些都是范例的客家建筑特色。
亦中公厅,也是宁化县拍照家协会创作基地。海峡网 李牧晨 摄
革命先驱徐赤生的孙子徐荣辉在此回顾徐赤生的点滴业绩。海峡网 李牧晨 摄
极具艺术代价的明清古建筑群也吸引了浩瀚拍照家前来创作,不少精美作品被保存在了亦中公厅里。革命先驱徐赤生的孙子徐荣辉在此回顾起作为宁化县第一个共产党员——徐赤生的点滴业绩。“我爷爷出生于地主家庭,家里霸占着大量地皮,在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认为革命要先从自己‘革’起,就率先将自家的田契当众烧毁,还派人宰杀自家的猪,打开谷仓救援贫民。”徐荣辉说:“当年家中的那些长辈肯定都把爷爷当作败家子,可在我心中他便是真英雄。”
曹春福讲述其爷爷曹生苟和祖宅的故事。海峡网 李牧晨 摄
在红四军、红一军驻地旧址,也是曹春福的祖宅——安祥公厅厦中,曹春福讲述了这栋老宅内发生的故事。“我爷爷是村落里的一位苏区干部,红军长征走后,在参加一次干部秘密会议时被国民党包围,浴血奋战后被捕。在国民党的严刑拷打下,爷爷宁去世也不说游击队的着落,后来国民党就进入这个品字厅,用刀将他残酷杀害了。爷爷被杀时,我奶奶和父亲就躲在隔壁的粮仓里。”曹春福说,由于打击太大,奶奶在三天后去世,留下年仅8岁的父亲为了躲避国民党的“鸡犬不留”东躲西藏,一贯到14岁往后才回到这里。
“我实在一贯不忍心让我父亲回顾那段悲哀往事,他也常常说都是过去的事了,让我不用知道。可我认为还是该当讲好赤色故事,让现在的人知道本日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让我们的赤色精神代代相传。”曹春福的一席话,让久难忘怀。
湘江战役幸存者、老红军曾繁益的侄孙曾令传讲述英雄故事。海峡网 李牧晨 摄
走完长征全程的“武术高手”、老红军冯义隆的侄孙冯国民讲述英雄故事。海峡网 李牧晨 摄
随后,湘江战役幸存者、老红军曾繁益的侄孙曾令传,走完长征全程的“武术高手”、老红军冯义隆的侄孙冯国民……一位位红军后代向采访调研团分享了红军战士们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
1933年,17岁的曾繁益毅然投身革命,后编入红五军团红三十四师。1934年,参加湘江战役后,曾繁益和战友们连续长征,在广西雾源山区轿顶山山顶决斗苦战到末了一刻,从几十米高的峭壁跳下,幸被树枝挂住,后被村落民所救。这些业绩记录于红三十四师一○○团团长的韩伟的《红三十四师浴血奋战湘江之侧》中。
1909年,冯义隆出生于宁化县曹坊镇三黄村落。家里兄弟五人,他排行老二。由于家境贫寒,为了生存,家里送他去连城县学习制作圆桶的手艺。手艺没学成,反倒习了一身身手回来。在清流草坪圩、田源、田口等战斗中,冯义隆一马当先,突入敌方阵地,缴获不少枪支弹药,受到记功奖励。一次战斗中,当地民团盘踞在一个土堡内,又有重机枪,红军久攻不下,冯义隆去老百姓家里借了一床棉被,扔到水沟里,背在身上匍匐提高。子弹穿不透湿棉被,他爬到城堡下面的一棵树下,背着棉被攀爬上去,用大刀砍去世了巡逻的仇敌,再跳到城墙下面砍杀守门人,打开城门,立下战功被奖励。
敬湖公祠的墙上,依稀可见红军标语。海峡网 李牧晨 摄
安祥公厅厦,也是红四军、红一军驻地旧址内的红军标语。海峡网 李牧晨 摄
曹春福先容红一军团军需仓库旧址大门旁的红军标语。海峡网 李牧晨 摄
走过一幢幢古民居,聆听一段段赤色故事,看着墙上时而涌现的红军标语,让人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在红一军团军需仓库旧址——立人公厅厦,曹春福指着门口墙壁上模糊不清的红军标语表示,据统计,下曹村落保存的红军标语共有34条,但随着韶光流逝这些标语已经越来越模糊。看着十多年前自己拍摄的照片与现在比拟,他感到很惋惜。
历经岁月,墙上的红军标语已模糊不清。海峡网 李牧晨 摄
“我小时候,在敬湖公祠墙上还能瞥见非常大的红军标语,一个字最少有一米多宽,内容我还记得,就6个字:当红军最光荣。可惜现在已经看不到了。”曹春福认为,岁月或许能磨灭红军留下的标语,却磨灭不了人们心中的红军印记。
来源:海峡网